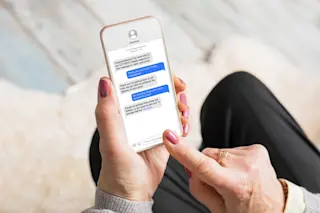奥利弗·萨克斯的格林威治村办公室的柜子里堆满了数百本黑色小笔记本,每本都写满了潦草的笔记和草图、报纸剪报和照片。这些是他一生观察人类大脑非同寻常的失灵和异常行为的积淀:一个坚信自己的一条腿不属于自己的男人,一个对动物有深刻理解能力的自闭症女性,以及那个将妻子误认为帽子的男人——这个案例启发了萨克斯最著名的一本书。
然而,人们可能不知道的是,74岁的神经学家萨克斯在大部分职业生涯中,一直在纽约市各地的精神卫生机构为病人看病。这些病人有更普遍的问题,比如痴呆症、坐骨神经痛、步态障碍和癫痫发作。当然,他也很喜欢挑战不寻常的病例,而且这类病例也一直在找他。他的书《觉醒》(Awakenings)被改编成一部获得奥斯卡提名的由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电影后,信件便如潮水般涌来,至今未断。许多信件来自正在经历有趣的神经系统现象,或者认识有此症状的人。“我的助手凯特会去掉大约十分之九的信件,”萨克斯说,“这样我每年还有大约一千封信要读。”
在他的最新著作《音乐狂:音乐与大脑的奇闻异事》(Musicophilia: Tales of Music and the Brain)中,萨克斯关注的是与音乐对大脑影响相关的罕见病例,例如,一位通过打鼓缓解妥瑞氏综合征的男人,以及另一位被脑海中不受控制且持续不断的旋律逼疯的男人。
萨克斯坐在一张老旧的木制书桌前,身后是一面贴满了过去病患快照的墙壁。他向《Discover》杂志讲述了他近期对音乐的研究、他试图解锁自己创造力秘藏的实验,以及为何他总是尽可能地在他病人身上强调积极的一面。
您以写书闻名,大多数人不知道您还有一份“正职”。您的日常工作是什么样的?嗯,我还是会看一些病人。有些病人住在疗养院或慢性病机构,比如 Beth Abraham 医院,那里的事件发生在 40 年前的《觉醒》一书中,或者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我也在那里工作了将近 40 年。我也会去诊所,还喜欢做一些上门拜访。例如,我亲自去布朗克斯区拜访了一位患有音乐缺失症(amusia,无法感知音乐音调和节奏)的女士。
一个没有音乐的世界:她的生活是怎样的?她是一位令人愉快、聪明的女士,曾是一名教师,从她年轻时起就无法辨认任何音乐,也听不出音乐。她自己对我说:“你想知道当我听音乐时是什么感觉吗?去厨房里把锅碗瓢盆扔得到处都是。我听到的就是那种声音。”所以,虽然有些人相当五音不全,但这与这位多才多艺、口才极佳的女性完全无法感知或理解音乐的能力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她非常庆幸得知这种所谓的先天性音乐缺失症有明确的神经学基础。这并非仅仅是她想象出来的;其他人也有这种情况,尽管非常罕见。她曾和丈夫一起去看音乐会。她说,她希望自己能早 70 年被诊断出来。这样她就可以避免一生中在听音乐时,尽管礼貌但却感到无聊、困惑,有时甚至痛苦。
在《音乐狂》中,您描述了 33 年前您在一次登山事故中严重受伤后,一次深刻的个人音乐体验。音乐是如何帮助您的?
我当时一条腿毫无知觉,又在高山上海拔五六千英尺的地方。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那是在手机普及之前的时代——我必须设法自救。我恰好带了一根雨伞,我把它顶端折断,用来固定我的腿。我试图用肘部推动自己下山,这是一个非常笨拙的动作。然后我发现《伏尔加船夫的歌》在我脑海中回响。我会在歌曲的每个节拍上用力地“嘿——哦——”地划动。就这样,我感觉自己仿佛被“音乐”推下了山。这变得有趣、轻松且高效。一切似乎都通过节拍得到了协调和同步。
音乐也帮助您康复了吗?是的,在我安全并被医治好腿后,我的神经系统仍然处于休眠状态。在这种损伤中,身体的感知会发生变化。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显示了这种情况。如果一个肢体长时间不动,它在大脑皮层映射的身体意象中的代表就会开始消失,变得难以使用。单纯的意志力可能不足以让它恢复;你几乎必须被“诱骗”回行动中。必须发生一些自发的事情。对我来说,其中一种形式就是音乐突然来到我脑海——我反复听的那盘磁带(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它像幻觉一样来到我脑海,促使我重新开始,激发了我再次行走的能力。我曾经见过一位老年妇女,她摔断了臀部;没人知道为什么她的腿不动。她告诉我,在她听爱尔兰吉格舞曲时,腿曾经动过一次。
您也发现,失语症患者——由于神经损伤无法说话——有时也能唱歌。相当一部分人可以。所以,当我见到失语症患者时,我会自动地和他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除了命题性言语和造句,语言似乎也内嵌在歌曲和各种自动化行为中。我不喜欢“自动化”这个词,但当你背诵一首诗时,它是存在的,它被用作一种不同于常规言语记忆的记忆形式。它是作为程序性记忆使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是机械的。
音乐似乎与大脑的许多功能有关:它可以帮助记忆,辅助运动,触发情绪。这是为什么?无论音乐是如何开始的——也许节奏感的进化与音调感的进化是完全不同的——它现在已经占据了大脑的许多不同区域,肯定比语言多。同样,音乐在神经学上也非常强大。有些人患有严重的大脑疾病,但仍然对音乐有反应。
这是否意味着音乐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类生存,或者至少是对社会生存至关重要?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只能说,没有哪个文化是没有音乐的。几乎没有个体是没有音乐的。布朗克斯的那位女士是百万分之一的例外。在每种文化中,音乐都是跳舞、唱歌的社会粘合剂。它总是仪式和宗教的一部分,然后还有劳动歌曲和军乐等。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曾说:“音乐可以从我们这个物种中消失,而我们生活方式的其他方面几乎不会受到影响。”我强烈反对这一点,而且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人类学家会同意这一点。
您对音乐如此着迷,为什么现在才开始写它?回溯 40 年前,我非常震惊于音乐对我所见的许多病人产生的治疗效果:帕金森病患者、失语症患者、痴呆症患者。但在过去的 20 年里,人们已经能够在大脑进行音乐聆听、想象或创作时检查活体大脑,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 30 年前是无法想象的——定义大脑不同区域在人们听音乐、想象音乐、创作音乐时所发生的一切。虽然我在 20 或 30 年前就已经体验到音乐的力量和各种音乐体验,但我无法像现在这样为其提供科学依据。
在《音乐狂》中,您认为对音乐的情感反应可能与其他情感反应不同。您认为区别是什么?
我认为对音乐的情感反应可以极其复杂、神秘而深刻。你可能会感到痛苦、狂喜,但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甚至无法说出那种感觉是什么。寻常的情感根本无法与音乐体验相提并论。在临床上,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在头部受伤或中风后——突然不再享受音乐,但仍然享受其他一切,并且能完美地感知音乐。然后也有与之相反的情况,这给了我的书起名:一些人发展出一种奇怪的对音乐的特定需求——他们必须拥有它。
音乐能成为一种饥渴,就像对食物、睡眠或性爱的需求一样,这似乎很奇怪。我同意。而且这种需求可能非常非常具体——因为通常你想要的不仅仅是音乐;你必须是勃拉姆斯,或者必须是某个特定的钢琴家。正是这种精确的音乐才能契合你的状况,填补某个特定的空虚——而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做到。
有一种观点认为,天才的能力可能普遍存在或潜在存在于我们所有人身上,并可以被释放出来。
还有一些人是音乐天才,他们的音乐能力远超常人。您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天才(savant)是指那些在计算、音乐或绘画方面具有非凡能力,但整体智力较低的人——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异常现象。我第一次在布朗克斯精神病院的自闭症机构人口中看到天才综合征。我研究最详细的天才是史蒂芬·威尔特希尔(Steven Wiltshire)。他身上确实有一种自主的感觉。他会瞥一眼风景,然后就开始绘画。他可能在画画时环顾四周;他会吹口哨。似乎没有集中注意力。而且他画画的方式可能很奇怪。他不会先打草稿;他不会画出显著的特征。他会从纸的一边开始,然后像这样(萨克斯发出一种颤音,并从纸的一侧到另一侧做出动作)。他也是一位音乐天才。他不仅具有绝对音准,还能理解赋格的结构。看到一个人一方面令人惊叹,另一方面却存在严重缺陷,这是非常非常令人震惊的。这种差异可能会随着练习和可能的痴迷而增加——因为,当然,这可能是他们生活中唯一高度令人愉悦和有益的事情。
像这样的人的大脑里发生了什么?一些神经学家认为,天才可能在大脑右半球保留并增强了原始的感知和计算能力——这种能力在抽象智力和语言发展时通常会被抑制。如果抽象智力和语言没有发展,那么它们可能,可以说,更加“自由”。支持这一观点的一个证据可能是天才般能力的晚期出现,例如在额颞叶痴呆患者身上;正是在语言和抽象智力衰退的同时,我们有时会看到艺术能力的出现。在澳大利亚,一位名叫艾伦·斯奈德(Allan Snyder)的研究人员正在使用 TMS(经颅磁刺激)来尝试抑制占主导地位的左颞叶。我曾尝试过,但 15 分钟后我就头痛了。而且我确实有点害怕 TMS 对我自己神经系统的影响。
您刺激自己的大脑是为了解锁创造力?发生了什么?有人让我画一条狗。我非常不擅长画画。我画的狗——嗯,它不太像阿米巴原虫,但它是一个图示化的四足动物。它都可以被画成大象或老鼠。实验者想看看我是否会失去一些抽象的公式化特点,画出一只迷人的侧面狗。也许如果我坚持更久……但我当时开始感到一种奇怪的头痛。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是一种特异反应。但确实,有一种诱人的想法是,这种天才般的能力可能普遍存在或潜在存在于我们所有人身上,并在某些情况下被释放出来。但如果释放是以失去清晰表达——我们更高层次的能力——为代价,那可能不是一个好交易。
您尝试过其他方法来改变您的大脑功能吗?嗯,我在我的新书的一个脚注中提到了一个相当自传性的事情,关于兴奋剂,那是在 40 多年前。 (萨克斯曾尝试过大量剂量的兴奋剂。)我曾有两个星期处于一种非常奇怪的状态,在那段时间里,我这个不会画画的人,发现自己能够画出最精确的解剖图。我有一本当时的笔记本,里面充满了各种我以前从未画过、也再也没有画过的解剖图。这还影响了音乐复制和嗅觉等。我能通过气味认出大多数人和地方。所以我自己确实有过各种感知能力被释放的经历。当这一切消失时,我心情复杂。这是一种巨大的解脱,但也有些遗憾。然而,我认为兴奋剂非常危险,我很高兴我熬过了那个时期。
一些评论家认为您将您的研究对象“浪漫化”了——您以一种伤感、甚至喜悦的方式描写了一些非常悲伤的病例。您为什么如此关注积极的一面?嗯,我想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它与消极的一面并存。在老式的病历中,人们会写下 HPC,即“主诉史”。病人去看医生是因为有问题;他们有主诉。我们会和病人一起回顾,但同时我们也想提醒他们那些仍然存在的能力,这些能力或许可以被他们利用,并能缓解生活。我对康复非常感兴趣。我不说“治愈”。或许“康复”听起来有些技术性,但它是在现有条件下让生活尽可能充实。
音乐与康复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之一,来自您病人克莱夫的故事。您能描述一下这个病例吗?克莱夫曾是英国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和音乐学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他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病毒引起的脑炎,是疱疹性脑炎。这导致他大脑的各个部分,尤其是颞叶和海马系统(对个人记忆至关重要)遭到严重破坏。结果,当克莱夫从高烧(疾病的急性症状)中恢复过来时,他患有严重的失忆症;也就是说,他记不住几秒钟前别人对他说过的话或他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还存在记忆的回溯性删除。所以,在他生病前的很多年,以及在他一生中的某些时刻,他的记忆都消失了。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没有记忆的人。因此,他显得非常沮丧、不在线,非常恐惧和混乱。但他的妻子黛博拉(她也是一位音乐家,曾是他的合唱团成员)发现,他的音乐感——他以最高专业水平识别和演奏音乐的能力——完全 intact。他能够唱歌、弹钢琴、指挥乐队或合唱团,而且演奏得非常出色。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事件的记忆几乎被抹去了,而演奏的记忆,尤其是演奏音乐的记忆,却完好无损。他仍然保持着演奏家的水平——这种情况持续了 20 多年。
您关于克莱夫的章节令人意外地振奋人心,因为他在指挥时似乎非常快乐。这种悖论在您的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克莱夫真是——我本来要说脏话。克莱夫真是太悲惨了。我们可以挑出亮点,但他在很多方面都被摧毁了。我是说,谢天谢地,还有音乐……我希望我没有不切实际地浪漫化。
我认为我的工作,以及医生的工作,都是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努力帮助一个人去生活——真实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