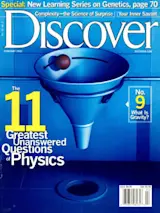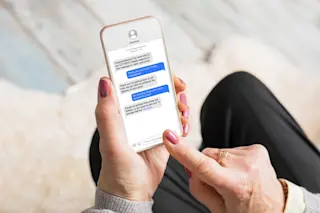上周我接到了一个我自1973年以来一直在等待的电话。那年我16岁,是纽约市一所另类高中的学生。我的同学们和我都想成为嬉皮士,嫉妒我们那些经历过1960年代的哥哥姐姐们。那个夏天,沃特金斯格伦镇举行了一场摇滚音乐节,结果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音乐节之一。在60万朝圣者中,有我们的两个朋友:邦妮·比克维特,穿着她的农妇衬衫和头巾;还有米切尔·魏泽,留着马尾辫。他们在城外邦妮工作的一个夏令营会合,然后搭便车去了摇滚音乐节。我们再也没见过他们。
我们对邦妮和米奇所知的一切都让我们相信他们没有私奔。他们肯定出了事。整个秋天,我们和脾气暴躁的乡村警长以及记者交谈。我们周末在曼哈顿东村张贴邦妮和米奇的照片,在那些据传绑架孩子的邪教组织建筑附近。我们噩梦连连,梦到强奸、折磨和谋杀。失去这些朋友是我青春期的催化事件。最终,这被证明是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青少年失踪悬案。
然后,漫长的搜寻突然结束了。米奇和邦妮的同学举行了25周年聚会。一场纪念他们的仪式得到了一些新闻报道。正确的人在失踪人口节目中看到了报道,并报了警。
那人告诉警察,他遇到的一对离开沃特金斯格伦的青少年情侣溺水身亡。这对情侣符合邦妮和米奇的描述,而且那人故事的细节听起来很真实。这个消息很快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在那些现在几乎不记得彼此的人中间传播开来。在沉闷的兴奋中,我们都不断回到同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人的故事是真的,邦妮和米奇的尸体应该已经被找到。我们想,把尸体给我们看,他们的失踪之谜就会一劳永逸地解决。
渴望我们认识或爱的人死亡的实物证据是人类的自然冲动。但这种渴望往往远远超出了对确定性的纯粹理性需求。在某人不可能再活着的丝毫机会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投入巨大的精力,甚至冒着其他人的生命危险去寻找死者。例如,去年秋天,一个国际潜水员团队在挪威海岸波涛汹涌的海域连续工作了两个多星期,冒着极大的风险从沉没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潜艇中打捞尸体。在去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之后,与打捞遗体相关的强烈情感渴望尤为突出。世贸中心双子塔倒塌后,随着日子和周的过去,美国陷入了一种肃穆的沉默,这是我们几代人以来最接近神圣的国家仪式的事情:在归零地搜寻死者。
9月11日之后在归零地附近张贴的失踪人员告示象征着死后无法找回尸体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当局尚未确定双子塔中遇难者的确切人数。最初估计的6700人几个月后减少到大约3100人。
找回遗体的任务在无数种情境中上演。例如,在智利,几十年前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残暴统治期间,持不同政见的平民失踪,现在这些失踪者的年迈母亲仍然聚集在一起,要求:“哪怕给我们一根我们孩子的骨头。”有时,对遗体的要求跨越了国家或文化界限,代代相传。最近,西班牙当局将一位酋长的遗体送回了他的故乡博茨瓦纳,那是在一个多世纪前,这具遗体被掠夺者从新挖的坟墓中偷走,并被运到博物馆展出。1993年,日本为1597年入侵朝鲜事件进行了赔偿,归还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利品:2万个鼻子,从而解决了一项更长时间的争端。
人们很容易认为这种对找回遗体的普遍痴迷根植于人类内心深处以尊重的方式举行丧葬仪式的需要:用一首老蓝调歌曲的话来说,“确保我的坟墓保持干净。”但事实上,丧葬仪式在不同文化之间差异巨大。虽然大多数社会传统上是埋葬或火化死者,但东非马赛人等其他社会则将尸体丢弃给食腐动物。即使在埋葬死者的文化中,坟墓作为圣地的观念也并非必然共享。在19世纪的北欧,埋葬就像租公寓一样:坟墓会被间歇性地挖开,遗体被丢弃,以便为下一批租户腾出空间。虽然西方的死亡模式涉及悲伤和低声的尊重,但马拉维的尼亚丘萨人却有华丽的嘲讽逝者的葬礼仪式。
文化甚至在何时认定某人已死方面存在差异。有时,我们认为身体健在的人却被视为已故。在传统的海地社会中,如果一个人做了非常禁忌的事情,萨满会将这个恶棍变成一个奴隶般的僵尸;此后,社区相信他生活在死者的世界里。反之,有些社会继续与不再在世的人进行热烈、积极的交流。在新加坡的传统华人社会中,年幼的兄弟姐妹必须排队结婚,所以有时一个未婚去世的年长兄弟姐妹会通过“冥婚”与某个合适且已故的人订婚。即使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其他沉迷于找回死者的文化中,随着时间的足够流逝(以及逝者直系亲属的逝去),尊重行为反而会变成完全相反。尽管我们认为从库尔斯克号潜艇中打捞尸体是一种道德上的必然,但对泰坦尼克号上的任何骨骸做同样的事情则会被视为不恰当地打扰死者。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遗余力地去取回尸体呢?
最明显的原因是确保这个人真的死了。在大约185年前现代听诊器发明之前,确定一个人是死了还是只是昏迷通常很困难。有些人被活埋的事实导致17世纪的法律规定埋葬前必须有一段等待期;贵族们在遗嘱中规定,要对他们的尸体施加旨在唤醒未死者的身体侮辱,例如切断脚趾。到了19世纪,发明家们提供了带有逃生舱的棺材。在德国的停尸间,这些停尸间是埋葬前的中转站,尸体的手指被系在警报器上。以防万一。
许多非人灵长类动物在真正放开它们的死者之前也需要时间。这是我在自己对狒狒的研究中观察到的。一只幼崽死了,母亲没有丢弃尸体,而是在之后的几天里一直带着它。社会生物学家认为这种行为有一个进化的原因:偶尔有后代从昏迷中苏醒的雌性会传递更多自己的基因副本。
对于人类来说,找回遗体的愿望与我们投入否认的非理性能量交织在一起。从我们第一次蹒跚学步时在后院遇到一只死去的知更鸟,以及父母不舒服的“它只是睡着了”开始,西方对死亡的模式就是委婉和否认。正如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的里程碑式作品首次展示的那样,我们社会中的人倾向于以一系列刻板的阶段来应对死亡或绝症的消息:否认,通常随后是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如果幸运的话,还有接受。在委婉的死亡模式——爷爷只是去了医院就再也没有回来——的背景下,哀悼的过程被视为触底,以便摆脱否认阶段。因此,我们很多人都倾向于认为打开棺材,让我们能够看到亲人的脸,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必要性。为此,我们需要遗体。
有时,我们想要找回尸体是为了了解这个人是如何死亡的。这会带来巨大的慰藉:“他死得没有痛苦;他从未知道发生了什么。”对“如何”的探求涉及法医的可怕世界,在那里顺序就是一切:“当X完成时,她已经死了。”有时,慰藉来自于通过死者的死因了解一些关于他的事情:英勇的行为,肯定一个群体价值观的牺牲。诺曼·麦克莱恩在他的故事《大河恋》中写道了他那闹事兄弟的年轻被害。他被不明暴徒殴打致死,尸检显示他手上的小骨头都断了。因此,“像他之前的许多苏格兰牧师一样,[麦克莱恩的父亲]不得不从他的儿子是在搏斗中死去的信念中获得安慰。”同样,许多人得知9月11日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被劫持飞机上的乘客显然进行了英勇的搏斗时,感到松了一口气。
找回遗体的愿望有时也与我们认为死者的精神福祉有关。例如,阿拉斯加的特林吉特人认为,必须找回尸体才能转世。在苏丹的努巴人中,男人死后才受割礼,这是来世的先决条件。一场顶级的英格兰教会葬礼需要一具可以被祝祷并安息的尸体。有些文化不仅需要尸体,还需要尸体的所有部分。正统犹太人会保存牙齿、截肢的肢体和切除的阑尾以备最终埋葬;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以色列人会在恐怖爆炸现场梳理撕碎的肉体碎片。
想找回遗体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掌握遗体的人的精神或其他方面的福祉。在《坟墓事宜》这本令人惊讶地有趣的关于跨文化死亡方面的书中,人类学家奈杰尔·巴利写道:“死者并不拥有他们的尸体。”以遗体为核心的丧葬仪式,是一个分享、肯定、灌输和重振群体价值观的无与伦比的机会。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烈士葬礼可以激励潜在的十字军进入一种自我牺牲、杀戮的狂热状态。另一方面,巴利认为,很少有场景能像国葬那样,为政府提供一个展示权力和团结的机会。想想20世纪20年代无神论的苏联,看似奇怪地永久保存列宁遗体,就像某个斯拉夫圣徒一样。这是向俄罗斯农民传达的信息:“我们已经粉碎并取代了教会。”
葬礼的群体价值即使不是为了权贵也同样存在。想想我们如何悼念逝者。巨大的压力是赞美、颂扬和夸大逝者的善行。如果逝者是个无赖,或者悼词者是个不认识逝者的雇佣枪手,这有时甚至会涉及彻头彻尾的虚构。在我们的社会中,善行取自一个清单,其中大量包含忠诚、对年幼子女和年迈父母的奉献、虔诚、强健的职业道德和对烧烤的喜爱。在某种程度上,葬礼的具体仪式是对下一代的教训。被颂扬的价值观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服从工具,在我们许多人的耳边低语着“我希望被如何铭记?”这种超我。
因此,葬礼上会有压力,要让逝者看起来像个圣人。当葬礼是为了那个社会真正认为是圣人的人时,可要小心了。当霍梅尼在伊朗去世时,狂热的送葬人群是如此渴望触碰他们敬爱的阿亚图拉,以至于他们推翻了他的棺材,撕碎了他的殓衣。奈杰尔·巴利讲述了1231年图林根的伊丽莎白去世的故事,她显然注定要成为圣人,以至于一群人很快肢解了她的身体以获取圣物。更离奇的是11世纪圣罗穆亚德的故事,他晚年犯了一个错误,透露了要从他的翁布里亚小镇搬走的计划;当地人担心其他城镇最终会得到他身体的圣物,便密谋杀害了他。
尸体可以成为解决文化冲突的载体。去年一艘小型日本渔船被一艘海军潜艇意外击沉后,美国政府投入数百万美元打捞死者。一位宗教教授向官员们提供了在军事公报中使用的文化敏感措辞建议。尸体在黄昏后被打捞出水面,并按照佛教传统,双脚先进袋。
相反,有时尸体也可以成为一个社会表达对另一个社会敌对价值观的载体。有一个毛利人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在战斗中受重伤的男人,恳求他的战友们迅速砍下他的头颅并带着它撤退,以免它被敌人夺走、缩小并作为战利品展示。作为推论,回想一下索马里人群拖着美国阵亡士兵尸体穿过街道的画面所带来的强烈冲击。当扎伊尔的盗贼统治者蒙博托的独裁统治进入最后阶段时,据信他花时间挖掘祖先的骨骸,以免它们被叛军亵渎。同样,即使美国放弃巴拿马运河时没有立即的敌意威胁,尸体也从美国公墓中被挖出并运回国,就像微波炉和录像机一样。
在邦妮和米奇的案例中,我和我的同学们多年前就意识到他们永远不会回来了。但是因为我们从未找回他们的遗体,所以关于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以及那个最终打电话报警的人,总会有一丝不确定性。艾林·史密斯在沃特金斯格伦摇滚音乐节时24岁。在回家的路上,他搭上了一辆大众面包车的便车。车后座上坐着一对瘦弱的年轻情侣,也是从音乐节搭便车。史密斯和司机抽了一支大麻。那天很热,附近有条河。他们停下来,打算在水里凉快一下。当史密斯蹲下来脱鞋,犹豫着是否该进入湍急的水流时,他听到一声叫喊。他转过身,看到女孩已经掉进了河里。男孩——她的同伴——跳进去试图救她。然后他们俩都被急流冲走了,当时还活着。
这是史密斯告诉警察的故事。他们在货车里没有交换姓名,但他无意中听到两人谈论一个女孩工作过的夏令营,并回忆起了关于她衣服的识别细节。看来这对情侣就是邦妮和米奇。史密斯现在正与警方合作,试图找出他说他们失踪的那段河流。“我觉得他说的话可信,”纽约州警方的调查侦探罗伊·斯特里弗说。然而,那天有些事情没有发生。史密斯,一位体格健壮的海军老兵,没有试图营救邦妮和米奇。面包车的司机也没有。最终他们开车离开了。在下一个出口,史密斯下车,朝另一个方向走了。司机说他会从加油站匿名打电话报警,报告说那两个孩子被河水冲走了。警方没有接到电话的记录。
邦妮和米奇的父母不仅要承受失去孩子的痛苦,还要背负着可怕的不确定性。一位父亲和一位继父带着永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遗憾长眠于地下。我们其他人终于得到了困扰我们几十年的谜团的答案。
曾经,我们是相信自己永生不灭的孩子,会搭乘陌生人的便车。现在,我们通过欺骗我们的低胆固醇饮食来炫耀同样的非理性。曾经,我们尚未学会生命中会有无法控制的悲剧。现在,我们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孩子免受那种知识的困扰。曾经,我们失去了两个朋友,只能想象出华丽而暴力的罪行。现在,我们却得到了一个关于静默的疏忽之罪和冷漠之毒的平淡无奇的中年教训。
有时,当你找回尸体,或者至少知道整个故事时,你会学到一些关于生者和那些一直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人的关键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