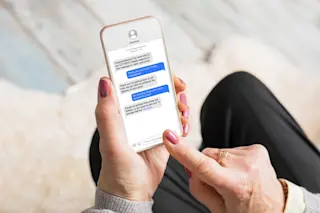在电视节目《钻石王老五》中,蕾切尔就昨晚的约会向其他参赛者撒谎。在《极速前进》中,乔纳森在妻子拖慢他们到达终点线的速度后推搡了她。在《飞黄腾达》中,玛丽亚攻击了韦斯,然后唐纳德·特朗普把他们两个都解雇了。
在短短几年内,100多档真人秀节目一直在努力帮助参赛者表现得像混蛋,观众们也乐此不疲。
当然,参赛者有时会结成高尚的联盟,偶尔也会萌生浪漫,但观众第二天在饮水机旁谈论的行为,无一例外都是参赛者恶意表现或因压力崩溃而让自己出糗。尽管很明显,参与者是故意被置于强制情境中的,但我们仍然认为我们正在看到一些关于人类同胞性格和心理的真实而值得注意的东西。
也许这种迷恋解释了为什么心理学领域的许多实验都像是真人秀节目的前提。想想最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63年发表的《服从行为研究》。在回复报纸广告后,志愿者(均为男性)来到耶鲁大学的一个实验室,一个穿着灰色实验服的男人请求他们帮助进行一项“学习实验”。受试者被指示,当隔壁房间的陌生人答错问题时,对其施加电击。电击最初很轻微,但每次答错后,实验者都会要求受试者施加更强的电压。随着电击以15伏的增量增加,隔壁房间陌生人的喊叫声变得更加痛苦。(电击不是真的;“陌生人”只是在表演。)如果受试者犹豫,实验服男子会严厉地说:“请继续。”如果受试者仍然犹豫,他首先会被告知:“实验要求你继续,”然后是,“你必须继续,”最后是,“你别无选择,你必须继续。”
当受试者施加他们认为是“非常强的电击”时,有些人已经汗流浃背、颤抖、结巴或咬嘴唇。最有趣的反应是,有些受试者出现无法控制的紧张性笑声,这本可以拍成精彩的电视节目。一位46岁的百科全书推销员因一阵阵笑声而无法自控,实验不得不停止,让他恢复过来。
米尔格拉姆的论文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报告说,大多数随机选择的男性都被说服按下标有“危险:严重电击”的开关,施加了据说420伏特的电击。米尔格拉姆感到惊讶的是,尽管“受试者从小就明白,违背他人意愿伤害他人是根本性的道德行为失范”,但大多数人仍愿意这样做。
米尔格拉姆受到启发,想弄明白二战纳粹死亡集中营的狱警为何心甘情愿地执行可怕的命令。这个问题今天仍然回荡,不仅在《幸存者》或《学徒》等电视节目中,也在新闻网络上,因为企业高管窃取数百万,恐怖分子斩首无辜者,以及阿富汗、伊拉克和古巴的战俘营守卫虐待囚犯。我们感到着迷、不安,并迫切想知道人类行为为何会如此偏离,我们担心自己也可能在类似情况下行为不端。
一个多世纪以来,心理学家们一直试图探究邪恶和错误的根源。他们所发现的并不令人鼓舞。米尔格拉姆和早期的研究人员表明,理性行为的能力可能被人群或权威人物的压力所颠覆。最近的研究表明,即使单独一人,人类也容易犯令人困惑的错误和偏见。
“基本上,社会心理学家的工作就是揭示人们是如何搞砸的,”布朗大学心理学副教授约阿希姆·克鲁格说。晚上,他曾被《幸存者》以及最近《学徒》中赤裸裸的野心和地位展示所吸引。然而,白天,他却坚信不端行为只是一半的故事。他认为,如果不首先理解人类为何经常做正确的事情,就无法理解邪恶和错误。如果他是正确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第一个世纪有一天可能会被比作医学的早期阶段,那时医生在不真正了解身体如何运作的情况下,通过像钻颅术这样的操作来寻找疾病的治疗方法。
最近,克鲁格和他的同事,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戴维·芬德,发表了一篇论文,呼吁重新定位该领域。他们认为,如果不加大努力审视人类如何做好事情,就会出现一种“扭曲的观点”,这种观点“对人性产生一种愤世嫉俗的看法”。另一位研究人员这样总结他们的论点:克鲁格和芬德要求研究人员放弃“人是愚蠢的社会心理学学派”。
克鲁格身材高大,说话轻声细语,带着德国口音。他的水泥砖办公室整洁朴素。一天下午,为了解释社会心理学为何如此痴迷于人类错误以及这种痴迷本身可能就是错误的,克鲁格开始从书架上取书,带我们回顾了这门科学的历史。
+++
社会心理学在19世纪围绕着对群体行为的关注而形成:为什么原本理性的人在人群中会变得非理性甚至危险?到了20世纪中叶,社会心理学家拓宽了研究范围,考察人们如何受到影响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或逾越道德底线。1950年代,社会心理学先驱所罗门·阿施让天真的受试者对抗一群陌生人,这些陌生人对线条的相对长度做出了奇怪的判断。在群体压力下,受试者往往无视明显的视觉证据,采纳了主流判断。
大约在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同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达利研究了旁观者在面对遇险的陌生人时,有时会选择走开或拉上窗帘的原因。受纽约市谋杀案受害者凯蒂·热诺维斯案的启发,她的求救声未能唤起邻居的行动,达利指出,如果受试者认为自己只是众多目击者之一,他们就越不可能帮助陌生人。
尽管有证据表明存在羊群行为,但许多研究人员仍然认为,个体在独立情况下可以被视为理性且有道德的。这种剧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源于经济学研究的见解。在一系列文章和书籍中,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驳斥了长期以来认为人类是市场中理性行为者的观念。他们认为,人类思维并非利用所有可用信息并计算出最佳决策,而是依赖“快速而粗略”的启发式方法,即心理捷径或经验法则来做出决策。
包括克鲁格在内的社会心理学家纷纷投入研究这些经验法则。由于这些法则并非总是理性,研究人员认为,在受试者被引导犯错的情况下,这些法则就会暴露出来。实际上,心理学家们开始寻找错误,以及能够促使这些错误发生的实验。
“和许多其他研究生一样,我觉得这些东西太酷了,”克鲁格拿着一本包含卡尼曼和特沃斯基部分著作的书说道。“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设计实验,展示错误和偏见,这些错误会告诉我们人类认知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真正发生的总是些不好的事情——偏离了某些研究人员对心智应如何运作的看法。”
克鲁格的兴趣在于刻板印象。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他发表了论文,展示了人们如何使用任意类别进行判断。例如,在炎热的八月天,人们期待九月的第一天,仿佛翻过日历就会突然让天气凉爽起来。克鲁格发现,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犯了两个错误:他们低估了月份内的温度变化(例如,假设八月会一直炎热),并高估了月底将发生的温度变化。
自那时起,关于人类误解和偏见的揭示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像雨后的蘑菇一样涌现。我们人类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认为自己比实际更聪明、更有技能、更有吸引力。例如,大多数司机都说他们开车比一般人更安全,尽管这在统计上是不可能的。人们也倾向于认为自己比别人说得更具吸引力。我们倾向于低估过去事件重演的可能性,比如连续赢两手扑克(“热手”谬误)。同样,我们错误地认为,篮球运动员既然投进了前五次投篮,那么第六次也能投进。我们高估了小的风险,比如被恐怖分子杀害,却低估了更大的风险,比如死于交通事故。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事后偏见”、“系统性扭曲效应”、“虚假独特性效应”、“公正世界偏见”、“判断混淆效应”和“外部代理错觉”。万一你认为自己已经很了解自己的偏见了,研究人员还揭示了“偏见盲点”,即你看到别人的偏见却忽视了自己身上的偏见。
+++
如果对这些研究照单全收,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当人们没有误判周围的世界时,他们正在对自己能力和动机撒谎。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人们被发现“不敏感”,被“无知”、“普遍的误解”以及一系列“缺点和偏见”所困扰。克鲁格记得社会心理学家之间有一场流行的辩论,讨论哪种比喻最能突出思维缺陷的深度:研究人员应该将思维视为“认知吝啬鬼”,强调我们有限的资源和对无关线索的依赖,还是更准确地将思维描绘成“极权主义自我”,以自欺欺人为代价追求自尊?你的思维是守财奴还是斯大林?
到了1990年代中期,克鲁格开始质疑在人类推理中寻找错误的价值。他的女儿当时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像许多父母一样,他被她的发展所吸引。“我被她思维日新月异的进步所震撼,”他回忆道。“我所欣赏的不是她的理性思考,而是她直觉、联想和自动化推理的发展。换句话说,我所欣赏的,正是社会心理学研究人员在研究成年人时发现错误的同一种思维方式。”
人类推理真的如此有缺陷吗?也许错误在于心理学家们试图解释它们的方式。克鲁格指出,人类思维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我们随性做出的快速判断,比如评估街上迎面而来的人是友善还是具有威胁性。另一种是我们全力以赴进行的活动,比如准备商业演示或解决数学问题。这种费力的推理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思维的黄金标准。这也是社会心理学家自己所采用的推理类型。然而,受试者通常被置于一种情境中,并被要求猜测、反应或估计。随后,研究人员通过统计或逻辑的视角,详细分析他们的行为。每当出现差异时,受试者就被认为是表现出错误或偏见,而不是研究人员。
克鲁格说,这些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研究人员在进行“零假设检验”。基本上,他们首先假设人类思维是理性的,然后寻找任何偏差。好的行为或理性的时刻被忽略,因为目的是研究坏的行为。这与真人秀节目并无二致:除非出现一些坏行为,否则研究就无从展示。
“我开始认为,通过将人类判断与客观现实进行比较,我们正在错失更大的图景,”克鲁格说。“我们记录错误,但却没有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行为或认知倾向,或者它们可能服务于什么普遍目的。我开始认为偏见和错误不可能是故事的结局。”
思想渴望相信善与恶行为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再看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人们会认为那些听从命令施加“电击”的受试者是懦夫,而那些拒绝的人是英雄。但设想一个不同的米尔格拉姆研究。如果,当受试者到达实验室时,他们看到窗户冒着浓烟,一个消防员告诉他们:“快,帮我把这条水管搬进这栋着火的建筑。”我们怎么看待在这种情况下服从权威的人?我们又会怎么看待那些拒绝的人?
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那些管理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士兵和那些解放集中营的士兵都听从上级的命令。他们所做的事情在道德含义上有着天壤之别,但人类服从权威的倾向却导致了邪恶和善良。克鲁格提出的挑战性问题是:如果科学家们考虑到服从的优势,他们难道不会对服从等心理机制了解得更多吗?我们难道不能通过研究好的行为来更多地了解坏的行为,或者至少在相同的背景下审视坏的和好的行为吗?
对一项特定经典错误研究的重新思考,对克鲁格的思想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在一项现已闻名的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的李·罗斯和同事们询问学生是否愿意穿着写有“Eat at Joe's”的夹心板在校园里走动。同意做这项令人尴尬任务的受试者预测,62%被要求背牌子的人会同意。但拒绝背牌子的受试者则认为,只有33%的人在被问到时会同意。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推理偏差,他们称之为“虚假共识效应”——即人们有一种天真地将自己的个人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投射到大多数人身上的倾向。
克鲁格对这项研究的批评印象深刻。克鲁格曾师从的教授罗宾·道斯反驳说,那些预测自己意见会是多数的学生根本没有犯错,而只是将自己的意见视为合法的数据。“根据定义,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属于多数,”克鲁格解释道。“因此,如果你认为你的意见会与大多数人相符,那么你正确的次数会多于错误的次数。”
克鲁格将这一思维更进一步,研究这种行为的个人和社会益处。通过这样做,他可能已经破解了“囚徒困境”,这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学都经典的实验。在囚徒困境中,你被要求想象自己独自一人被关在一个牢房里,一个看不见的同伴被隔离在另一个独立的牢房里。你们俩都被怀疑一起犯了罪,但警方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给你们定罪。如果你同意背叛你的同伴,作证指控他,而他选择保持沉默,你将被释放(零年);如果你们互相告发,你将受到接近最高刑罚的三年监禁。如果你保持沉默,你的同伴也保持沉默,你们都只会被判最短的刑期(一年),但如果你保持沉默而你的同伴背叛你,你将受到最重的惩罚——五年,这是傻瓜的结果。背叛还是沉默,哪种选择能让你获得最少的刑期?
+++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逻辑选择是背叛,因为你的潜在结果,取决于另一个囚犯怎么做,是零年或三年——平均而言比保持沉默(一年或五年)的后果更短。然而,当面临这个问题时,大多数普通人做出了不合逻辑的保持沉默的选择。为什么?
克鲁格认为,答案是他们正在使用社会投射:他们假设第二个囚犯会像他们一样行动,然后将这个假设纳入决策过程。按照这种推理,选择就变成了互相背叛(三年)或互相合作(一年)。合作就成了逻辑选择。
克鲁格理论中令人费解的部分是,参与者在自己决定如何行动之前,就假设其他人会像他们一样行动。人们不是先决定一种策略,然后假设别人会采取类似的行动。相反,他们先假设相似性,然后根据这个假设行动。克鲁格认为,这可能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做许多有社会意识的行为,比如花时间投票,即使我们知道我们个人的投票可能不会产生影响。人们会像我们一样行动的假设实际上影响了我们参与的决定。
“结果是,在那些人们将自己的信念投射到他人身上的群体中,合作水平更高,”克鲁格说。“集体利益是这种行为的副产品。在这个模型中,自私行为和为公共利益行为之间没有冲突。后者源于前者。”
一天晚上,我在布朗大学校园外与克鲁格交谈时,我向他询问邪恶。如果人类推理有所有这些迄今未知的积极方面,那么如何解释每晚新闻中的恐怖事件呢?社会心理学还有希望真正理解人类的不良行为吗?
我不是唯一一个好奇的人。明尼苏达大学发展心理学家迈克尔·马拉佐斯在评论克鲁格和芬德的论文时指出,米尔格拉姆实验真正令人不安的发现是服从和残忍的程度,“考虑到受试者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纵观历史,人们为了避免惩罚或获得地位而心甘情愿地做出了可怕的事情;马拉佐斯引用缠足、奴隶制和最近的公司丑闻作为例子。像马拉佐斯一样,从人们“基本上令人失望”的结论开始研究人类,难道不合理吗?
在道德问题上,克鲁格显得有些不自在。他曾赞赏地、几乎是渴望地谈论过关于视力的研究,在那里“好”与“坏”的问题并不适用。当研究人员找到一种方法来欺骗我们的视觉感知时,没有人会感到警觉。实验室中产生的视觉错觉被认为是揭示视力在现实世界中如何良好运作的机制。而人类互动科学并非如此。
“我并不是说人类行为是美好的,应该如此,”克鲁格最后说。“我的意思是,这个领域在追逐错误和偏见方面失去了平衡,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好的行为和坏的行为了解得都不够。你不了解好的行为,就无法了解坏的行为。”
我和克鲁格走着,我们的注意力被街对面吸引。一群高中生聚集在公交车站。突然,一阵急促的动作,几声叫喊,一个年轻人跳起来开始奔跑。我们站在那里,努力辨别发生了什么。那些声音是求救的吗?那个年轻人是在逃跑吗?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正处于一个社会心理学实验中。我瞥了一眼克鲁格,然后环顾四周。灌木丛中藏着摄像机或研究生,记录我的反应吗?
我们继续走着,但我略感不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吗?我们都认为没有什么可做的,但显然有人不这么认为:一辆警车很快鸣着警笛开了过来。晚饭时,我不断地向克鲁格提问。他对我们所看到的有什么印象?这种情况与旁观者干预的经典研究相比如何?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一个:我做得对吗?
“世界上发生在你身上的大多数事情都很快,”克鲁格说。
“幸运的是,我们快速而简单的推理从长远来看对我们很有帮助。生活是一个没有对照组的实验。你永远不会知道,如果情况稍有不同,你的行为会如何变化。这就是我们做实验的原因。有一点是肯定的: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研究都记在心里,并时刻鸟瞰自己的行为。你会崩溃的。”
我建议,或许可以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人类的不当行为,从中获得慰藉,甚至是一种解脱。“是的,”克鲁格说。“我认为下一波研究将把我们带到一个更加平衡和接受的境地。如果我们能对自己有一个更现实和准确的理解,我们或许就能更好地原谅自己和他人。”
当然,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将行为分类为正确、错误、善或恶。但理解行为和评判行为是两个不同的任务;前者是科学的,后者则不是。在理解方面,或许用好奇心而不是失望来对待我们自己会更有成效。
“我看着我的孩子们,”克鲁格说,“即使他们做了一些让我恼火的事情,我也会想,他们正在以他们应有的方式行动,作为高度进化的哺乳动物。有一位禅师说过类似‘人类是完美的,但他们可以稍作改进’的话。对于亚里士多德式思维来说,这个想法将是一个矛盾;它将是胡言乱语。对我来说,它有很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