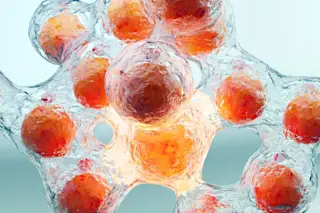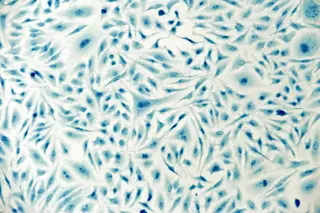去年六月的一个星期五早上,埃弗拉特·法迪达(Efrat Fadida)在她的白色夏装衬衫外面套了一件牛仔夹克,搭她父亲的车从以色列小镇格代拉向东前往耶路撒冷。这位25岁的姑娘走进哈达萨大学医学中心时,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高颧骨,方下巴,头皮像她出生那天一样光秃秃的。法迪达患有普秃(alopecia universalis),这是一种受基因影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可在任何年龄发作,导致全身毛发脱落。她来哈达萨是为了会见一支基因研究团队。
“我患这个病一年了,”法迪达告诉研究人员,她用简单明了的句子说话,并用手指在“病”这个词周围画上引号。“它一开始是小块秃斑。后来变得非常大,所以我决定剃光头。唯一困扰我的是我没有眉毛和睫毛。我已经学会了爱自己。”她没有说的是,她并非一直都如此坦然接受,尽管她的家族中还有另外四人患有同样的疾病。当法迪达的头发开始消失时,她对洗头变得小心翼翼。她担心男朋友会离开她。第一个月她不停地哭泣。如今,她与支持她的父母住在一起,不再和男朋友约会,并且对别人的反应保持警惕。“我化妆了,但我看起来仍然像个病人,”她说。“当人们看到我时,他们会自动认为我得了癌症。”
最近,遗传学家已开始发现可能导致法迪达疾病治疗方法的线索。他们的努力是更广泛地研究300多种已知遗传性脱发疾病的一部分,这些疾病从少数几十个家庭中发现的罕见疾病到影响数亿人的男性型脱发不等。所有这些疾病可能都共享一个共同点:毛囊复杂生长周期中的某个环节受到干扰。
当法迪达讲话时,小组中的一位科学家特别感兴趣地听着。安吉拉·克里斯蒂亚诺是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的分子遗传学家,她与法迪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要是因为她的头发。一头真正的秀发高高耸立在克里斯蒂亚诺的头顶,如瀑布般从她的肩膀倾泻而下,黑色和青铜色交织。她的头发精心染色和卷曲,更像是一件雕塑而非发型,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注意到她的第一件事。
尽管外表如此,克里斯蒂亚诺完全理解这位年轻以色列姑娘的感受。她于1996年被诊断出患有斑秃,这位遗传学家在症状最终消退之前,从她那华丽的鬃毛上掉了10大团头发。
从那时起,克里斯蒂亚诺已经破解了三种头发疾病的基因密码。现在她想确定导致法迪达脱发的突变,并通过这样做,找出导致她自己脱发的原因。

纽约州布赖尔克利夫庄园的建筑照明设计师西娅·查辛领导着美国斑秃基金会的威彻斯特资源和支持网络,该网络为脱发者组织讨论小组。“知识就是力量,”她说。| 杰西·切哈克
尽管她的两位亲戚以理发为生,但克里斯蒂亚诺家族中的一些女性却难以保留自己的头发。当她们进入更年期时,克里斯蒂亚诺的母亲和祖母都开始秃顶。她们在公共场合戴假发,并避开任何可能暴露她们身份的活动,比如游泳。与克里斯蒂亚诺的第二个表亲相比,她们的毛发还算浓密,她的表亲患有普秃,全身没有一根毛发。
然而,所有这些家族史都没有引导克里斯蒂亚诺进行她的研究。这发生在一次非凡的巧合中。她在1991年从罗格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开始了一项情感上令人痛苦的博士后研究:寻找大疱性表皮松解症(一种导致毁容甚至致命水疱的儿童疾病)的遗传基础。每隔几个月,克里斯蒂亚诺就会从纽约市洛克菲勒大学医院的孩子们那里采集血样,以分析他们的DNA。“这些孩子从头到脚都覆盖着像三度烧伤一样的水疱。他们必须不断地包扎。而且要取下这些绷带,你必须把孩子们浸泡在温水中,因为如果你只是取下纱布,就会把他们的皮肤撕下来。”
克里斯蒂亚诺感到无能为力,因为科学家们对这种疾病知之甚少。但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她分离出一个基因,然后又一个,再一个,直到与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相关的几个基因上的50多个突变被确定。她的研究不仅为有效的遗传咨询奠定了基础,她还开发了该疾病的第一个产前检测。那时她30岁。
功成名就后,她于1995年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任命。在新工作中,她被期望摆脱旧的博士后研究,成为一名具有新研究兴趣的独立科学家。在她的第一个学年里,她似乎漫无目的地旋转着。然后有一天,她去理发了。
那是1996年5月9日。克里斯蒂亚诺在她新泽西州梅特琴最喜欢的沙龙里,美容师随意地提到了一个小的秃斑:“怎么了?你后面是不是做了活检?”克里斯蒂亚诺以为她只是把头发扎得太紧了,但那天晚些时候她向一位同事寻求了第二意见。关上办公室门后,免疫学家莫妮卡·皮考克拨开了克里斯蒂亚诺的头发。当皮考克看到一个咖啡杯直径大小的秃斑时,她尖叫起来。“不小!”她喊道。
医生诊断出的问题是斑秃,这是一种基因决定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中人体的T细胞将毛囊细胞识别为外来入侵者并试图摧毁它们。健康的头皮毛发遵循一个错开的过程,经过三个阶段:生长期,可持续长达八年;退化期,持续两到三周;以及休止期,持续两到四个月,在此期间毛囊变弱,毛发脱落。这些时期在不同的人身上长度可能有所不同,但对于斑秃患者来说,一个区域的所有毛发会同时进入退化期和休止期,导致毛发一次性脱落。

九年前,当她失去所有头发时,查辛不知所措。她需要学习化妆和假发。“这不像出去买车或电视,”她说。现在她说她不总是戴头发。“今年夏天我是那个光头女孩。” | 杰西·切哈克
医生告诉克里斯蒂亚诺,唯一的治疗方法是在她的头皮上进行一系列痛苦的皮质醇衍生物注射,以减弱免疫细胞的攻击。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她又出现了九个秃斑。一个注射过皮质类固醇的斑块上的头发刚开始重新生长——起初像米粉一样没有颜色——另一个就会出现。
克里斯蒂亚诺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你每天早上醒来,在把头抬离枕头之前,你都会想,‘都在吗?没了吗?’然后你又为自己的虚荣而生气。你心想,‘我刚刚花了五年时间研究这些致命的皮肤病。我应该庆幸我只有这些。’但那没有用。”她决定,答案是全身心投入到弄清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
随着她了解得越多,她惊讶地发现,对于这种困扰500万美国人的疾病,人们知之甚少。她想知道,哪些基因负责正常的头发?在分子水平上,又是什么导致这些周期出错?
由于斑秃被认为是由不止一个变异基因引起的,克里斯蒂亚诺知道要破译它将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还需要近十年时间。相反,她决定寻找一种更简单的疾病形式,一种由单个基因调控的疾病。她知道要寻找什么:一个家族中有大量人患有极端脱发,但其他成员的头发完全正常。这种遗传模式将表明单个基因突变的强烈影响,并且很可能出现在通过表亲通婚而共享大量基因的家族中。
她在巴基斯坦的一个偏远地区找到了她正在寻找的东西。
在她的脱发被诊断出来不到两周后,克里斯蒂亚诺读到了一份关于旁遮普一个小村庄里一个家庭的临床报告。许多婴儿出生时有头发,但很快就脱落了,甚至包括他们的睫毛。这个问题似乎与更复杂的皮肤病无关:他们的牙齿很好。他们的指甲也很好。他们正常出汗。“这正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她说。
克里斯蒂亚诺给伊斯兰堡的研究人员寄了一封信,建议合作,并附上了她自己秃斑的照片。五个月后,30份血样寄到,随后是巴基斯坦研究员瓦西姆·艾哈迈德,他在纽约实验室待了两年。克里斯蒂亚诺和她的团队选择了其中几个样本,分析了DNA,然后将秃顶患者与头发正常生长的亲属进行了比较。她确定了8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区域,受影响的家庭成员在那里有明显不同的基因。
她欣喜若狂:“哦,天哪,这就像吸食海洛因一样。”但她离分离出基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简单来说:我们从整个美国缩小到了一个邮政编码。也许是一个县,”她说。在这个区域内,有数百个基因,其中很少有被绘制出来的。在进一步缩小范围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团队陷入了僵局。
一张年轻家庭成员的照片最终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通常,这个家庭遵循穆斯林的习俗,给婴儿剃头。一旦头发被剃掉,就再也没有长回来。然而,一位母亲没有剃女儿的头。艾哈迈德得到了这个女孩6岁时的照片。在脱发过程中,她的后脑勺保留了一圈头发,很像一个50岁的男性型脱发患者。
不久之后,克里斯蒂亚诺参加了皮肤病学研究协会会议上的一次讲座。她听说了一只小鼠,它的一个隐性基因发生了突变,被昵称为“无毛”(hairless)。幻灯片演示了这只小鼠的毛发在四天内如何从鼻子向尾巴迁移,直到动物几乎完全秃顶。当克里斯蒂亚诺观看这些幻灯片时,她意识到这种模式与那个年轻的巴基斯坦女孩的模式相似。她决定探究这只小鼠和女孩是否患有相同的疾病。由于小鼠和人类有许多相同的基因,克里斯蒂亚诺的实验室得以分离出人类版本的“无毛”基因。令所有人高兴的是,它位于8号染色体上。然后,团队比较了受影响患者和健康对照的DNA序列。果然,这个秃头的巴基斯坦家庭的“无毛”基因中含有一个突变。
“这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吕贝克大学皮肤病学教授、毛囊生物学专家拉尔夫·保斯说。匹配人类和啮齿动物的表型(可观察到的特征)以寻找人类突变,是毛发研究人员中的一个新颖想法。“临床医生一直困扰我们,问‘小鼠对人类毛发生长有什么启示?’”保斯说。“这证明了你用小鼠可以做到的事情,可以推广到人类情况。”
然而,克里斯蒂亚诺于1998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包含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错误命名。她使用了最初的巴基斯坦诊断,认为该家族患有先天性脱发的一种形式。结果发现,患者患的是一种更为罕见的疾病,称为毛发稀疏性丘疹(papular atrichia),这种疾病会破坏毛囊。保斯说,这使得她的发现“在生物学上引人入胜,但在临床上相关性有限”。
(全球只有大约30个有文献记载的家族患有丘疹性无毛症。)尽管如此,通过将人类“无毛”基因确定为调节毛囊细胞死亡的重要主开关——这一发现可能导致针对多余毛发增长的基因疗法——克里斯蒂亚诺成为了该领域一颗新星,而且是一位魅力四射的新星。
“她第一次演讲时,人们会想:‘这到底是谁?她是怎么进来的?’”保斯回忆道。“她那华丽的发型,没人会相信这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皮肤研究者之一。但她像前人一样,为毛发领域注入了活力。有些人对她的华丽有点措手不及。我只是喜欢它——如果你看看她的工作,没有人能与之竞争。”
当克里斯蒂亚诺从皮肤水疱研究转向毛发研究时,她在大疱性表皮松解症领域的一些同事想知道她的研究是否变得琐碎。“头发?”她记得他们问道,“你怎么能从研究这种危及生命的疾病转到头发?”但随着她的研究消息传开,克里斯蒂亚诺收到了大量来自各种毛发异常患者的来信。有些人写道他们从不离开家。另一些人则考虑过自杀。“我很沮丧、害怕,感到绝望,”一位头发所剩无几的中西部妇女写道,“我不知道如果我继续脱发,它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
费城拉萨尔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翰·鲁尼发现,女性如此珍视自己的头发,以至于在课堂练习中接受调查的大多数学生表示,即使出价100万美元,她们也不会剃光头。德克萨斯大学进化心理学家大卫·巴斯说,这种强烈情感依恋的根源很可能在于自然选择:“发质——丰盈度、质地、颜色,甚至长度——都是青春和健康的强烈相关指标。它们预示着高配偶价值。脱发则预示着配偶价值的丧失,因此在心理上令人不安。”
“直到那些信件开始涌入,我才意识到,尽管人们不会因此病而死去,但他们灵魂的一部分却死去了,”克里斯蒂亚诺说。
在她发现不久之后,克里斯蒂亚诺在哈佛大学演讲时,一位皮肤科医生走过来告诉她关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郊外山顶村庄阿切尔诺的两姐妹。这两个女孩出生时免疫系统受损。一个在她一岁生日左右去世了。另一个在五个月时接受了骨髓移植,使她得以存活到童年,但没有头皮毛发、眉毛或睫毛。“我认为这可能与裸鼠有关,”这位哈佛科学家建议道。带有所谓裸基因突变的小鼠胸腺(胸腔内的一个小器官,在抗感染T细胞成熟中起关键作用)没有完全发育。由于与胸腺无关的原因,这些啮齿动物的毛囊也不成熟,并且完全秃顶。
克里斯蒂亚诺联系了那不勒斯费德里科二世大学的克劳迪奥·皮尼亚塔,皮尼亚塔告诉她,阿切尔诺每年有少数儿童死于同样的免疫缺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儿童病情严重,死得很早,以至于他们的秃头症没有引起注意。皮尼亚塔将血液样本寄到了纽约。克里斯蒂亚诺的实验室发现,这对姐妹在17号染色体的相同区域存在一个共同突变,恰好在人类裸基因附近。更深入的分析证实了她的猜测,将裸基因与姐妹的疾病联系起来。皮尼亚塔现在根据意大利村庄中未来父母的血液检测提供基因咨询,该村庄每15名居民中就有一人携带该突变。
与此同时,更多的信件寄来了。克里斯蒂亚诺收到了一位得克萨斯州儿科医生的来信,这位巴基斯坦裔美国家庭的头发稀疏易断,有时还会卷曲在皮肤下,因为它们太脆弱,无法穿透表面。此时她已经建立了一个系统:找到一只具有相似表型的突变小鼠,然后看看人类患者是否在等位基因上也有突变。“这是我们的帽子戏法,”她想。但是当她用一个已知的突变测试一个候选小鼠时,这个戏法失败了。
沮丧之下,克里斯蒂亚诺向一位同事求助,同事建议她研究一种披针形小鼠,这种啮齿动物毛发稀疏、粗短,但没有发现突变。寻找这种小鼠奇怪毛发模式的来源花了五年时间。2002年,克里斯蒂亚诺实验室的一名学生在研究人类基因组计划数据库时,发现了一个未命名的区域,克里斯蒂亚诺曾预测人类版本的披针形基因会存在于此。事实证明,该基因在德克萨斯州家族和一些披针形小鼠中都严重突变。“这个花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克里斯蒂亚诺说,“但这只是因为我们必须等待基因组计划赶上并指引我们正确的方向。”
与高血压等在大多数患者中病程相似的疾病不同,毛发疾病有多种类型。虽然最常见的疾病是脱发,但有些人毛发却过多。克里斯蒂亚诺转而研究一种罕见的疾病,称为多毛症,患者有时被称为狼人。他们不是长出正常的面部毛发,而是在整个脸上长出浓密、有色素的头皮毛发,称为终毛。他们的外貌如此不同寻常,以至于一些多毛症患者在马戏团表演。这种综合征有不同的病因,但可以在家族中遗传,克里斯蒂亚诺怀疑它涉及一个单一基因。
研究多毛症的困难在于,患有遗传性多毛症的人很少。因此在过去的六年里,克里斯蒂亚诺一直在世界各地寻找研究对象。1998年,她在欧洲找到了两个家庭。然后,2001年,她飞往墨西哥蒙特雷,一位同事开车带她去了一个农村的露天诊所。在那里,她遇到一个具有奇特表型的家庭:那些毛发过多的人同时也是聋哑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羞耻之中,足不出户,不断剃毛。
与这个家庭见面,尤其是与一位叔叔和他的小侄子,深深触动了克里斯蒂亚诺。“这位叔叔简直美得惊人,”她说,“我的意思是,我从未见过一个人有那么多头发。家族中其他人并没有那么公开自己的疾病,但他对此非常自豪。他迫不及待地脱下衬衫,给我看他的胸部。”
“我们可以看出侄子把这位叔叔当作他未来生活的向导。反过来,叔叔把这个孩子视为自己的责任。他们甚至不互相使用手语。尽管他们无法互相发声或听到对方,但他们之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系。”
克里斯蒂亚诺采集了血样。她尚未发现任何基因线索,但如果她成功了,其影响可能是惊人的。多毛症是男性型秃发的镜像。对于秃发男性,普通的头皮毛发被绒毛取代,即细小的桃子绒毛。而对于多毛症患者,面部绒毛被头皮毛发取代。解开多毛症的秘密,不仅可能为毛发过多的人,也可能为一些毛发过少的人带来基因疗法。
克里斯蒂亚诺不是一个理论家。“虽然她是一名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但她总是寻找她的发现的临床相关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基因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哈尔·迪茨说。“她对患者群体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她总是寻求她的工作与疾病的产前诊断、家庭咨询以及开发新的合理治疗策略之间的相关性。”
克里斯蒂亚诺渴望与她的研究对象建立联系,正是这种渴望促使她于去年六月来到耶路撒冷。哈达萨大学医学中心拥有全球最大的遗传性毛发疾病患者群,其中包括约一半已记录的丘疹性无毛症病例,这是克里斯蒂亚诺与“无毛”基因关联的疾病。它还有许多斑秃患者,这种疾病引发了克里斯蒂亚诺自身的脱发,并且至今仍未解决。“这极其重要,不仅仅是看血液或DNA,还要看到这背后是活生生的人。而且他们正在受苦,”哈达萨皮肤科医生亚伯拉罕·兹洛托戈尔斯基说,他是克里斯蒂亚诺在以色列的主要合作者。“对于患者来说,看到有国际努力来寻找解决他们问题的办法非常重要。”像丘疹性无毛症这样的疾病有时被称为“孤儿病”,因为它们的发生频率不足以引起大量研究。“但对于患者来说,这不是孤儿病,”兹洛托戈尔斯基说,“这是他们100%的问题。”
当克里斯蒂亚诺那个星期五早上到达诊所时,候诊室里已经坐满了她熟知的DNA患者。几位丘疹性无毛症患者家庭从约旦河西岸和约旦赶来,不畏官僚主义和公路检查站,纯粹为了科学,因为这种疾病至今仍无治疗方法。走出电梯,这位遗传学家看到两名秃头的巴勒斯坦女孩,分别为3岁和8岁,她们和父亲从约旦河西岸赶来,是近亲结婚家庭中的表亲。她们的头上戴着头巾。这是克里斯蒂亚诺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无毛症患者。“哦,天哪,”她低声说,“她们真漂亮。”
接下来的五个小时里,哈达萨会议室里一片忙碌。病人前来接受检查。大多数秃头的人都戴着假发或头巾;他们的尴尬显而易见。兹洛托戈尔斯基指出了无毛症患者头皮、手肘和膝盖上的丘疹(微小的凸起)——这些微妙的表现在临床上有助于区分该病与自身免疫性普秃。问题和答案被翻译成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英语。午餐时间到了又过,长椭圆形会议桌中央的糕点消失了。
研究人员采集了血样和皮肤活检,并在废纸上绘制了家族谱系。普秃患者的眉毛被注射了类固醇,希望能刺激毛发生长。当兹洛托戈尔斯基为一名14岁的以色列女孩注射时——她握着秃头母亲的手,被针头刺得瑟缩了一下——克里斯蒂亚诺看着她,也跟着皱起了眉头。“这勾起了太多回忆,”她说。
“但你治愈了,对吧?”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哈达萨医生巴塞尔·萨阿德·埃丁问道。
“你永远不会被治愈,”克里斯蒂亚诺说。“你每天早上醒来都会觉得……”她的句子拖长了,然后她拍了拍自己的后脑勺。“太多回忆了,”她终于说道。
“在阿拉伯语中,有句谚语:如果发生危机,有时会造福他人,”这位巴勒斯坦医生说。他回顾了由克里斯蒂亚诺的疾病推动的国际努力——这项努力使科学家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找到斑秃及其更极端变体的基因基础。“也许,”他说,“你遇到这个问题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