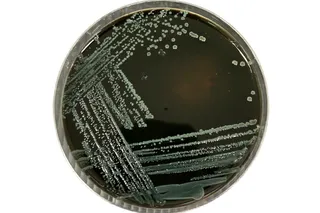他冲进我的急诊室,快步向我走来:一个高个子、肩膀方方的男人,怀里紧紧抱着他年幼的儿子。“这边走,”我说。“你没事,伙计;你没事。”这孩子看起来大约6岁,似乎没有受伤。
“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父亲开始说道,同时把儿子小心地放到担架上。“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人行道上玩。天色渐晚。他们说他从商店前面一个金属地下室送货门摔了下去。”
“他撞到头了吗?”我问道。“有没有失去意识?”
父亲似乎不确定,所以我转向男孩。“你滑倒了吗,朋友?你记得发生了什么吗?”
“我摔倒了,”他低声说。
“你撞到头了吗?肚子?”他的眼睛盯着父亲。他什么也没说。护士们给他脱了衣服。他的生命体征很出色:血压稳定在120/86,心率略高,为106。
“告诉医生有没有哪里疼,好吗?”男孩似乎有些迷糊,不知道自己是受伤了、大麻烦了,还是两者都有。他瘦骨嶙峋,皮肤近乎半透明——似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隐藏内伤。在听他肺部时,我注意到他肋骨上有个擦伤,但仅此而已。他模糊地指向左腹部,但当我按压那里时,没有反应。
母亲到了。她睁大眼睛,沉默着,亲吻了他的头。“所以哪里都不疼,对吗,伙计?”我又问了一遍。这只是单纯的岔气吗?男孩茫然地看着父母。他躺得太安静了。
擦伤在左下肋部,那里是脾脏所在的位置。儿童的肋骨比成人的肋骨弯曲度更大;它们倾向于传递而不是吸收冲击。我需要看清楚内部。我推过来一台超声波机,将探头放在男孩的左侧腹部。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明亮的弧形——膈肌。我向下倾斜,脾脏,灰白色、椭圆形,出现在了视野中。仔细扫描其轮廓,我没有看到黑色的液体,那是出血的迹象。一切都还好。最后一个标志:肾脏。
在这里,屏幕上充斥着一片黑白交织的混乱。什么——?我差点惊呼出来。快速扫描,我寻找着肾脏的轮廓。什么都没有。然而,在右侧腹部,它的另一半清晰地显现出来。“我不确定,”我含糊地告诉父母,“但肾脏可能出了问题。我们需要做CT扫描。”
他们倒吸一口凉气。
头顶的监视器显示血压稳定,但出血的儿童的血压不像成人那样逐渐下降。他们的血管系统会剧烈收缩以维持血压——直到突然,什么都没有了。
我和一名护士将男孩连接到便携式监视器上,并迅速将他推到急诊室的CT扫描室。“我知道这有点吓人,”我在将他放到扫描担架上时告诉他,“但我们会让你好起来的,好吗?”他点了点头。仍然是一个惜字如金的人。
扫描仪发出嗡嗡声。我凑在技术员旁边,看着显示器,第一张图像出现了。
“天哪,”我嘟囔着。超声检查并没有骗人。一个巨大的、黑暗的血块——一个血肿——从膈肌一直延伸到骨盆,似乎占了男孩总血容量的一半。一小块肾脏显现出来,其锯齿状的边缘显示出器官分裂的痕迹。
“肾脏上半部分骨折,”放射科医生喊道。“巨大的血肿。看起来还在出血。”一股恐惧攫住了我。
在过去的20年里,实质性器官损伤的管理已经得到了发展。以前的态度是,“疑则切之”。从那时起,创伤研究表明,观察并信任身体的凝血能力通常是安全的;凝血可以保护器官并避免手术可能带来的并发症。但这颗肾脏看起来已经报废了,而且出血仍在继续。为了止住大量的失血,可能需要进行肾切除术,即完全摘除肾脏。
我的当务之急是:我们没有儿科外科医生。
伯杰委员会——纽约州一项旨在削减医院过剩容量的倡议——最近关闭了我医院的儿科病房,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对儿童进行手术。现在,任何需要住院的儿童都由我们的儿科医生进行稳定,然后转送到纽约长老会医院。市区救护车会自动将受伤的儿童送往创伤中心,但我的病人是由他父亲送来的。如果他处于危急状态,我们的成人创伤外科医生会立即接手。然而,正常的血压意味着理论上我们有时间将他转送给儿科外科医生。但我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腹部血肿。血压会保持住吗?
我冲出控制室。“我们现在必须把他送上去。”妈妈听到了我的话,无力地靠在墙上。我责怪自己,抓起最近的电话,转向我的护士Pilar,说道:“告诉血库,我们现在需要两单位O型阴性血。”我们没有时间交叉配型他的血型。如果他的生命体征发生变化,O型阴性血——万能供血者——就必须输进去。
转运中心接通了电话。“我们的儿科转运团队在布朗克斯,”他们说。“他们什么时候有空?”我问道。
“三十分钟。”
我们医院有自己的救护车,但它受纽约市911系统的管辖。要调动一辆救护车进行转运,你需要拨打911调度员的电话,然后等待请求通过层层审批。我又拨通了电话。“托尼?”我说。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D医生?”托尼·苏亚雷斯是我们救护车主管。他只需要听到:“六岁男孩。肾脏破碎。需要十分钟前送上去。”“没问题,”他说。
医院白天有一支独立的救护车队负责转运病人。当时已过下班时间,但托尼叫来了这支队伍,让他们立刻上岗。Pilar带着两单位血下来了。里奇和诺曼,两位经验丰富的急救员,推着一辆担架走了进来:“我们要去哪儿,Dajer医生?”
“去市中心。”我向他们介绍了我的病人。“本市最勇敢的孩子。”父母每人抓住他的一只手。男孩盯着我们,仿佛在估量过山车的高度。
“别担心生命体征和静脉输液,”我告诉急救员。“Pilar会处理的,她也会一起去。我们走吧。”我不能让这个孩子离开我的视线。如果在途中他的血压下降,我将负责输血并抢救他。
“Dajer医生,你也去?”里奇吹了声口哨。“真是头一次。”
一只手拿着一单位O型阴性血,我坐到了前排座位。男孩和担架紧随其后。里奇走了进来,安装好血压监护仪。Pilar拿着输血管;父母挤了进来。“开吧,诺曼,”我大喊。
救护车驶出车道。三十秒后,我问里奇:“血压?”
“120/85,D医生。”很好,他的血压保持稳定。
我抱着他的头,问道:“怎么样,伙计?”
“还好,”他低声回答。我把手放在他的头上。当我们疾驰在FDR高速公路上时,城市的灯光似乎遥不可及。
“血压,里奇?”
“120/78。” “还有多久,诺曼?”
“五分钟。”
接着是一些转弯、颠簸,以及救护车通道。半打医生和护士围了上来。“最后血压,里奇?”我问道。他竖起了大拇指。“120/78。”
父亲用力握了握我的手;母亲的脸色恢复了血色。我最后一次抚摸了男孩的头发,说道:“随时可以再载你,大家伙。”
一周后,儿科主任打电话给我。“我们差点把他送进手术室。他损失了一半的血容量,但我们通过输血控制住了,而且肾脏自己停止了出血。令人惊讶的是,肾脏仍然能工作。”“哇,”我说。
“是啊。六岁有时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Tony Dajer是曼哈顿纽约市中心医院急诊医学系的系主任。生命体征中描述的案例属实,但姓名和某些细节已作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