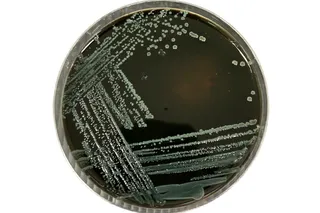我感觉到一股骚动在急诊室里蔓延。靠近入口处,一名戴着外科口罩、穿着睡衣的男子像被拴住的雪貂一样踱来踱去。已是凌晨2点,但一般来说,大多数病人不会穿着睡衣来急诊室。这个人有些不对劲。走上前去,我看到接待护士克劳迪娅正试图哄他坐到分诊椅上。他坐了一会儿,站起来,然后又瘫坐下去。
“我要见你们的专家,”他吐出一句。“我得快点做完。”
“做什么,先生?”克劳迪娅问道。
病人猛地站起来。“我感觉不到我的腿了。我无法呼吸。你们的专家在哪里?”
他的妻子平静地从挂号处走了过来。
“约翰四天前在楼上医院住院了,”她告诉我。“当时就像今晚一样,头痛、意识模糊,就这么开始了。”楼上做的腰椎穿刺显示白细胞计数很高,表明有感染,但所有的培养结果都是阴性的。约翰住在重症监护室,一夜之间就好转了——这让楼上医院的医护人员感到惊讶,他们诊断为病毒性脑膜炎。(脑膜炎是大脑和脊髓脑膜的炎症,通常由细菌或病毒引起;细菌性脑膜炎可能危及生命,但病毒性脑膜炎通常更像流感。)根据这个诊断,他们让约翰回家了。“但今晚睡前,他头痛,然后又醒来胡言乱语,”他妻子解释道。
现在我转向病人本人。约翰看起来大约40岁。他用一种空洞、激烈的眼神盯着我,让我想起吸了“天使尘”的人。那种令人不安的目光证实了我的第一印象:这位病人患有意识模糊,这是“大脑功能失调”的统称。这意味着他的大脑可能确实受到了病毒的侵袭,导致脑膜炎;炎症和引起他意识模糊的任何相关病毒可能已经自行消退。但无法解释为什么它会再次出现。楼上医院错过了什么?
我看了看约翰的生命体征。血压、脉搏、呼吸频率和体温都正常。这很有趣。病毒性脑膜炎通常会导致发烧和心率加快。
我又转向病人。“今晚怎么了,先生?”
“没事,亲爱的,”他妻子温柔地说。“这没什么比上次更糟了。”
“没有发烧、呕吐或新服用的药物吗?”我问道。
她摇了摇头。
“我不能待,”约翰急促地说。“我们得走了。”
“首先,我能确保你没事吗?”我恳求道。“如果你留下来会更好,”我用我最轻柔的“求你了别让我绑住你”的声音说。
“看?医生很好,”他妻子恳求道。
“我们把你安排到一个舒适的房间怎么样?”我提议道。“里面有电视。”
我的大一学生斯泰西出现了;她是自愿来的,认为在急诊室过夜很有趣。
我们一起把约翰送进了一个房间。我们必须快速行动;对于一个身体健康的病人来说,意识模糊需要进行头部CT扫描以排除出血和肿瘤,并进行腰椎穿刺检查脑膜炎和脑炎(大脑炎症)。
约翰仍然戴着外科口罩,不停地从房间里出来。
“你们要干什么?”他质问道。“我要专家。神经科医生!”
他妻子把手放在他胳膊上。他停止说话,平静了下来。我告诉他我们要进行检查,但考虑到他在楼上医院已经做了大量的检查,我怀疑这些检查会有什么结果。最安全的方法是直截了当:首先排除立即危及生命的情况,然后重新思考。
“好吧,”我告诉斯泰西。“进去获取更多细节:发烧?头痛?噩梦?旅行史?幻听?最奇怪的是他怎么会好转,然后又突然变糟。我指望你了,孩子。”
几分钟内,一切都很平静。然后斯泰西从房间里小跑出来。
“戴杰医生,他能喝水和服用布洛芬吗?他头痛。”
“当然,”我刚要说。然后我停了下来。
布洛芬?
在本杂志17年前的一期“生命体征”专栏中,传染病医生艾比盖尔·祖格描述了一位年轻女子反复患脑膜炎的困境。她在几个月内住院了四次,病人出现高烧、谵妄和颈部僵硬——这些都是危及生命的细菌性或败血性脑膜炎的迹象。CT扫描正常。腰椎穿刺显示脑脊液中白细胞计数很高——这通常是严重感染的预兆——但细菌和病毒培养均无生长。病人病情时好时坏。第四次,在众人的普遍翻白眼下,一名医学生被指派第无数次地询问该女子在生病前是否服用过任何东西。他得到了关键信息:布洛芬。
祖格的病人没有将非处方的日常布洛芬视为药物。它也以鲁芬或美林等品牌销售,其化学名称是布洛芬。这种药物无处不在,但在阅读祖格的文章之前,我并不知道它在极少数情况下会导致脑膜炎。
病历报告是诊断的生命线。医学教科书中枯燥、简化、有多少比例咳嗽和有多少比例发烧的列表会让你睡着。但好的故事会留下。医生们像交换棒球卡一样交易奇怪的诊断;我们从期刊、电视和朋友那里获取信息,为下次疑难诊断做准备。祖格的故事——即使在16年后——也让我能抓住一个小小的线索。
“布洛芬!”我喊道,对斯泰西说。“他今天来之前有没有吃过?”
“是的,他上床睡觉时吃的。三个小时前。”
“四天前呢?”
“我没问。”
“好吧,”我微笑着说,“我们问问吧。”
约翰又站起来了,依然眼神明亮而凝视,但似乎更清醒了。
“结果怎么样?”他质问道。“我需要交通回家。”他的妻子警惕地站在一旁。
“你还记得上次吃药了吗?”我问他。
“那天晚上他头痛。”妻子摸了摸嘴唇。“也许吃了一些布洛芬?”
我亮出了我的底牌。
“看,”我开始说,“我无法证明这一点,但我认为你所有的症状都是由布洛芬引起的。最好的证据是你是否在每次发作前都服用了一些。”
妻子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是的。他第一次肯定吃了一些。真的会是这样吗?”
“这还不完全清楚,”我说。“这可能是一种过敏性免疫反应。布洛芬可能与特定组织结合,如覆盖大脑的脑膜,并引发抗体攻击。大多数报告的病例发生在患有狼疮等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中。但也有一些发生在健康人身上。这可能与其他抗炎药,如泰诺(Aleve)等药物发生。除了意识模糊和脑膜刺激外,其标志性特点是停用布洛芬后会迅速好转。”
我转向斯泰西,微笑着说:“干得好,夏洛克。”
她脸红了。“谢谢。”
(不,我心想,感谢祖格医生。)
我告诉约翰:“我不会给你做扫描或穿刺的。”我抱起胳膊。“我认为你没事。”
“你确定吗?”他问道。
我有一个好转的病人,一个可靠的故事,一份最近阴性的检查报告,和一个非常聪明、细心的配偶。我觉得释放他是安全的。
“回家吧,”我冒险说。“好好睡一觉,我今天早上晚些时候会给你打电话。请你的神经科医生今天下午重新检查一切。不可协商的是:如果感觉任何事情变糟,请立即回来。”
约翰仍然半信半疑地问道:“我可以摘下口罩了吗?”
“是的,亲爱的,请吧,”他妻子叹了口气。
八小时后我们通了电话。
“我好多了,”约翰迟疑地说,仍然有些犹豫。“腿有点麻,但我能走了,头痛也消失了。”
“你有我的手机号,”我说。“有什么事随时打给我。”
一周后,他妻子打电话告诉我,一位神经科医生诊断约翰患有一种颞叶癫痫。这些症状可能导致怪异的行为,但没有“普通”强直性癫痫发作时的肌肉抽搐或意识丧失。
“他开始给约翰服用左乙拉西坦,”她讲述道,指的是一种强效抗惊厥药。“但它让他非常昏昏欲睡。”
约翰出院后的病情与我预测的差不多,可能有一些模糊的症状。而且癫痫的诊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病人病史。没有确凿的检查方法。虽然神经科医生尽最大努力根据模糊、非特异性的症状做出诊断,但我确信我的诊断是正确的。我决定直言不讳。
“听着,”我告诉他妻子,“每个专科都有其默认的诊断。癫痫几乎可以引起任何症状,但它们不会导致腰椎穿刺中出现白细胞。我真的认为约翰没事。归根结底是数据太少,而相互竞争的假设太多。”
她沉默了,然后终于说:“我不会再让他服用左乙拉西坦了。”一个月后,他一切安好。
在文献中,报道的布洛芬引起的脑膜炎病例不超过100例。但不得不怀疑,考虑到布洛芬几乎无处不在,有多少“病毒性脑膜炎”的误诊案例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