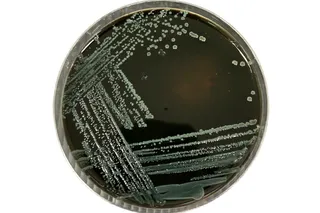克里斯托弗·普斯特还没有回到家,就注意到他左二头肌上有一个大约镍币大小的红点。结束了人生中难忘的非洲一个月的野生动物追踪之旅,他感到疲惫、酸痛、发热。这位50岁的股票经纪人想,也许是湿疹吧。他觉得过几天就会好起来。
但几天后,普斯特先生的情况变得更糟,发烧更高了。他手臂上的红点也变大了。他的内科医生出差了,于是他开车去了附近的一家医院。
“你在非洲用过疟疾药吗?”急诊室医生问道。
“是的,而且我出发前还打了疫苗,”普斯特先生说。为了去坦桑尼亚和卢旺达的旅行,他做了充分的准备:黄热病和伤寒疫苗、一种预防疟疾的奎宁类药物,以及一些止泻药。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虫咬,”医生沉思道,“但你的发烧很典型。听起来像是疟疾。我们先做个血液检查。”
一个小时后,他带着显微镜载玻片回来了。
“普斯特先生,”他表情严肃地说,“你的问题并非我所想。这是你的血涂片。我们医院无法为您提供治疗。他们正在大学医院等您,请您尽快赶过去。”
安迪·彼得斯是那天在大学医院急诊室值班的内科住院医师。他喜欢诊断传染病——越是罕见越好。当安迪扫过普斯特先生的血涂片时,他的下巴惊掉了。他原本以为会看到红细胞中细致的疟原虫环。取而代之的是,他看到了像鳗鱼一样自由游动的、鞭状的鞭毛虫。按显微镜标准来看,它们是巨大的鳗鱼——长度是患者血细胞的两倍。安迪查阅了关于另一种源自非洲的通过血液传播的寄生虫的描述:布氏锥虫(Trypanosoma brucei)。Bingo。完美匹配。
他走向病房,做了自我介绍,并解释了他的发现:昏睡病。
这时,克里斯托弗·普斯特决定立遗嘱。
东非昏睡病(感染普斯特先生的那种)的受害者常常迅速死亡。1906年,它至少夺走了乌干达600万人口中的一半。西非或冈比亚昏睡病则更为隐匿,是经典的昏睡病,会导致大脑慢性炎症,在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里引发癫痫、精神错乱、昏迷、昏睡和死亡。
但无论其地理亚型如何,非洲昏睡病的传播媒介始终是同一种:采采蝇。它比家蝇大一倍,拥有掠食性的口器和剪刀状的翅膀,在撒哈拉以南森林和灌木丛的阴暗潮湿角落繁殖。东非采采蝇从受感染的动物(通常是草原上的羚羊)或受感染的人类血液中获取锥虫。西非采采蝇则倾向于通过叮咬受感染的人类来获取寄生虫。在两个地区,寄生虫都会在苍蝇的胃中繁殖,然后迁移到唾液腺。一旦到达那里,一次叮咬就足以在另一只动物或人类身上引发新的感染。
疾病数周后,普斯特先生回忆起在非洲时曾拍打过一些“非常大的昆虫”。然而,当时他并不知道它们是采采蝇。在他的 wildest savanna dreams 中,他也无法想象这些寄生虫会在他体内发起怎样的战斗。
锥虫有一种狡猾的方式来对付身体的免疫防御。早在1910年,研究人员就注意到昏睡病患者血液中出现一波又一波的寄生虫。如今我们知道,每一波都代表着一种具有改变表面蛋白的新一代寄生虫。这件新外套会触发宿主产生新一轮的抗体。起初抗体有效,但最终它们会在另一批重组的寄生虫面前失效。
当普斯特先生抵达大学医院时,他血液中的战斗已经持续了好几周。寄生虫不仅充斥着他的血管,他还遭受着自己免疫系统的“友军火力”。他患有严重的贫血、血小板计数危险地低、肾功能障碍,以及一个松弛、发炎的心脏,所有这些都是由他自身的抗体攻击自身组织造成的。
昏睡病最令人恐惧的并发症是脑部感染。对普斯特先生脊髓液的检测将表明寄生虫是否已侵入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如果我们在那里发现了它们,我们让普斯特先生摆脱感染的唯一希望就是灭疟疾(melarsoprol),一种基于砷的寄生虫毒药,它也会杀死约百分之六的患者。
我们治疗昏睡病的方案非常有限,而且所有方案都有毒性。要选择正确的药物,我们必须确定寄生虫的具体菌株及其感染阶段。不用说,当我接到普斯特先生的电话时,我很担心。我是当地的热带医学专家,但我也不介意寻求帮助。
我首先打电话给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他们有一个24小时热线,处理像布氏锥虫(Trypanosoma brucei)这样的寄生虫危机。在得知普斯特先生的脊髓液没有问题后,值班医生推荐了苏拉明(suramin),另一种有毒的药物,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在使用。唯一的问题是,CDC是美国唯一的苏拉明供应点。这意味着它至少要到第二天才能送到普斯特先生那里。我们能等得起吗?在过去的12个小时里,他的发烧更高了,后续的血液检查显示寄生虫密密麻麻。无奈之下,我们冒险使用了医院药房中的一种抗寄生虫药物——喷他脒(pentamidine)。第二天下午,我们开始了苏拉明治疗。
接下来的几天很艰难。治疗几小时后,药物杀死寄生虫,将它们的残骸释放到血液中。这使得免疫系统过载。普斯特先生的血细胞计数骤降,心脏和肾脏状况恶化,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手臂上的咬伤变得巨大,边缘锯齿状,呈紫红色。我们的皮肤科医生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但两周后,患者战胜了病魔。现代医疗保健中我们理所当然的一切——技术、团队合作和药物——都为战胜感染做出了贡献。
如今,普斯特先生和我之间有着特殊的羁绊。毕竟,我不太可能很快再见到他这样的病例。在他抵达急诊室之前,美国十年间只见过寥寥数例发烧严重的昏睡病感染。普斯特先生反过来获得了教科书无法传授的热带医学视角。与许多患者相比,普斯特先生的护理是高科技的奢侈,是难以置信的奇迹。
在采采蝇的国度,连最基本医疗保健都匮乏,每年有成千上万人死于昏睡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