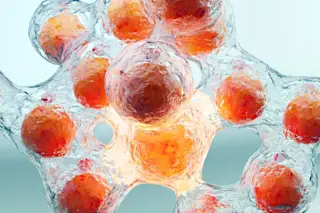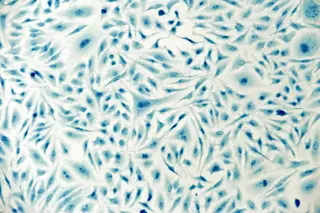现代科学的伟大革命之一,建立在一种怪诞的突变蠕虫的细长背部上。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在实验室中操作简单且廉价,三天内即可从卵发育为成虫,三天后可产下数百个后代。几乎所有蠕虫都是雌雄同体,既有雄性生殖器官也有雌性生殖器官,能够产生精子和卵子,因此每个生物都能自我受精。由于这种蠕虫是透明的,成虫只有 959 个细胞,因此在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并近乎完美地记录从卵到成虫的每个发育阶段,而蠕虫还活着,这是剑桥大学研究员、该领域的传奇人物西德尼·布伦纳(Sidney Brenner)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取得的成就。
由于其透明度、快速的繁殖周期和按指令变异的能力,秀丽隐杆线虫多年来一直是生物学实验室的最爱。只需对其进行辐照或向其培养皿中添加化学诱变剂,然后等待几天,即可观察到后代中会出现何种畸形蠕虫。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蠕虫讲座”(C. elegans 讲座的俗称)总是以对正常蠕虫发育的描述开始,然后转向讲师发现的任何引人入胜的突变体。
“一袋蠕虫”就是这样一种突变体。这种秀丽隐杆线虫版本有一个独特的悲惨遭遇,即无法产下它已受精的卵。它停留在蠕虫发育的最早期阶段,反复生成相同的幼虫细胞,却无法形成后期生命所需的器官和身体部位——包括排出卵子所需的阴门。结果是一个充满数十个后代的超大幼虫,因此得名。但它不会长时间保持这种状态。“卵在蠕虫体内孵化,幼虫会吃掉母亲并爬走,”马萨诸塞大学生物学家维克多·安布罗斯(Victor Ambros)解释道。
安布罗斯于 1979 年在罗伯特·霍尔维茨(Robert Horvitz)的一次讲座中首次听说“一袋蠕虫”,霍尔维茨曾在布伦纳的剑桥实验室研究秀丽隐杆线虫。当时,安布罗斯正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博士学位,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几个月后,他开始与霍尔维茨一起进行博士后研究,霍尔维茨建议他尝试识别导致“一袋蠕虫”这种怪异现象的缺陷基因。随后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这项断断续续的工作发展成了巴尔的摩现在所说的“一种全新的生物学”。
安布罗斯花了 13 年时间才从正常的秀丽隐杆线虫母亲身上鉴定并测序了产生“一袋蠕虫”突变体的缺陷基因;该突变基因位于蠕虫基因组的 2 号染色体上,被命名为 lin-4。事实证明,该基因并不编码蛋白质——当时所有基因都被认为如此——而是编码一小段 RNA,一种比 DNA 简单的分子表亲。该 RNA 分子的体积是编码典型蛋白质基因的百分之一,小到难以想象它会有任何功能,更不用说产生像“一袋蠕虫”这样引人注目的突变体了。
安布罗斯对那种奇异突变体的研究首次表明,RNA 可能比任何人想象的都重要得多,但直到 2001 年,完整的故事才开始展开。那时,研究终于说服科学家们,他们称之为“微小 RNA”的微小 RNA 片段正在调节人体内的细胞和遗传过程,并且是决定健康和疾病的关键因素。
关于基因作用方式的传统观点去年刚刚庆祝了它的 50 岁生日。正是在 1958 年,因双螺旋结构而闻名的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提出了“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可以用六个字概括:DNA 制造 RNA;RNA 制造蛋白质。
基因编码在染色体的 DNA 中。它们以大约 30 亿个核苷酸对的离散片段形式出现,这些核苷酸是构成双螺旋阶梯的遗传密码“字母”。受精的人类卵子以其基因组中的 DNA 开始生命,一半来自母亲,一半来自父亲。由此,一个拥有大约 10 万亿个细胞的完整人类被编程。根据中心法则,这发生在基因转录为 RNA,以及 RNA 转录为蛋白质的过程中。蛋白质反过来是生物学的“主力军”,它促进细胞内的化学反应,并控制基因本身的表达、转录和复制。
在这种观念中,RNA 是一种单链分子,与 DNA 的双链结构不同,它被视为次要角色,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菲利普·夏普 (Philip Sharp) 表示,“它有点像一种奴隶分子,以一种相当无趣的方式从 DNA 复制而来。”这种信念从未动摇,即使遗传学家意识到人类细胞中只有大约 2% 的 DNA 实际包含产生蛋白质的基因。其余大部分被认为是“垃圾 DNA”,这是日本遗传学家大野乾 (Susumu Ohno) 在 1972 年创造的术语,旨在表达我们大多数 DNA 实际上是无用的,是古老病毒或现已失效基因的残余。
随着安布罗斯发现微小RNA,一个惊人的认识随之而来:部分被认为是神秘垃圾DNA(近90%的DNA曾被如此分类)实际上被我们细胞中的机器转录成RNA片段,而这些片段是生命的基本控制者。这些微小RNA分子已被证实与心脏病和糖尿病有关;与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和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关;与长寿(至少在蠕虫中)有关;并与各种人类癌症,包括肺癌、乳腺癌、胃癌、前列腺癌、结肠癌、胰腺癌和脑癌的整个谱系有关。
“人们问我这些 RNA 会涉及哪些疾病,”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生物化学家、因其在 RNA 作为酶作用方面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的托马斯·切赫(Thomas Cech)说。“答案是百分之百——身体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百分之百。”这一见解要求我们对基因工作方式的传统认知进行根本性的修正。
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现在发现自己纳闷,他们怎么会在这么多年里错过了生命有机体如此基本的一个方面。毕竟,寻找微小 RNA 基因所需的技术自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经存在。一个答案是,他们没有特别的理由去寻找。“我们接受了蛋白质是生物系统中最精微的分子参与者的范式,”巴尔的摩说。“我们并没有强烈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缺失,而通常你需要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缺失才会去寻找它。”事实上,当安布罗斯发现第一个微小 RNA 时,他并没有刻意寻找。他有一个问题要解决——找到导致 lin-4 “一袋蠕虫”的基因——并且在其他研究人员可能已经放弃的情况下,他坚持不懈地思考这个问题。
另一个解释是,与其他非凡的科学发现一样,发现微小 RNA 需要天赋、环境和运气恰到好处的结合。安布罗斯在他的妻子、实验室技术员坎迪·李(Candy Lee)身上找到了完美的合作者。正如巴尔的摩(曾与他们二人共事)所描述的,他们遵循数据而非科学时尚;两人在实验室技术上都很熟练;而且“他们从未野心勃勃到妨碍现实的程度。”这并不是说他们缺乏做好科学研究的动力,而是“他们不担心科学的浮华,”巴尔的摩说。
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分子生物学家加里·鲁夫昆(Gary Ruvkun)也曾与安布罗斯和李共事。鲁夫昆说:“很多时候,你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遇到的人都有些拘谨。他们会说,‘这是我的小东西,我不希望别人来研究它。’而维克多则是‘嘿,咱们一起攻克这个!’有点天真烂漫。”
安布罗斯和李于 1972 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有机化学课上相识,当时安布罗斯是二年级学生,李是一年级学生。一年后他们开始约会,并于 1976 年李毕业那年结婚。他们都曾去麻省理工学院期望学习物理学,但安布罗斯转而学习生物学和遗传学,因为他认为这些领域更适合他的智力才能。他说,这些领域有其叙事,“而且没有你必须真正擅长的数学。”很快,李也开始从事生物学研究。由于作为实验室员工她将比作为研究生获得更多的报酬,她从未攻读高级学位,而是陆续在学术实验室(包括巴尔的摩的实验室)和生物技术行业担任技术员工作。最终,她去了安布罗斯的实验室工作——“家族生意”,她说道。
当安布罗斯于 1979 年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与霍尔维茨合作时,研究像 lin-4 突变体这样的蠕虫带有很高的失败风险。遗传学家通常更喜欢研究容易突变的基因,以便可以复制或改变工作,但在此之前,只有布伦纳的剑桥实验室在几年前观察到过一次 lin-4 突变。安布罗斯和他的同事们研究的突变体都是那个原始品系的后代。
安布罗斯在“蠕虫袋”上度过了第一年,试图在 lin-4 基因中产生另一个突变。当他失败后,他将注意力转向了参与秀丽隐杆线虫发育的其他基因。其中一个,名为 lin-14,具有令人困惑的相似名称,却拥有“逆转”lin-4 的有趣能力。这是关于 lin-4 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工作的第一个线索。无论 lin-4 如何作用产生“蠕虫袋”,突变的 lin-14 都可以通过做相反的事情来修复。安布罗斯发现,如果一条蠕虫在生命开始时带有 lin-4 突变,然后又在 lin-14 中获得了第二个突变,它的后代将看起来完全正常。lin-14 逆转 lin-4 效应的能力暗示这两个基因在控制发育中是耦合在一起的,并且一个基因的蛋白质产物调节另一个基因。
安布罗斯与鲁夫昆(当时是霍尔维茨实验室的另一位博士后)合作了两年,克隆了 lin-14 基因。1984 年,安布罗斯在哈佛大学创办了自己的实验室,带着 lin-4 项目,并将 lin-14 基因留给了鲁夫昆。(鲁夫昆随后在几个月后在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创办自己的实验室时,将 lin-14 项目带到了那里。)
与此同时,在哈佛,安布罗斯和李迎来了一位新的博士后,隆达·费恩鲍姆。他们的目标是使用经典的遗传技术,精确定位 lin-4 基因在蠕虫 DNA 上的位置,逐步缩小相关核苷酸的范围,直到只剩下基因本身。这个过程最终耗时四年。然而,在完成之前,安布罗斯为这个前景不明朗的项目付出了代价:他被哈佛拒绝了终身教职。他在生物系的同事认为他的工作兴趣不足以留住他。“那真是一个糟糕、黑暗的时期,”他说,“你的自尊心被彻底摧毁了。”
1992年,安布罗斯在纽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大学找到了一份工作。那时,李和费恩鲍姆已经意识到lin-4基因小得惊人。首先,两位研究人员将lin-4基因的可能位置缩小到一段700个核苷酸长的DNA序列,大约是典型蛋白质编码基因大小的三分之一。到1993年,他们已将该基因定位到一段仅70个核苷酸长的DNA,并确定这小段DNA编码了一段更小的RNA,长度仅为22个核苷酸。在他们意识到自己发现了什么之前,“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种schmutz,”安布罗斯用意第绪语的“污垢”一词说道。“我们认为这么小的东西不可能有任何意义……而且记住这个基因正在做什么:你把它移除后,整个动物的所有细胞都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幼虫阶段,这是一件真正普遍而深刻的事情。”
当李和费恩鲍姆在安布罗斯的实验室追踪 lin-4 DNA 时,鲁夫昆和他在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同事们已将他们的 lin-14 基因产物鉴定为典型的信使 RNA 片段,这种 RNA 促进蛋白质的构建。关键问题是这两个基因如何相互作用。安布罗斯和鲁夫昆通了电话,开始在各自的屏幕上读出序列,安布罗斯提供了由 lin-4 产生的 22 个核苷酸长的 RNA,鲁夫昆则提供了从 lin-14 转录的蛋白质编码 RNA。这两个序列完美匹配。在分子生物学的术语中,来自 lin-4 的微小 RNA 片段可以与 lin-14 信使 RNA “碱基配对”。安布罗斯和鲁夫昆毫不怀疑 lin-4 RNA 可以附着到从 lin-14 转录的 RNA 上,从而调节最终产生的蛋白质数量。其意义是深远的。RNA 不仅似乎充当了基因,而且它是一个直接受另一个 RNA 片段控制的基因。“它太完美了,一定是正确的,”鲁夫昆说。
1993 年 12 月,《细胞》杂志背靠背发表了安布罗斯关于 lin-4 的文章和鲁夫昆实验室关于 lin-14 的文章。回想起来,这两篇论文开启了 RNA 革命,改变了现代生物学的面貌。然而,当时它们实际上被忽视了。
鲁夫昆说,当时(和现在一样),研究人员最重要的是证明一个感兴趣的基因存在于不同物种——从线虫和果蝇到人类——的谱系中。如果一个基因很重要,进化就会保留它,同样的基因或其同源基因会在不同生物中反复发现。但到 1993 年,研究人员只对少数果蝇和人类基因进行了测序,lin-14 和 lin-4 都与它们不匹配。因此,当时人们的假设是这些基因并不那么重要。
“我读过那些论文,”菲尔·夏普说。“我认识这些人,但我对此什么也没做。我们都说这确实很有趣,但这只是蠕虫身上一个愚蠢的基因。这个基因重要吗?它只存在于蠕虫身上还是广泛存在?回答这些问题本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实验,但我并没有因此感到困惑。”
在接下来的七年里,世界上只有少数人,包括安布罗斯和鲁夫昆,继续探索在“蠕虫袋”中看到的这种奇怪 RNA 的调节能力是独一无二的怪异现象还是更普遍的存在。最终,鲁夫昆的研究人员偶然发现了秀丽隐杆线虫的另一个怪诞突变体,名为 let-7,它在最终幼虫阶段会“爆裂”(let-7 中的“let”代表“致命”)。当鲁夫昆的团队克隆出 let-7 基因时,他们意识到其产物仍然是一小段 RNA,这次只有 21 个核苷酸长。显然,lin-4 RNA 基因并非孤例。
到 1999 年,当 Ruvkun 实验室完成 let-7 测序时,人类和果蝇基因组的很大一部分已被绘制出来。现在 Ruvkun 可以在人类和果蝇中寻找 let-7 的版本——他在两者中都找到了。“然后我写信给世界各地研究奇异生物的人,我问,它存在于软体动物中吗?它存在于海葵中吗?它存在于海绵中吗?我们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Fed-Ex 包裹。我们可以快速进行实验——砰——它就在那里。”发现 let-7 基因的正常版本在各种生物中都保守存在,这表明它在所有这些生物中都具有功能并发挥着某种有益的作用。尽管研究人员仍在努力确切了解它的作用,但有些人认为,至少在人类中,它可能控制细胞的生长。2000 年,Ruvkun 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两篇里程碑式的论文。第一篇[pdf]报告称 let-7 编码了 21 个核苷酸的微小 RNA。第二篇[pdf],九个月后,揭示了他的实验室已在“来自各种动物物种的样本中”检测到 let-7 RNA。
一个短小的 RNA 基因(现已被称为 microRNA)可以被视为偶然。有了两个,其中一个遍布整个动物界,研究人员开始关注。“那是我生命中花 10 分钟彻底重组宇宙观的时刻之一,”安布罗斯说。“我们立刻就知道有许多 microRNA,它们必须存在于所有动物中。想象一下,经过 5 亿年的进化,let-7 是唯一的 microRNA,这太疯狂了。”
2001 年,受这些非凡发现的吸引,三个团队竞相发现他们猜测的大量微小 RNA。其中一个小组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巴特尔(David Bartel)领导;另一个小组在德国,由刚刚完成夏普博士后研究的汤姆·图什尔(Tom Tuschl)领导。第三个小组当然是安布罗斯和李,尽管他们起步较早,但资源却比其他人少得多。他们仍在达特茅斯,招募了他们的三个儿子中的第二个,当时是一名高中新生,来做他们的计算机编程。
所有三个实验室都使用了图什尔开发的一种技术来克隆小型 RNA 分子,他们的研究结果——总共 103 个新的微小 RNA 基因——于 2001 年 10 月同时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图什尔从果蝇胚胎中鉴定出 14 个微小 RNA,从人类癌细胞系中鉴定出 19 个。巴特尔从秀丽隐杆线虫中鉴定出 55 个,安布罗斯和李则鉴定出 15 个。所有三个团队都意识到,这些可能只是这些物种基因组中隐藏的所有微小 RNA 的一小部分。可能还有数千个。
一年后,现任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癌症遗传学项目主任的卡洛·克罗切(Carlo Croce)报告称,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这种疾病最常见的形式,是由两个微小 RNA 基因缺失引起的。这一发现是顽强侦查的结果:克罗切花了七年时间寻找导致 CLL 的基因。在大约 70% 的病例中,他发现某个染色体的特定区域存在错位,但起初他找不到任何负责的蛋白质编码基因。一旦新的微小 RNA 基因被鉴定出来,结果发现其中两个映射到该染色体区域。认识到微小 RNA 基因突变可能导致一种常见形式的癌症是“一个启示”,克罗切说。“这表明一类全新的基因可能在该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
很快,其他研究人员开始发现微小 RNA 与癌症之间更多的联系,微小 RNA 研究开始通过医学和生物学传播——用大卫·巴尔的摩的话来说,就像“实验室里的一种感染”。例如,在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和布罗德研究所,癌症遗传学专家托德·戈卢布(Todd Golub)花了十年时间学习如何通过癌细胞中表达的蛋白质编码信使 RNA 模式来识别恶性肿瘤。这项技术可以捕捉疾病的分子指纹,可用于定制治疗方案,以最佳地对抗患者特定类型的癌症。戈卢布对微小 RNA 研究关注甚少,直到 2004 年初,霍尔维茨打电话建议他们合作。
起初,戈卢布对 microRNA 可能在癌症中发挥作用持怀疑态度,但证据很快消除了他的疑虑。“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东西在不同肿瘤中大量、动态地表达,”他说。简而言之,一种肿瘤中开启的 microRNA 基因模式与另一种肿瘤中的模式完全不同,也与健康细胞中观察到的模式完全不同。“在人类基因组中,很难找到一个 microRNA 不会在不同组织的各种肿瘤类型中差异性地开启或关闭,”戈卢布说。事实上,正如他和他的同事们继续报告的那样,迄今为止已识别的 217 个 microRNA 在肿瘤分类方面的效果可能比已用于诊断的 20,000 个蛋白质编码 RNA 更有效。
微小 RNA 不仅被证明对识别不同类型的癌症有用,而且对指明潜在的新治疗方法也很有用。事实上,戈卢布发现许多微小 RNA 在癌症中(无论癌症类型如何)的活性都低于健康组织。在与麻省理工学院的泰勒·杰克斯(Tyler Jacks)的后续合作中,戈卢布问道:“如果我能关闭肿瘤细胞中的微小 RNA,细胞会介意吗?明确的观察结果是肿瘤会变大。”相反的操作——增加微小 RNA 的活性——可以缩小肿瘤。一旦该机制得到利用,癌症的治疗方法可能就会出现。
现在看来,通过增加或减少微小 RNA 的活性来微调蛋白质的产生,可能会带来针对各种疾病的疗法。在新的生物学模型中,蛋白质仍然承担着催化反应和开启或关闭基因的繁重工作,但微小 RNA 调节蛋白质的数量,从而调节每个特定任务的完成程度。至少,其结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细胞信号网络,它们不断地协同工作(或者根据情况相互对立)来调整细胞中表达的蛋白质的数量和类型,从而最终影响细胞本身的健康。无处不在的微小 RNA 调控云相当于一个前瞻性的反馈系统。每当一个基因被开启并开始转录以制造蛋白质时,它也可能产生一个或多个微小 RNA,这些微小 RNA 反过来会在整个细胞中引发一系列同步的调整或变化。
影响是巨大的。任何尚未查明遗传成分的疾病——包括阿尔茨海默病、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肥胖症、心脏病和糖尿病在内的长长清单——都可能通过调整编码微小RNA的基因来治疗,至少部分如此。现在,每当研究人员自问微小RNA是否可能在特定疾病或健康问题中发挥作用时,答案几乎总是肯定的,因为微小RNA似乎无处不在,是器官基本健康的一部分,对我们原以为已经了解的生化级联反应至关重要。
以肌球蛋白为例,它是心肌中的主要蛋白质,根据德克萨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埃里克·奥尔森(Eric Olson)的说法,几十年来它一直是“肌肉生物学中研究最多的蛋白质”,奥尔森研究微小 RNA 在心脏组织和心力衰竭中的作用。“我们以为我们对肌球蛋白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它是如何工作的,它是如何使肌肉收缩的,”他说。“但一直以来,肌球蛋白都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它的一个内含子中隐藏着一个微小 RNA,”内含子是 DNA 中不编码蛋白质的区域。“而那个微小 RNA 调节着肌肉的许多基本特性。它控制着心脏对损伤的反应能力以及对甲状腺激素的反应能力,甲状腺激素是心脏功能的主要调节剂。所以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肌球蛋白是为了使肌肉收缩。事实上,它通过编码这个微小 RNA 在肌肉生物学中扮演着更深更广的角色。”
奥尔森和他的同事们现在正在不同形式的心脏病中发现不同的 microRNA 模式,并将心脏病的进展追溯到 microRNA 的渐进变化。他们已经培育出通过从基因组中移除单个 microRNA 基因而免受心力衰竭影响的小鼠;他们还通过基因工程使其过表达特定 microRNA 基因,从而培育出特别容易患心力衰竭的小鼠。鉴于所有这些,microRNA 显然是药物开发的目标,甚至可能本身就可用作药物。“现在我们知道单个 microRNA 调节心脏病的许多方面,”奥尔森说。“所以我们可以制定策略来调节或抑制那些病理性 RNA。”
RNA 革命的走向——除了无处不在之外——几乎无法预测。启示以惊人的速度涌现,研究人员将其描述为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望而生畏。安布罗斯和李最近将他们的实验室搬到了伍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他们对涌入他们这个曾经是科学“死水区”的领域的人才数量和质量感到惊叹。他们还报告说,发现自己处于游戏巅峰的感觉是超现实的。
“在科学界,你总有一些钦佩的人,比如菲尔·夏普和大卫·巴尔的摩,”安布罗斯说。“我的抱负是,有一天,在我职业生涯的后期,他们或许会注意到我的工作,或许会说,‘维克多,干得好。’”夏普和巴尔的摩两人都将在安布罗斯自己开创的领域工作,“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令人无比欣喜。”
微小 RNA 的作用
微小 RNA 基因的长度仅为典型基因的百分之一。典型基因编码信使 RNA。信使 RNA 反过来指导蛋白质的组装。最近,科学家们发现微小 RNA 基因可以通过编码与信使 RNA 结合的微小 RNA 片段来控制这一基本过程,从而有效地关闭蛋白质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