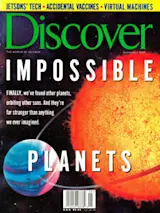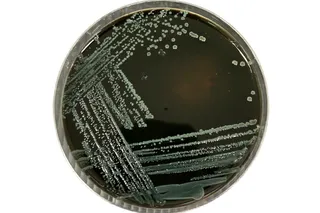约翰·西蒙(John Simon)是一家知名健康保险公司的商业高管。在一次关于医疗管理研讨会上,他打了个喷嚏,然后从椅子上滑落到地板上。他看到的第一张脸是他旁边的那个女人。
“怎么了?”他问道,但说出这些话时,他对自己声音和话语都感到陌生。他抬起手,但当他这样做时,他的手似乎消失了。人们围了上来。他们都在说话,但声音却像是从远处传来。有人不停地说:“911,911,911。”也许是他自己在说。一张张脸出现又消失,但那个女人一直都在。他努力思考。她告诉过他她曾是一名护士;现在她是一名律师。此刻她俯身在他上方,看起来非常像一名护士。午餐时他们还谈论了合同。她叫什么名字?他短暂地看到了他妻子和她站在一起,这很奇怪,因为这是一个商务研讨会。他也记不起他妻子的名字了。
两名年轻的制服人员过来照顾他。起初他以为他们是警察,但后来意识到他们是急救员。他们拿出设备,给他接上监护仪导联和氧气,这太荒谬了。看看这个:现在他们竟然在试图测量他的血压。
“是什么?我怎么了?”他问道。
“先生,我认为您可能中风了。”
“这太荒谬了,”他心想。“我才37岁。”他试图坐起来,但做不到。他感觉自己像在溺水。
他们坐上救护车,拐弯抹角地行驶着,他觉得这很有趣;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在濒死。然后他意识到这并不好笑。过了一会儿,救护车车门打开,他被推入医院。人们跟着担架一路小跑。除了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女人,其他人都穿着绿色手术服。她留着深色头发,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她一定是医生,他想。女人当医生了,男人当护士了,护士当律师了。有一会儿,他感觉自己漂浮了起来,被一群手托着抬到了床上。然后,那位医生俯身过来,问了他一些问题。他叫什么名字?他多大了?
那位医生就是我。
快速检查。血压 160/90,脉搏 88,呼吸平稳。自发睁眼。先生,先生!他叫什么名字?西蒙先生,我是您的医生。瞳孔等大且对光有反应。心音正常。先生,握住我的手。用您的右手握住。好。现在用您的左手握住。握住您的左手……
没有反应。这位37岁、身体健康的男性出现了突发的神经系统事件——很可能是中风。
接待处的工作人员拿着笔和纸站着。先生,您生日是什么时候?您有保险卡吗?您的医生是谁?她站在那里问着一些对于危重病人早期护理来说其实并不重要的问题。但不幸的是,当某人中风时,除了体检本身,几乎没有多少护理可以干预。除了输氧、控制血压和纠正偶发问题外,医生几乎无事可做,只能等待,看看中风症状是好转还是恶化。至少过去是这样。现在可能有一种新疗法,而这,对我来说,更是个难题。
我读过一些引人注目的报道,说一种用于治疗心脏病的溶栓药物可以用于治疗某些中风患者,从而显著降低他们遭受严重残疾的风险。这确实很棒,但我持怀疑态度。我了解到一些最近的研究表明,在某些情况下,溶栓药物可能会使中风恶化。事实上,只有一项研究显示了溶栓药物的明确益处——即使那样也仅限于症状出现后三小时内接受治疗的患者。因此,我心存疑虑,这些疑虑让我对如何治疗西蒙先生感到不安。
中风是大脑心脏病发作的版本。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由脑血管中的血栓引起。另一种是由脑血管破裂、血液渗入脑组织引起。两者都会扰乱大脑的氧气供应,常常导致永久性脑损伤。溶栓药物只能对血栓引起的中风有效。如果中风是由于出血引起的,药物可能会使出血加剧,将轻度中风变成灾难性的。
如何判断中风是出血还是血栓引起的?通过 CT 扫描,这是彻底改变脑成像的放射学检查。最大的问题是时间。在某些机构,脑部 CT 扫描可以在 15 到 20 分钟内完成。在另一些机构,可能需要两个小时。但研究表明,如果溶栓药物要起作用,必须尽早使用。许多中风患者到达医院时,症状已经出现数小时,为时已晚,无法开始用药。西蒙先生很幸运。他到达时,症状才刚刚出现几分钟。如果有人能从药物中获益,那将是他——也就是说,如果他有血栓。
西蒙先生的检查显示左侧面部下垂,左手完全瘫痪,左腿明显无力。当我用反射锤敲击他脚底时,我抬起头,看到两位护士推着一张载有一位老年妇女的病床。我一小时前已经给她安排了 CT 扫描。
“停!”我喊道。“他先来。”
我坐在了推车的前座,和护士们一起推着输液架,浩浩荡荡地走向扫描室。我坐在 CT 技术员后面,看着大脑核心的图像在屏幕上结晶又消融。那里是大自然美丽的图案——脑沟、大脑、丘脑、镰。我曾经费尽心思在学校里死记硬背的那些结构,现在都轻松地呈现在我眼前。
只用了几分钟。我看到约翰·西蒙的 CT 扫描结果是正常的。
这显然不意味着他的大脑是正常的。由血栓引起的中风患者,CT 扫描通常在数小时后才能显示异常。然而,出血通常会立即显现。约翰·西蒙似乎是血栓引起的中风。
我给值班的神经科医生留了言;我确信他会建议我使用溶栓药物。但我仍然担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适得其反。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齐默尔医生回了电话。
“一个正常人,”我说。“没有病史。他在一个会议上,然后打了个喷嚏……”
“打了喷嚏?”
“打了喷嚏。”
“夹层。”
“什么?”
“我认为可能是夹层。”
这很有道理。夹层是血管内壁上的一个微小撕裂;它会严重损害血流,而不会导致血管外出血。夹层很罕见,但那一喷嚏通过暂时增加西蒙先生脑内压力,可能会导致夹层。用溶栓药物治疗夹层可能会弊大于利。
“另一方面,”他补充道,“也可能是血栓。唯一能确切知道的方法是做血管造影。”
血管造影是通过向脑动脉注射造影剂进行的;造影剂让我们能够追踪血流,并实际看到是否存在血栓或夹层。这比 CT 扫描要困难得多,而且由于是侵入性的,也更危险一些。但我工作的医院没有先进的设备和经验丰富的医务人员来做血管造影。
“试试大学医院,”齐默尔医生说。“脑卒中团队。”
大学医院是当地两家宣传最新中风治疗方法的医疗中心之一。
我挂了电话,拨通了大学医院的寻呼台,要求与脑卒中团队通话。达什医生立刻接了电话。我只说了几句话,她就接手了病例。
“我们现在就准备血管造影室。快送他过来——时间非常关键。”她挂了电话,我听到她说道:“直升机在哪儿?”
“出去了,”我听到有人喊道。
“我们医院有危重症转运团队,Lifeline。”轮到我俯身问接待员了。
“Lifeline?”我问玛丽。
“出去了,”她说。“今天只有一辆车。”
“医院裁员。”
她举起一根手指,说道:“让我看看我能做什么。”
“医生。”急诊科护士长琳恩走到柜台前。“你为什么不来看看这个病人?”
我跑向西蒙先生的房间。他看起来更糟了。现在他完全无法移动他的左腿。我用笔尖在他的脚底划了一下,他的脚趾张开了,大脚趾向外拱起。这不是个好兆头。他正在失去更多的运动控制。
他妻子到了。我试图向她解释发生了什么,但她几乎歇斯底里。“拜托,医生,”她说,“拜托救救他。”
我说我想把他转到大学医院。他们有一个专家团队,也许能用我们无法使用的疗法治疗他。也许,我对自己说,也许,也许。他们可以做血管造影……我犹豫是否要向这位焦躁不安的女人解释血管造影。
有人拍了拍我的胳膊。是我的病人用右手戳了我一下。连那只手现在似乎也无力了。他想说话但放弃了;他的言语含糊不清。他举起手,摆出了一个熟悉的 OK 手势——同意转院。
玛丽探身进来,宣布她联系上了转运团队——一个知道如何驾驶救护车的人员,还有护士长琳恩。现在距离西蒙先生晕倒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35分钟。我只能祈祷救护车一路平安,对方能迅速响应。
就在他们正要离开病房时,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达什医生,”玛丽告诉我。
我拿起电话。“我们正在装车,”我说。“他很快就会到的。”
“不,你们必须停下。”
“停?为什么?”
“我们的临床协调员联系了你们的注册登记员。你不能把他转到这里来。这个人买了错误的保险。”
“什么?”
“错误的保险。你从来没有查过他的保险状况。我们不接受他的保险。你从来没有查过。”
“这是我最不担心的事情。”
“听着。把他送到基金会医院。他们有一个脑卒中团队,我认为他们可能正在接收病人。”
“但那会让我们再耽误一个小时。听着,你们接受了他,而且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勃然大怒,无助地看着所有节省的时间付诸东流。基金会医院甚至可能不接受他。
“他们会接受的,”她说。“我很有把握。”
“但我刚告诉他和他的妻子,大学医院是全市治疗中风的最佳选择。现在你想让我告诉他们我把他送往全市另一家最佳选择的中风医院。”
“他妻子在吗?我来解释。”
团队推着病人,他身上缠满了来自便携式监视器、氧气管和静脉输液管的电线,走进了走廊。“停!”我喊道,双手举过头顶。
“怎么了?”琳恩问道。所有人都停了下来,看着我。“怎么了?怎么了?”
我招手叫他妻子过来。她看起来比病人还糟糕,如果可能的话。我把听筒递给她,让她和医生说话。我走到琳恩身边。“他买了错误的保险,”我低声说。“他们想让我们把他送到基金会医院。”
我们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我看向他妻子。她的手垂了下来,听筒离耳朵很远。她显然无法做出决定。我站在那里片刻,心想:这不可能。然后我跑过去,从她手中夺过电话。
“我们已经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你们已经接受了他。他要来你们这里!讨论结束。”
达什医生听起来几乎如释重负。“好吧,好吧。送他过来。我们稍后再处理所有这些。”
我猛地挂断电话,对琳恩挥了挥手。“去大学医院!”我喊道,他们立刻出发了。
我坐下来,盯着自己的双手。在医学领域,我们已经习惯了成本无关紧要的奢侈,任何经济上的限制都显得碍眼。然而,这种经济上的担忧,更像是一种令人震惊。
我双手抱头,坐在那里。
我突然想到,我可能要为这个男人的住院费用负责。毕竟,我刚刚明知故犯地把他送到了他保险不覆盖的医院。我从未征得他的同意。也许我得支付账单。然后我摇了摇头。我们所有人,护士、技师和我,都在大约一个小时内让这个病人得到了诊治、扫描和转院。如果这个人有机会康复,那将是因为这一切。我们做了对他最有利的事情。
我想象着如此严重的中风可能意味着什么:瘫痪、鼻饲管、留置尿管、压疮——那些侵蚀性极强的褥疮,仿佛有了自己的生命。你无法独立行走;无法洗澡;无法穿衣。你不能唱歌;你不能跳舞。
但你仍然可以哭。
一个小时后,达什医生打电话给我。她的声音有些不对劲。我花了片刻才意识到她在哭。
“怎么了?”我大喊。“是夹层还是血栓,还是什么?”
“他有血栓,”她抽泣着回答。“在脑中动脉中间有一个大血栓。我们进去做了。在屏幕上可以看到。我们给他用了药,血栓就消失了。他的腿部力量完全恢复了,他的手臂活动也好了很多。几乎完全康复了!”
我此刻感受到圣人目睹奇迹时的感受,既渺小又伟大。
“他想回家,”达什医生说。“他想回到他的商务会议。他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告诉他……我开始说,但停住了。我本来想说,告诉他他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把他送到了错误医院,去拿了一种我本以为没用的药物。”
我挂断电话,用双手捂住了脸。我又一次感到了谦卑。我想,这就是医学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