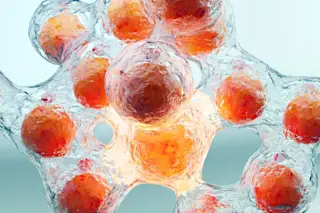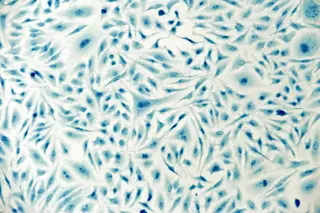连续三天,亚历克斯·乔弗里特每天喝一杯8盎司的牛奶。这可是一件大事,因为他已经多年没碰这东西了。乔弗里特患有克罗恩病,这是一种人们知之甚少的慢性肠道炎症。吃错了东西,甚至吃太多对的东西,他都会付出代价:在洗手间里痛苦地待上几个小时,胃痛、胀气和腹泻。
但乔弗里特还是冒了这个险。他和他的医生谢赫扎德·赛义德决定进行一项实验,乔弗里特将是唯一的受试者。在那三天里,他会像无所畏惧一样喝牛奶,就像他过去八年里没有小心翼翼地与消化系统达成和解一样。他会喝牛奶并记录那几天的感受。他排便了多少次?粪便里有没有血?他有没有胃痛和腹胀?然后赛义德将统计比较乔弗里特喝牛奶的日子和不喝牛奶的日子里的健康状况。
这不是科学家通常回答健康问题的方式。事实上,这个问题本身就完全错了。医学研究是在人口层面上进行的。你应该问一些大问题,比如“喝牛奶会导致克罗恩病患者出现负面症状吗?”然后你应该召集大量有代表性的患者样本,随机将他们分成几组,使用安慰剂或其他对照组来验证假设,并检查所有个体结果是否能得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综合答案。
这是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的基本大纲——医学研究的黄金标准,也是我们从医生那里听到和像本杂志这样的刊物中读到的许多医学事实的基础。这是我们了解身体如何运作(以及不运作)以及如何修复它们的最佳方式。
但即使是黄金标准也并非完美无缺。对照临床试验实际上是关于平均值的,而平均值不一定能告诉你个体身上会发生什么。这样的试验可能会告诉你,从统计学上讲,牛奶对克罗恩病患者不利。但在这个样本中,可能有人喝牛奶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有人在喝牛奶时症状有所改善。在医生办公室一对一的情况下,你所了解的群体平均结果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最终结论。
弥补黄金标准在我们知识上留下的空白的一种方法是“N=1”试验,其中参与者人数(N)是一个,而不是数百或数千名志愿者。那一个人与医生合作,测试一个狭窄的假设——例如,“我认为喝牛奶会让我生病。我说的对吗?”仍然有对照组。理想情况下,仍然有安慰剂。但最终,你得到的是一个针对患者的、个性化的答案。这个过程——通过对照临床试验,毫不逊色——已被证明可以改善患者的预后。而今天从事这些研究的科学家,包括赛义德,几乎无一例外地对N=1的潜力充满热情。
问题是,其他对N=1研究充满热情的医生和研究人员最终却感到失望。三十年来,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一直试图建立服务,帮助医生进行N=1试验。但这些服务一直失败,被成本、官僚作风以及医生和患者(这些研究本应帮助的对象)缺乏兴趣所拖累。
是什么让一个伟大的想法在实践中如此失败?赛义德和其他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已经找出了问题所在。而这一次,N=1将不再消失,而是会持续存在。
信任但核实
亚历克斯·乔弗里特一直是个挑食的人。但大约在四年级的时候,他生病了,随意的挑食——那种“早上醒来就觉得意大利香肠恶心”的挑食——变成了一些别的东西。他的胃开始疼痛。他在厕所里待了几个小时,反复发作腹泻。
介于此和吃进去的东西大部分都吐出来之间,不吃东西反而更容易。等到大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对几种食物的挑剔厌恶或一次严重的肠胃流感时,乔弗里特已经瘦了20磅,并且疲惫不堪,不得不坐在杂货店的货架上休息。10岁时,他背部缺钙的骨头裂开并骨折。

从10岁开始,亚历克斯在接下来的八年里经历了无数次手术和治疗。尽管如此,他常常显得乐观积极,即使在辛辛那提儿童医院接受治疗期间也是如此。| 乔弗里特家族提供
那是乔弗里特患上克罗恩病的开始。这也是他与食物之间奇怪关系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他将经历无数次手术和治疗,这些事情,连同克罗恩病的实际症状,都会影响他能吃什么以及何时吃。有时他只靠泰迪饼干和几罐佩迪亚舒维持生命。有时他根本不吃东西,所有营养都通过一根从他背上的背包延伸到他鼻子再到胃里的管子输送。乔弗里特在他高中二年级时唯一能去舞会的方式是,从他刚做完腹部手术的医院获得六小时的通行证。
如今,18岁的他正享受着小学以来最好的健康状况。没有人确切知道为什么他的病情在初中和高中期间会以可怕的方式爆发,但在与医生进行了一些实验后,他终于找到了一种可以控制克罗恩病的药物。这让乔弗里特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他越来越健康,不想做任何可能危及健康的事情。像他这种情况的克罗恩病患者不进行正式的实验,而是凭直觉尝试时尚饮食、补充剂、新食物和替代疗法,这并不少见。
这种实验并非克罗恩病患者独有。每个人在某个时候都尝试过单人实验。你想减肥,所以你尝试了新闻中不断听到的低碳水化合物饮食。你患有关节炎,你认为针灸可能比药物更能缓解你的疼痛。你的孩子感冒了,听了朋友的建议,你给他服用了一些锌。从这个意义上说,N=1试验并非新鲜事物。
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小实验的结果都值得怀疑。我们很少有人在尝试新疗法之前,先记录基线,追踪症状。我们通常也不会记录开始新疗法后发生的情况,或者分别测试不同的疗法,将它们相互比较,并与身体在没有任何治疗的情况下发生的情况进行比较。
这就是正式的N=1实验与日常关于健康的决策的区别。哥伦比亚大学退休生物统计学家、联邦医疗保健研究与质量局召集的专家团队成员(该团队最近发布了N=1实验用户指南)的奈华·端表示,有些实验比其他实验更正式,但最好的实验有三个重要的元素,这些元素在患者或患者及其医生只是尝试时并不存在。
正式 N=1 实验的第一个特征是治疗条件的随机分配。也就是说,患者应该在主动治疗期和某种安慰剂期之间,或在两种不同治疗期之间循环。其次,医生和患者都不知道患者何时服用安慰剂或治疗药物。这称为盲法。最后,医生和患者应该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详细跟踪症状,就像 Jofriet 和 Saeed 所做的那样。如果其中一个症状是腹胀,那么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每天的不同时间点都应该记录腹胀的量。
自20世纪中期以来,心理学家一直在运用这些基本原理进行单人实验。但单受试者研究真正跳跃到身体医学领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加拿大医生戈登·盖亚特(现在被称为循证医学的创始人)开始在安大略省麦克马斯特大学的一个跨学科部门工作,心理学家、生物统计学家、伦理学家和临床流行病学家都在那里协同工作。
在每周一次的部门研讨会上,一个人会展示他或她当前的研究,其他人则会提出批评和想法。盖亚特回忆说,在这些辩论中,一位心理学家不断提出N=1试验的想法。盖亚特决定了解更多。
当时,他正处理许多健康状况与大型随机临床试验结果不符的患者。其中一位是患哮喘的七旬老人,他服用的三种处方药似乎都没有帮助。盖亚特意识到,N=1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盖亚特和他的团队打算在安慰剂和三种药物中的一种之间进行三次盲法比较:茶碱,一种有助于呼吸的支气管扩张剂。但在茶碱和安慰剂之间切换两次后,他们不得不停止实验。很明显,改变药物正在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患者服用安慰剂时更健康。活性药物实际上使患者病情恶化,而不是好转。结果并不意味着仍在使用的茶碱是一种不好的药物。它只是对这位特定患者来说是一种不好的药物。从他的治疗方案中去除茶碱后,患者康复了。
盖亚特于1986年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这些结果。“明确确定某件事在个体身上是否有效,这真是一种激动人心的体验,”他说。“一项涉及1000人的试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仅仅招募就可能需要三年。有很多艰苦的工作。但N=1能让你快速得到答案。”
尽管N=1患者的改善并非总是如此显著,但过去20多年的研究为这些研究确实可以帮助医生和患者共同做出更好的决定这一观点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在慢性疾病方面尤其如此。
辛辛那提儿童医院医疗中心的赛义德(乔弗里特的医生)讲述了另一个案例:一个患有克罗恩病的女孩认为服用益生菌可以缓解她的症状。赛义德随后进行的N=1实验表明,益生菌实际上并没有帮助;症状的波动与她是否服用益生菌无关。所以她停用了益生菌,转而和她的医生们一起专注于找出症状波动的原因。
1990年,当盖亚特和他的团队发表他们的第一次工作回顾时,他们正在寻找的就是这种结果——回答了一个问题并改变了患者治疗计划的实验。在那时他们已经进行的70个N=1实验中,50个得出了明确的答案,其中39%的答案导致了治疗的改变。后来的研究也发现了N=1试验的类似益处。
然而,从盖亚特的角度来看,N=1试验一直令人失望。他和许多其他科学家在1990年代早期到中期发表了大量关于这些实验的研究,但后来他们大多放弃了。尽管这些实验产生了有用的结果,但其复杂的后勤使得单个患者和医生难以妥善管理,成本高昂且困难重重。与此同时,盖亚特和其他科学家发现自己为了进行这些实验的权利,不得不与内部官僚机构斗争。“我们坚持了大约五年,”盖亚特说,“人们仍然会时不时地打电话问我。我跟他们聊聊,然后说‘祝你好运’。”
起起落落,再起
如今,很少有人听说过N=1实验。当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内科研究副主任理查德·克拉维茨进行焦点小组,了解医生对N=1试验的看法时,他通常不得不从解释什么是N=1试验开始。
克拉维茨研究医生的行为如何影响患者健康,他将 N=1 实验视为改变医疗方式的巧妙手段——一个无需依赖超高科技、超昂贵的基因测序技术,即可为患者个体需求量身定制护理的机会。“它允许您在没有‘组学’的情况下实施个性化医疗,”他说。“您可以严谨科学,但不需要实验室。”不幸的是,虽然 N=1 实验可能比个人基因组学更接地气,但它们也有其自身的缺点——这些问题导致像盖亚特这样的研究人员在 20 年前放弃了它们。

Lienhard.Illustrator/Shutterstock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进行 N=1 试验非常复杂。大多数医生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工具、行政协助或额外资金来使其成功。而且在大多数试验中,你还需要安慰剂或糖丸,安慰剂和药物都需要进行伪装,以便患者和医生都不知道何时服用的是哪一种。
保罗·格拉齐奥曾负责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一项帮助医生设计 N=1 实验的服务,他表示这比听起来要复杂。尽管成分简单,安慰剂却不便宜。“(这意味着)让制药公司关闭正常的生产系统,转而放入惰性粉末,”他说。对于简单的单次实验,你可以去找复合药剂师制作胶囊,隐藏活性药物或安慰剂,但这类药房并不常见,而且它们很少批量生产。如果你想建立一个服务,理想情况下会有大量医生前来获取数百名患者的安慰剂或胶囊,那么这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官僚主义是笼罩N=1的第二个挑战。每当科学家想在人体上进行实验时,他们都必须获得机构审查委员会(IRB)的批准。N=1试验并没有明确地融入这种既定的官僚体系。这些试验不完全是研究:没有人利用它们在药物向公众发布之前弄清楚它是否有效或安全。这只是医生使用已批准的药物,弄清楚它们是否对特定患者有效。
但与此同时,它们也都是实验。而且,获取安慰剂和设置适当对照的过程使一些机构审查委员会(IRB)相信,N=1 试验应该遵循标准实验伦理协议。“IRB 完全不习惯这个想法,”克拉维茨说。“有些甚至要求每次试验都要单独批准。”所以,每次医生和患者想要比较一种药物和安慰剂时,他们都必须首先获得 IRB 的批准。“项目就此崩溃了,”克拉维茨说。这些问题导致盖亚特在麦克马斯特大学帮助医生设计和进行 N=1 试验的项目失败,许多其他项目甚至从未通过规划阶段。
当N=1实验的兴趣在过去十年开始反弹时,支持者不得不处理同样的问题。苏尼塔·沃赫拉负责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N=1服务。尽管她于2004年获得了资金,但直到2006年才能启动该服务。中间的几年充满了漫长的谈判,以说服大学N=1实验主要是为了改善患者护理,而不是研究药物和其他治疗方法的工作原理。
如今,她可以开展各种儿科N=1实验。她测试过益生菌是否能帮助患有湿疹的儿童。她帮助一个家庭弄清他们在另一个国家购买的补充剂是否真的改善了他们孩子的关节炎。她可以在不陷入官僚泥潭的情况下完成这些事情。
寻找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辛辛那提儿童医院医疗中心的项目——帮助乔弗里特的那个项目——找到了解决成本和复杂性的方法。科技提供了帮助:乔弗里特使用一个网络界面,他和他的医生赛义德可以在办公室预约之间设定目标、计划实验并跟踪乔弗里特的症状。乔弗里特可以发送短信或电子邮件,并填写在线调查。
但辛辛那提儿童医院也通过放弃安慰剂和盲法简化了 N=1 流程。例如,当乔弗里特进行实验以观察喝牛奶是否会让他生病时,他和他的医生没有制造假的“牛奶”——他们知道乔弗里特何时在喝牛奶,何时没有。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严重的牺牲。毕竟,盲法和安慰剂,以及随机分配和结果记录,本应是N=1实验与随意摸索的区别所在。但克拉维茨表示,像乔弗里特这样的实验仍然属于N=1。事实上,取消安慰剂可能是一件好事,这不仅仅因为它简化了实验过程。克拉维茨说,每当一种治疗起作用时,其效果实际上是药物的生物效应和一系列其他效应的结合,包括由医生在诊室中表现出的信心程度或药丸的颜色等因素引发的安慰剂效应。重要的是整体效果。
回想一下乔弗里特的牛奶试验。赛义德说,那个实验的目的不仅仅是看他喝牛奶后会发生什么。它还关乎情感和心理上的安慰。乔弗里特已经多年没有正常饮食了。尝试牛奶是迈向正常饮食的第一步。他需要看到自己喝牛奶,就像他需要看到结果一样:它没有伤害他。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乔弗里特继续用 Cheerios、绿色蔬菜、水果、花生酱、椒盐脆饼和肉类进行同样的实验。所有这些也都取得了成功,不仅因为他没有生病,还因为他恢复了正常生活。
辛辛那提儿童医院健康结果和护理质量研究主任迈克尔·赛德表示,这就是 N=1 实验值得进行的原因,即使你无法完美地进行。从赛德的角度来看,N=1 实验提供的个性化不仅是一种更便宜、技术含量更低的个性化医疗方式,它甚至比高科技工具提供的个性化更好。
个性化是关键
单受试者试验允许你个性化结果,而不仅仅是治疗。在N=1实验的帮助下,乔弗里特可以决定“能够喝牛奶”是期望的结果,他和他的医生可以找出如何实现这一点。
奈华·端说,这种以真正个性化的方式改善护理质量的能力解释了 N=1 试验为何卷土重来。这是影响大型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的更大趋势的一部分。从历史上看,这些“黄金标准”试验一直专注于获得 FDA 对药物的批准,或产生关于身体如何工作和对药物反应的普遍知识。换句话说,它们专注于为科学家服务。
段永平说,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在过去十年中,医学研究人员开始更加重视直接服务于患者需求的研究。其中一些以大型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的形式出现,旨在回答诸如两种现有治疗同一种疾病的方法中哪一种能以最少的钱产生最佳结果等问题。这种以患者为中心的研究趋势正在重塑医学研究的方式。2008年,这项运动有了自己的期刊《患者:以患者为中心的结果研究》。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成立了患者为中心的结果研究所。
N=1 实验完美契合了这种思维转变,这可能是让这些实验在曾经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的催化剂。段永平当然希望如此,他正在利用这个机会确保更多人了解 N=1 实验及其作用。今年夏天,他与克拉维茨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比较了近 250 名患者的 N=1 实验与标准医疗治疗。这项研究代表了 N=1 首次与传统医疗保健正面交锋。根据段永平和克拉维茨的发现,这项研究可能导致一个拥有更多亚历克斯·乔弗里特的世界——以及更多人一次一个患者地改善健康的机会。
[本文最初以“ singled Out ”的形式发表于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