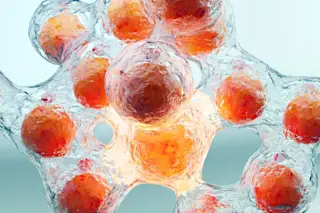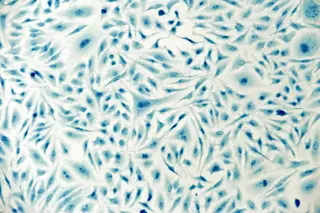“猜猜谁在候诊室?”值班护士以尖锐的声音唱道,然后走进了急诊室。“不等我们猜,她就自己回答了:Livinia!”
从工作站里爆发出一阵医生和护士的合唱。
“她又来了?”
“真是一个软弱的人。”
“但我才两周前刚见过她。”
“哦,不——不是 Livinia!”
我承认——这是医护人员对病人,尤其是患有严重慢性疾病的病人,不恰当的谈话方式。如果你见到引起这种反应的人,你会更加震惊。Livinia Johnson 是一位非常 pleasant、举止得体、穿着讲究的 29 岁黑人女性,她是一名计算机程序员,业余时间喜欢阅读科幻小说。
但 Livinia Johnson 也饱受因一种令人沮丧的常见且无法治愈的疾病——镰状细胞贫血——引起的严重反复发作的疼痛。当她被推过我座位旁的玻璃窗时,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手里拿着一本科幻小说,我心中充满了熟悉感和恐惧。又来了,我对空气说。
尽管研究为骨髓移植或基因疗法治疗镰状细胞疾病提供了希望,但目前我们医生所能做的就是开些“创可贴”:治疗感染,尽力减轻难以忍受的疼痛。这是最令人不满的医学——对医生和病人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看到 Livinia 再次出现让我们感到沮丧。这也是为什么她总是会在这里。
在镰状细胞疾病中,正常情况下柔软圆形的红细胞携带着一种有缺陷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会扭曲并使其锁定成一种不寻常的形状——弯钩形。这些有缺陷的、镰状的细胞非常坚硬且脆弱,并且比正常红细胞的寿命短。因此,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几乎总是贫血,而输送氧气的红细胞稀少意味着他们会感到疲劳和呼吸短促。
此外,僵硬的细胞不像正常细胞那样能够灵巧地通过小血管。有时它们会卡住,阻塞流向器官、肌肉或骨骼的血液。组织缺氧,开始窒息,当细胞死亡时,它们会发出信号,神经将其解释为疼痛。但这并非寻常的疼痛。这是与心脏病发作的人经历的相同类型的疼痛——由完全相同的原因引起。有些人将其严重程度比作分娩的疼痛。
Livinia 的疼痛通常在腰部、腹部或膝盖。这次也不例外:她病历上的护理记录显示她抱怨腹部剧痛。
“你好,Rosenthal 医生,”当我走进房间时,她疲惫地从担架上向我打招呼。“你家小姑娘怎么样了?”
“她很好,谢谢,Livinia,”我回答。“你怎么样?我猜不太好,如果你在这里的话。”
在我们断断续续的七年医患关系中,Livinia 陪伴我度过了医学培训、婚姻和怀孕,现在她正看着我缓慢地爬升学术阶梯。我看着她更换男友、搬出父母家、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几年前,她让我直呼其名。
但现在她不太有心情闲聊了。她告诉我,她的疼痛从昨晚开始,即使服用了家里的止痛药,她也无法忍受了。“我一整晚都在服用 Percocet,但我的肚子越来越疼,”她说,眼中噙满了泪水。
我迅速地问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我已经问过她,她也回答过十几次了。
“有发烧吗?”(没有。)
“饮食还好吗?”(直到昨晚都还好。)
“在疼痛开始前,有感染的迹象——咳嗽、喉咙痛、小便时有灼热感吗?”(没有。)
尽管这些疼痛危象可能毫无征兆地发生,但它们通常是由某种身体应激引起的,例如感冒或其他病毒感染或脱水,这会使本已受损的红细胞更难通过血管流动。然而,这并非仅仅是警惕感染的原因。在镰状细胞疾病患者中,脾脏——通常通过过滤血液中的细菌来帮助免疫系统——经常因反复的血管堵塞而受损,因此难以抵抗某些病原体。因此,当出现感染迹象时——例如发烧或极高的白细胞计数——这些患者几乎总是需要住院。
Livinia 没有发烧。我抽了一些血来检测她的白细胞和其他一些指标,但没有任何感染迹象。因此,没有必要让她住院;Livinia 应该可以在急诊室通过一些止痛药、氧气和输液来度过这次危机。我们输氧是为了让窒息的组织有最好的机会吸收一些重要的气体。我们输送大量的液体,以保持血液稀薄并尽可能自由地流动,并防止脱水。
麻醉剂的原因很明显。“我们通常给你什么来止痛?”当护士将氧气面罩戴在 Livinia 脸上并费力地在她手臂上插上静脉输液管时,我问她。她过去曾被扎过无数次针,导致她的血管布满深疤。
“Demerol,125 毫克,Vistaril,50 毫克。所有的镰状细胞病患者,就像我们称呼这些病人一样,都牢记着对他们最有效的止痛组合。”
“好的。稍等几分钟。我去开医嘱,护士会给你打一针。”
当我坐下来为 Livinia 开药时,工作站里挤满了医生和护士。
“你给她开 125 毫克的 Demerol?”一位医生问,他从我身后探过头来。“我不知道。她看起来挺好的。”
“我觉得她在装,”一位护士插话道。“在候诊室里她疼得直打滚,但当我经过她房间时,她却在看书。”
我已经写好了医嘱,但他们的评论让我犹豫。我决定在把医嘱单交给护士之前,偷偷看一眼 Livinia 的病历卡。
急诊室里最常用的设备之一是一个绿色塑料文件盒,里面装满了磨损的四乘六英寸的索引卡。每张卡片上都写着一位因慢性疼痛在急诊室反复接受治疗的患者的名字,以及(通常是麻醉剂)和(通常是大剂量)的药物,这些药物被用来对抗这种疼痛。每一行都记录了一次单独的就诊;一些病人的病历现在有五到六张卡片长。虽然有几位病人患有偏头痛,有几位患有腰痛,但绝大多数是镰状细胞患者。
Livinia 的卡片详细记录了她几十年的痛苦。我翻到最后一项记录:Demerol 125 mg/Vistaril 50 mg。正如她所说。我为检查感到内疚——毕竟,如果一个痛苦的病人告诉我,他通常服用 125 毫克的抗生素来治疗耳部感染,或者 125 毫克的强心药来治疗胸痛,我会立即给他开药。那么,为什么镰状细胞患者在痛苦并寻求帮助时,却要遇到这种怀疑的墙壁呢?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医生和护士都是按照科学家的培训方式——而且仍然没有科学方法来衡量镰状红细胞引起的痛苦。我可以看进耳朵里,看到红肿的鼓膜。我可以扫描心电图,确定心脏需要更多的血液。但是当 Livinia 告诉我她很痛时,我无法进行任何血液检查,也无法用手指或探针或触诊来确信这一点。
我能衡量的只有她的反应。一些护士认为,因为 Livinia 在急诊室里可以坐起来看书,所以她真的不痛。至于我,我也不确定。Livinia 看书是否一定意味着她没有遭受痛苦?也许情节转移了她对内心灼痛的注意力。但是当我把药物医嘱交给护士时,她告诉我,她会在完成其他几项工作后给她注射,然后她会开玩笑地称我为“毒贩”和“容易上当的人”。
如何治疗处于危象中的镰状细胞患者的困境,因其有帮助的药物几乎都是潜在的成瘾性麻醉剂而变得更加复杂。在我们的整个教育过程中,医生和护士都被警告过这些药物的成瘾潜力;我们被告诫要谨慎使用。但镰状细胞患者需要它们,而且需要很多。
当然,我们在急诊室工作的医护人员见过不少很可能对注射上瘾的病人,或者至少非常享受短暂的住院体验。三年前,当一种名为 Toradol 的强效非麻醉性止痛药上市时,这一点变得非常明显。在我工作的医院,我们曾尝试使用它来减轻镰状细胞危象患者的疼痛。虽然一些病人说它确实有帮助,但其他病人甚至拒绝尝试,立即声称对 Toradol 过敏。
在美国,镰状细胞疾病几乎只发生在黑人身上。(在中东和印度,非黑人也有此病。)在这个急诊室里,由于疾病的性质和我们所处的社区的性质,它最常出现在年轻、贫穷的黑人身上——这正是我们最担心麻醉剂成瘾的人群。
把所有这些加起来,就会很容易让倦怠的医生和护士认为年轻的镰状细胞患者是装病,只是为了获得药物。事实上,对镰状细胞患者的偏见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血液学家说他们害怕不得不收治他们的病人。
“这是一位很棒的男人,尽管患有可怕的疾病,他仍然努力工作,”我记得一位这样的医生评论道,当时他正在为一位 30 岁的患有肺炎的镰状细胞患者办理入院手续。“他是一位成功、受人尊敬的专业人士,除非遇到真正的麻烦,否则他讨厌吃药。然后他来到医院,却被轻蔑和怀疑地对待,就像一个瘾君子。太不公平了。”
在第一次注射麻醉剂两小时后,Livinia 走过我房间时叫住了我。她说她想要再打一针;她又开始疼痛了。时间还太早,但镰状细胞患者需要两针或更多针是很常见的。他们很少只用一针就能摆脱疼痛。Livinia 坐起来时正龇牙咧嘴——尽管她膝盖上的书仍然打开着。当我开出另一份止痛药的医嘱时,我不禁希望她能在护士来之前把书合上。
在我开出她第二针的医嘱后,她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出来了。她的白细胞计数略有升高——但不足以表明感染。这种升高无疑是由于引起疼痛的组织炎症以及身处剧痛中的压力。她的肾功能肌酐检测为 1.8。肌酐是代谢的废物产品,通过尿液从体内排出——如果血液中残留大量肌酐,则意味着肾脏功能不正常。通常,Livinia 这个年龄的人的肌酐水平会低于 1,但 1.8 对她来说不算太糟。相比之下,透析患者的肌酐水平通常在 8 到 10 之间。但这表明,这些镰状红细胞多年来已经损害了她的肾脏,需要密切关注。她的血细胞比容——血液中红细胞的百分比——为 28%,远低于 37% 到 48% 的正常范围,但对于患有这种可怕疾病的人来说,这仍然是正常的。
Livinia 实际上对镰状细胞患者来说算很幸运了。许多人不得不看着他们的内部器官一点一点地死亡。一位我经常看到的年轻女性患有严重的充血性心力衰竭——那些镰状化的血细胞过多地阻碍了流向她心肌的血液。另一位患者有两个人工髋关节:卷曲的细胞会阻塞流向关节的血液,导致骨骼死亡。我们急诊室里经常同时会有两三个镰状细胞患者,他们经常互相交流。听到这些故事肯定让 Livinia 感到害怕。或者听到她停止讲述这些故事。尽管镰状细胞患者的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但感染和主要器官(如心脏、肺和肾脏)的阻塞仍然使他们的寿命比正常人短。
如果 Livinia 的疼痛能有所缓解,我就可以让她回家了。但这并非总是可能的。大约一半的镰状细胞患者在疼痛危象后会被收治入院。我们有一个宽松的政策:三轮麻醉剂或八小时治疗后,患者要么回家,要么入院。在病房里,他们将继续在疼痛和麻醉剂之间循环。一些医院——但不是我的医院——现在使用患者控制的麻醉剂泵。只需按一下按钮,镰状细胞患者就可以给自己注射剂量的止痛药。这避免了已经生病的成年男女为了乞求药物而忍受进一步的羞辱,并在疼痛中等待。
Livinia 走进医院七小时后,她蹒跚地走向护士站。我看着她——她是那种在医院里待了足够长的时间,懂得如何熟练携带输液袋的病人。她显然感觉好多了,但当她探头到工作站时,她说:“我觉得我还需要再打一针。然后我就准备好了。”
她还有疼痛吗?我应该再给她打一针吗?她只是想再打一针作为保险,以确保她回家后疼痛不会复发吗?如果我处于她的处境,我难道不想再打一针吗?
我没有任何理由相信 Livinia 上瘾:她在工作,并且服用着稳定的药物剂量。而且,我自己已经决定,我宁愿给急诊室里一个并不真正承受身体痛苦的人注射麻醉剂,也不愿拒绝给真正痛苦的人用药。
所以我开出了再注射一针的医嘱。一小时后,Livinia 已经穿好衣服,准备回家了。她感谢我的照顾。我祝她升职顺利。我喜欢她。我相信她当时是疼痛的。我知道她患有严重的疾病。然而,我确保更新了她在那个破旧的绿色盒子里的卡片:Demerol 125 mg/Vistaril 50 mg,三次。无感染。出院时带 25 片 Percocet。可能为疼痛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