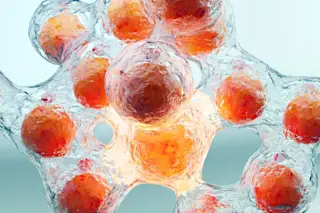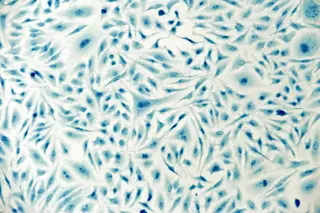不久前在非洲,我曾在一个似乎是地球上最完美的地方之一露营,那是在一片树林边缘,俯瞰着一片洪泛平原。星星在天空中闪烁,形成烟雾状的光团,我躺在帐篷里,听着远处狮子的低吼和豺狼悲伤的哀鸣。早上,我和我的同伴们围着一堆篝火蹲坐着,看着夜晚在开阔的平原上渐渐融入黎明。那可能是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是狩猎采集者。那也可能是数百万年前,我们是猿猴。
那感觉就像家一样,我拜访的生物学家建议,也许我们在这片景观中的进化,不仅塑造了我们髋关节的活动方式或手的抓握方式,还塑造了更多。他说,也许进化影响了我们的喜好。也许我们喜欢光滑闪亮的表面,因为它们暗示着靠近水源。也许我们喜欢某种多枝的树形,因为更新世的祖先晚上在这样的树上栖息,以躲避捕食者。也许我们认为是纯粹文化和艺术的东西——比如芭蕾舞演员踮脚时脚踝优雅的伸展方式,这是很少有男人能做到的——实际上是类人猿进化的产物。一位生物学家曾提出,女性的脚踝可以旋转更大的弧度,因为我们的早期女性祖先在树木和灌木丛中觅食时必须从一个树枝伸展到另一个树枝,而体型较重的男性则倾向于在平地上活动。
当我回到家开始阅读时,发现“美学可能具有自然史”的观点不仅仅是闲聊。理查德·科斯(Richard Coss),现在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教授,在他30年前作为一名年轻的工业设计研究生所写的一篇论文中,很大程度上创立了进化美学这一概念。科斯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我们对艺术和视觉世界的反应,不仅仅是作为审美家(甚至是粗俗之人),而是作为动物。除其他例子外,他引用了保罗·克利(Paul Klee)的一幅抽象画《蛇女神和她的敌人》。科斯指出,蝴蝶和其他生物常常利用假眼点来制造捕食者的警报。他认为,克利通过类似的“释放机制”——蛇的S形和带有两个突出眼睛的面具——在观者中引发了一种固有的生物反应。
从动物行为的角度审视艺术的理念也曾出现在华盛顿大学的戈登·奥里安斯(Gordon Orians)的脑海中。奥里安斯在研究乌鸫如何选择栖息地时,注意到人类也根据特定标准选择他们的栖息地,比如水的存在、大树、开阔的空间和远处的视野——这些标准都让人联想到人类进化的稀树草原。此外,当奥里安斯请受试者评价风景画时,他们往往更喜欢符合这些标准的画作。奥里安斯认为,像约翰·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的风景画《德勒姆谷》(Dedham Vale)之所以吸引我们,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它为观者提供了寻找资源和避免危险的线索。审视它是一种无意识的栖息地选择练习:我能住在这里吗?探索安全吗?我应该转身逃跑吗?
科斯和奥里安斯开创的观点已经越来越流行。但对许多人来说,从动物行为角度看待艺术仍然是对我们关于“何以为人”观念的冒犯。我们倾向于认为,很少有事物比艺术更具个性,而我们独特的品味可能具有共同的生物学基础,这一观点难以接受。例如,奥里安斯认为,著名的英国乡村别墅景观是无意识地试图重现非洲大草原的环境。我最近向一位英国贵族提到了这个想法,他惊恐地回答说:“不。我们是想展现英国乡村的自然特色。”但几个世纪以来,她的家人为了在他们的宅邸中营造“自然”效果,所采取的手段包括砍伐森林以创造开阔的视野,引入水塘,以及将庄园改造成一片稀树草原。
进化论的观点也一直难以被接受,因为美学生物学研究往往比科学家(和一些艺术史学家)所希望的要模糊。奥里安斯、科斯和其他人通过语言和生理测量(如瞳孔大小和血压)来量化偏好。然后,他们将这些偏好在不同文化(有时是不同物种)之间进行比较,以辨别它们是天生还是后天的产物。怀疑是典型的反应:一位著名博物馆的策展人认为,艺术受文化发展的影响远大于进化,例如摄影术的发明或印象派的兴起。
但生物学家相信,远古历史——不同体型、生存策略和栖息地本能的兴衰——以一种塑造DNA的方式,使DNA成为一种幽灵般的木偶师。对人类而言,将我们与过去联系起来的绳索可能延伸到200多万年前。这些绳索以先天倾向的形式存在,是我们不假思索、无需从父母那里学习就能做的事情。正如在克利和康斯特布尔的画作中,艺术家们常常无意识地表达这些相同的倾向。
动物最基本的遗传倾向之一是选择祖先繁衍生息的栖息地。例如,草原鹿鼠只生活在中西部的草原上。当科学家在隔离状态下饲养它们,并让它们在草原和其他栖息地之间做出选择时,未经训练的幼崽几乎总是选择草原。这是它们基因中的特性,自然选择使其得以保留。对于大多数动物,包括人类,选择适宜栖息地——一个提供充足食物、繁殖机会和庇护所的地方——的本能是生与死的区别。过去选择不佳的个体留下的后代较少,无法延续其愚蠢的行为。另一方面,具有选择良好栖息地本能的个体倾向于产生更多后代,从而将它们的本能传播到种群中。奥里安斯说,因此被编入我们基因的,是对良好栖息地——以及良好栖息地的绘画和照片——的情感或心理反应。
大多数动物似乎在生物学上就准备好识别良好栖息地的高度特定指标。当黄莺每年春天抵达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时,树木仍然没有叶子,地上还有雪。但黄莺似乎通过光秃柳枝的形状和颜色来识别,这里很快就会成为良好的栖息地。同样,当科学家向笼养的鸣雀提供落叶和针叶树枝时,它们会栖息在针叶树枝上,这正是它们祖先栖息地的线索。
即使天生具备辨别合适栖息地的能力被写入基因,个体动物也常常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忽略或改变这些先天倾向。游隼已经进化到在悬崖峭壁上筑巢。但如果一只游隼飞到纽约市,那里没有合适的悬崖,它并不会突然像知更鸟一样在中央公园的树上筑巢。相反,它会在仅次于悬崖的次优选择上筑巢——一栋俯瞰公园的第五大道公寓楼。生物学家认为,人类的适应方式与此非常相似。那栋楼里的住户会比游隼建造更精致的巢穴。但进化生物学表明,他们也在美化先天倾向:人类和游隼选择栖息地出于同样的原因——也就是说,靠近良好栖息地和安全的视野。
证明人类对自然有基因预设的负面反应相对容易。例如,我们理性地知道,在现代世界中,手枪和磨损的电线比蛇或蜘蛛构成更大的威胁。但我们的进化使我们更本能地恐惧自然威胁,这些恐惧一直伴随着我们,尽管致命的蛇或蜘蛛可能已经几千年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科学家们进行了巴甫洛夫式条件反射实验,受试者反复暴露于威胁性图像。对手枪和磨损电线的恐惧相对较快地消失了。但对蛇和蜘蛛的恐惧,通过心率和其他自主神经系统活动测量,在很久之后仍然存在。这在我们的基因里。
证明我们对自然有着生物学上预设的积极反应则更为困难,因为我们对非威胁性的事物反应并不那么剧烈。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研究表明自然风光对身心健康的微妙治愈力量。例如,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研究员罗杰·乌尔里希(Roger Ulrich)发现,经历过压力后观看平静自然视频的人,在不到五分钟内,肌肉张力、脉搏和皮肤电导活动均显著降低。这转化为显著的医疗益处。乌尔里希监测了胆囊手术后的患者,发现那些被分配到能看到树木的房间的患者比那些面向砖墙房间的患者需要更少的止痛药。在墙上贴有自然风光画的房间里的心脏手术患者比那些墙壁空白或挂有抽象艺术品的患者焦虑程度更低,康复也更顺利。同样,被困在太空数月的宇航员很快就对视频节目和其他消遣失去了兴趣。他们宁愿凝视窗外那遥不可及的地球。
我们似乎在生物学上已准备好寻找关于自然世界的非常具体的线索,就像鸣雀选择针叶树枝的方式一样。在不同的调查中,乌尔里希、奥里安斯和其他人发现,人们对拥有开阔草地植被、零星的枝繁叶茂的树木、水、地势变化、蜿蜒小径和光线充足的空地(最好前景被树叶部分遮挡)的风景反应强烈。这是一种邀请探索的景观,同时承诺着资源和避难所。地势的变化——例如远山的景色——提供了一个地标,帮助观者在场景中定位自己。蜿蜒的小径和部分被遮挡的空地则提供了神秘感,并激发出我们天生的探索好奇心。花朵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们的美丽,还在于它们预示着果实和蜂蜜。奥里安斯和合著者朱迪思·希尔瓦根指出,我们更喜欢大而不对称的花朵,这些特征表明花蜜含量更高。他们认为我们把花带到医院,因为它们确实是良药:它们以未来会更好的承诺来抚慰我们。
所有这些似乎与约翰·康斯特布尔的风景画相去甚远。但奥里安斯和希尔瓦根发现,康斯特布尔和其他艺术家的风景画中充满了这些栖息地线索。当他们将康斯特布尔现场绘制的素描与他后来在工作室创作的成品画作进行比较时,他们发现这位艺术家始终在“稀树草原化”现实,以增强理想的线索——移除树叶以露出树枝,或添加房屋以作避难所。栖息地线索甚至出现在莱昂纳多·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这样的肖像画中。宁静的不仅仅是这位女士;而是背景:一条蜿蜒的小路穿过稀疏的树木,通向一个光线充足的空地,远处有横跨河流的桥梁和山脉,所有这些都在蓝天下。在随后的研究中,奥里安斯和希尔瓦根将他们的进化论观点应用于弗雷德里克·丘奇和马丁·约翰逊·海德等艺术家的35幅日落画作,他们的理论是日落对我们的祖先来说充满了紧张感。“当你在非洲稀树草原上行走时,”奥里安斯说,“天空变得粉红色,半小时后狮子和鬣狗就要出来了,日落是可怕的。我们在日落时真的会担心晚上会在哪里过夜。”奥里安斯和希尔瓦根发现,三分之二的画作都包含了一个观者清晰可见的避难所——一座教堂或一栋房子,通常窗户里透着光。
当然,在英国或美国风景的背景下,对狮子的焦虑是不理性的。但生物学家说,我们天生就会对这类风景做出快速判断,无需有意识的思考。乌尔里希说:“直到最近,行为科学一直被那些强调有意识、深思熟虑的思维是情感来源的理论所主导。但这样的动物会非常功能失调:‘有东西在动。天哪,它看起来像一条蛇。上次我看到蛇,有人被咬了。嘿,也许我应该感到有点害怕。’嗯,不。”当我们看到蛇时,跳开的速度比我们说出这个词的速度更快。身体对威胁产生生理反应只需不到四分之一秒,而对积极刺激产生反应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据乌尔里希说,大约一两秒。
但是等等。除非精神错乱,博物馆里的人难道不知道他们看的是墙上的画,而不是真实的风景或真实的蛇吗?在传统批评中,我们的审美反应实际上被定义为不真实且没有实际应用。看到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画的坎贝尔汤罐并不会让我们拿起勺子,日落的画作也不应该让我们想象自己身处稀树草原,无处可睡。
但生物学家认为,审美反应和现实生活反应仅有程度上的差异。“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在这方面很出色,”《艺术的生物学起源》一书的作者南希·艾肯说,“你看到一把刀落下,你不需要看到受害者;你知道它击中了。你可能会真的倒吸一口凉气,抓住椅子的扶手。血压升高,手掌出汗。这是一种内在的、本能的警报反应。我们正在生理上为逃离危险做准备。”意识大脑需要一点时间来提醒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危险。
那么,我们应该根据什么来评判艺术呢?是让手掌出汗的,还是能抚平愁眉的?一位驳斥生物学与艺术毫不相干观点的艺术史学家建议我查阅一本近期出版的书,名为《数字绘画:科马尔和梅拉米德的艺术科学指南》。俄罗斯移民维塔利·科马尔和亚历山大·梅拉米德委托在各国进行民意调查,了解人们在绘画中想要什么。对梅拉米德来说,结果的一致性表明了基因印记:“在每个国家,最喜欢的颜色都是蓝色,几乎所有地方绿色都位居第二……所有人都想要户外场景,有野生动物、水、树木和一些人。”两位艺术家随后绘制了每个国家“最受欢迎”的图像。例如,肯尼亚的画作中,耶稣基督从湖中升起,远处是乞力马扎罗山,一头河马在岸边吃草,一家人正在用杵臼准备晚餐,天空是蓝色的。当然,重点在于讽刺。
有时,生物学观点似乎危险地接近科马尔和梅拉米德的视角,却缺乏讽刺意味。例如,乌尔里希写道:“需要研究以建立科学指南,帮助室内设计师选择能够有效减压并提供生理支持的艺术品……”但他只谈论医院和其他医疗环境中的艺术,他认为唯一重要的评判标准是艺术是否“改善患者的治疗结果,如果不能,那就是糟糕的艺术”。
任何关于艺术的科学指导方针的提法都注定会激怒众人。听着乌尔里希的说法,你很容易想象到某些医疗事故律师脑海中已经酝酿的侵权行为:“那幅杰克逊·波洛克的画杀死了我的委托人。”实际上,弄清何为治疗性艺术可能很困难。20世纪90年代中期,杜克大学医学中心安装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庭院雕塑装置,名为“鸟园”,灵感来自弗洛伦萨·南丁格尔的信念,即医院中的好艺术可以成为“实际康复的手段”。它由10英尺高的钢制雕塑组成,纪念那些已经灭绝的鸟类,如渡渡鸟和旅鸽。患者看着庭院雕塑,很快就开始将自己的烦恼投射到艺术品上。其中一件让他们想起从坟墓中伸出的手。另一件描绘猫头鹰的雕塑,因其阴沉的眼神而令他们不安。像科斯这样的心理学家可能会告诉管理人员,黑猩猩会避免看有突出眼睛的玩具,大猩猩会因望远镜的空洞凝视而感到威胁,而“人类今天对形式最原始的避免反应之一,就是对陌生人固执的凝视产生回避反应。”该医院此后已移除了这些雕塑,并用无害的植物重新设计了庭院。
但所有这些都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些不身在医院的人,实际上却会去寻求那些令人不安的艺术?如果进化塑造了我们的喜好,为什么我们不坚持那些宁静的稀树草原景观呢?为什么要进博物馆去看乔治·斯塔布斯(George Stubbs)的画作?他从未离开欧洲,却描绘了狮子用牙和爪刺入受惊马匹颈部的场景。J.M.W.特纳(J.M.W. Turner)的暴风雨海景画为何如此吸引我们?它似乎在画布上旋转,没有地平线或其他任何能让观者立足的东西。奥里安斯说,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这类画作引人入胜,因为它们能帮助我们做好准备。我们看它们的原因,与我们对车祸视而不见或在探索频道观看《鲨鱼周》的原因相同:为了学习如何避免陷入同样的境地。看希区柯克的《惊魂记》会吓到我们——并提醒我们锁上浴室门。艺术是关于生存的信息。我们也被设计成寻求刺激,最好是在安全的环境中。博物馆里的一幅画让我们无需像艺术家那样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冒着沉船的危险,就能体验特纳笔下的完美风暴。
关于视觉快感与危险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些最引人入胜的观点持续来自科斯,他研究了从加州地松鼠的捕食者反应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飞船上宇航员的视觉刺激设计等一切。在他目前的研究中,科斯正在学习各种灵长类动物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豹子的侵害,豹子捕食它们(和我们)已有300多万年。例如,食蟹猴的视觉系统对黄色高度敏感,显然是为了更容易发现豹子。科斯还发现,一块足球大小的斑点皮毛即使在几代未接触过豹子的帽猴种群中也会引发警报。他推测豹子的斑点也会在人类中引发天生的捕食者反应。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扎伊尔已故独裁者蒙博托·塞塞·塞科等国家元首会穿着豹皮长袍和帽子。
蛇身上之字形的鳞片图案似乎也能在许多动物中引发一种先天的兴奋。科斯翻看一本服装目录,看到一张穿着高缇耶泳衣的女性照片。他说,这个图案来自一种有毒的亚洲蝮蛇。这让他不禁思考其预期的效果:“如果你的服装上有引人注目的东西,你再结合一个不会伤害你的人的身体,那可能会让你更感兴趣。它不会让你感到恐惧,因为它不是一个可怕的环境。”
教堂和寺庙似乎以略微不同的方式使用蛇皮图案,科斯建议道。旧清真寺和教堂中类似蛇皮的瓷砖图案“可能会增强宗教的、狂热的情绪”,引发“敬畏和尊崇”的混合情感。或者这些图案可能仅仅有助于让信徒保持清醒:“这些是吸引注意力的东西,”他说,“而且它不会减弱,我们不容易习惯它,图案不会变得中性。”科斯说,我们的视觉世界充满了这些生物学线索,它们常常在无意识中被运用,人们也以同样不假思索的方式对此作出反应。
科斯认为,在某些公共场所,尤其是楼梯和走廊,复杂的视觉细节,如带图案的墙纸或地毯上醒目的图形,可能通过转移靠近陌生人的视线来发挥社会功能。在其他情况下,这些细节可能微妙地令人感到压抑。例如,不久前,我住在一个海滨出租屋里,后来我开始把它称为“节疤松木地狱”。过了一会儿,我明白了是什么让我如此不舒服:木镶板上的节疤就像一双双不眨的眼睛,环绕着我。
奥里安斯说,有证据表明,我们的视觉环境深刻影响着我们的身心健康,就像一个合适的栖息地能让动物园里的动物更健康一样。
我在家里想着这一切,坐在我和妻子最近在康涅狄格海岸建造的房子门廊上。我周围的门廊柱子突然感觉像树干,天花板变成了森林冠层,头顶的吊扇像微风中的树叶一样 fluttering。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所创造的不过是非洲森林边缘那个营地的一个精致复制品。从我的庇护所望出去,看到了一个完美的生物栖息地线索清单:有绿草茵茵的草坪,一条小径蜿蜒穿过零星的枝繁叶茂的树木,远处是一个光线充足的空地,部分被植被遮挡,再远一点,是一大片深蓝色的水域。我闭上眼睛,能感受到进化的牵线木偶般地牵引着我千禧年之交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