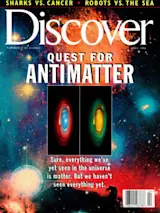在经历了贝斯手、训狗师、木匠、生物学学生和《花花公子》兔女郎的生涯后,波莉·马辛格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附近的一家餐厅找到了一份鸡尾酒女服务员的工作。一天晚上,她为两位科学家服务,其中一位是罗伯特·斯旺皮·施瓦布(Robert Swampy Schwab),他当时是戴维斯分校野生动物与渔业系主任,现在是名誉教授。施瓦布和他的同事正在讨论一项最近的实验,这时他们的女服务员指出了他们推理中的几个错误。“我们说,‘天哪,那是谁?’”
马辛格和施瓦布因此结识。施瓦布说,她思想敏锐。她能发现问题、抓住要点,并找到一半的解决方案。有些人天生适合做研究,你能看得出来。马辛格说:“他发起了长达九个月的‘攻势’。他说,‘你是个科学家!你应该成为科学家!’我说,‘走开——这会像其他任何工作一样变得无聊。所有事情过一段时间都会变得无聊。’然后他会在打烊时回来,我们会去一家通宵营业的丹尼斯餐厅聊科学。”
马辛格说,那些谈话帮助她决定重返校园,成为一名科学家。几年后,当施瓦布听说马辛格正在获得免疫学研究资助时,施瓦布的同事斥责她是个江湖骗子。施瓦布回忆说,“他说,‘她只是个酒吧女招待。’但我说,‘不,我认为这是真的。如果更多酒吧女招待有她那样的头脑,你和我就要失业了。’”
近20年后,这位昔日的酒吧女招待如今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免疫学实验室主任、数十篇科学论文的作者,以及一部获奖免疫系统电影的创作者。但她仍然在科学家们的推理中挑毛病。事实上,马辛格认为免疫学的核心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近50年来,免疫学家一直认为他们了解免疫系统的基本职责:识别“自我”与“非我”的区别,并抵御外来侵略。马辛格对此不以为然。她说,免疫系统不费心去感知“自我”——它只对危险有清晰的感知。
“自我/非我”模型可追溯到二战结束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它——以及它所享有的广泛支持——可能受到了冷战仇外心理的影响。但奠定该模型实验基础的研究者是一位免疫学耐受性的先驱。1944年的一天,彼得·梅达沃(Peter Medawar),当时是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尚未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彼得爵士——正和家人坐在花园里,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低空掠过,在几百码外的路上坠毁。一名严重烧伤的飞行员被从残骸中救出,当地医院的外科医生,梅达沃的同事,请求梅达沃帮助用皮肤移植治疗受害者。
那时人们已经知道,虽然身体会接受自身皮肤的移植,但会迅速排斥来自他人的皮肤移植。尽管如此,飞行员还是接受了异体移植,希望给他自己的皮肤一个重新生长的机会。梅达沃和他的同事随后做了一个有趣的观察:来自特定供体的第二次移植被排斥的速度比第一次快,也比来自新供体的移植快。这一观察结果的含义很明确,梅达沃随后通过对兔子的对照实验证实了这一点:排斥是免疫学上的。飞行员的免疫系统正在排斥异体皮肤,就像它排斥病毒一样,而且一旦见过,下次就会记住它——就像免疫系统会记住并为水痘等做好准备一样。
这项观察对飞行员没有帮助(尽管他康复了),但它使梅达沃走上了一条研究之路,这条路不仅使他成为一名免疫学家,而且彻底改变了免疫学。如果皮肤移植排斥是一种免疫现象,那么很自然地会问,正如梅达沃所问的那样,是否有可能使免疫系统更具耐受性。对牛双胞胎的实验已经表明这种耐受性是可能的。由于牛双胞胎共享胎盘,它们的造血细胞在子宫内发育时会混合。因此,即使是异卵牛双胞胎——它们在基因上不完全相同——也可以相互接受皮肤移植。不知何故,早期接触异体血细胞会训练免疫系统将异体组织视为自身。
在一系列开创性的实验中,梅达沃证明了这种耐受性可以通过人工诱导。他取来怀孕的棕色小鼠,并向其胎儿注射了来自白色小鼠的细胞。当棕色后代长大后,他将白色皮肤补丁移植到它们身上。白色皮肤没有被排斥;相反,它在棕色皮毛的海洋中形成了健康的白色岛屿。
如果梅达沃对兔子的实验表明免疫系统能区分自我与非我,那么他对小鼠的实验则表明,这种自我意识并非固定在我们的基因构成中,而是在胎儿免疫系统发育过程中习得的——这就是为什么它在那个阶段可以通过接触异体细胞而改变。一位名叫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Frank Macfarlane Burnet)的澳大利亚病毒学家早已预料到这一点;正是他首次提出了自我/非我模型的理论公式。1960年,梅达沃和伯内特因其开创性工作分享了诺贝尔医学奖,他们的工作为移植生物学铺平了道路。如今,所有的器官移植都离不开组织仔细匹配——即免疫自我的匹配——以及服用抑制对外来器官免疫反应的药物。
然而,“自我/非我”模型自梅达沃和伯内特时代以来已变得更加复杂。免疫学家现在知道,例如,排斥异体皮肤移植的责任在于T细胞——免疫反应的中间人,如果反应不停止,它们必须针对特定目标被激活。甚至有一个标准理论来解释T细胞在异体皮肤上识别为异体的物质:一种独特的分子标志,称为MHC,即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是一组蛋白质,存在于几乎所有体细胞表面,其功能是提供细胞内容物(包括正常蛋白质,以及如果细胞被感染,则为病毒蛋白质)的展示窗口。但由于MHC本身的结构因人而异,它被认为是“自我”的标记。因此,免疫系统将带有病毒蛋白质(由自身MHC显示)的细胞视为异体。它将皮肤移植视为异体,因为它们含有显示非我MHC的细胞。
T细胞如何学习什么是“自我”和“非我”?长期以来的解释是,未成熟的T细胞在骨髓中产生后,会进行一场巧妙的“试镜”,它们从骨髓迁移并穿过胸腺,胸腺是一个位于胸骨下方的小而灰色的腺体。T细胞在那里遇到的是胸腺细胞表面的蛋白质-MHC复合物,这种表面装饰与身体大多数细胞的表面非常相似。理论认为,对任何这些蛋白质做出反应的成熟T细胞——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因为T细胞是大量产生的——都会被自动杀死。只有那些不对自身蛋白质做出反应的T细胞才能存活下来,并迁移到血液和身体各处。在那里它们可以攻击任何“非我”的东西——比如皮肤移植。
虽然T细胞的这种淘汰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伴随终生(就像一个人的心理自我意识总是在不断完善),但大部分被认为发生在早期发育阶段。此外,在那个形成阶段,幼年T细胞无法被激活。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梅达沃的新生小鼠没有排斥异体血细胞的原因。当然,梅达沃当时对T细胞一无所知,对MHC也只有一点点了解。但他和伯内特的基本见解——免疫系统的职责是区分自我与非我,并且它主要在胎儿发育过程中学习什么是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挑战。只是波莉·马辛格现在正在挑战它。
在他的自传《思考的萝卜回忆录》中,梅达沃描述了轰炸机坠毁对他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他写道,回想起他在牛津大学担任年轻讲师时无忧无虑的日子,他现在明白了自己浪费了多少时间在不重要的项目、智力消遣和幻想上。此后,他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伯内特所描述的自我/非我识别问题上。马辛格的职业道路也是间接的,尽管她进入免疫学领域所需要的刺激比飞机失事要小得多。在罗伯特·施瓦布将她指引回学校后,她最终成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生物学研究生。为了满足她的博士学位要求,马辛格必须设计一个实验,她正在寻找一个可以研究的想法。1976年的一天,她正在和朋友、索尔克研究所免疫学家罗德尼·朗曼(Rodney Langman)下棋,他建议她探索T细胞是如何变得如此有选择性地响应——当时刚刚发现——T细胞是如何变得如此有选择性地响应的。马辛格回忆说,那是在和罗德争论的过程中,我产生了我的第一个创造性科学思想。
然而,马辛格对她所选择的领域的理论基础了解得越多,她就越感到不满。“变化是生命的标志,”她说,“然而基于自我/非我识别的模型似乎无法解释为什么当我们的身体发生变化时,免疫系统不会杀死我们。当我们经历青春期时会发生什么?一个小时候从未被母乳喂养的女性生了第一个孩子并开始泌乳时,为什么泌乳的乳房不会被排斥?身体的变化也不是自我/非我模型难以适应的唯一问题。例如,为什么成熟的T细胞不经常攻击它们在胸腺中从未接触过的蛋白质,比如皮肤、大脑和肝脏细胞上的蛋白质?”
一些研究人员已经提出了答案的萌芽。他们假设,激活一个T细胞需要更多条件,而不仅仅是与它在另一个细胞表面识别的蛋白质结合。不知何故——研究人员在细节上存在分歧——除非它也接收到第二个信号,否则它不会被激活。第二个信号可能来自同一细胞分泌或携带的分子,也可能来自不同的细胞。无论机制如何,这个模型的基石是只有当第二个信号存在时,T细胞才会增殖并开始攻击。
反之,任何时候T细胞接收到第一个信号而没有第二个信号,它就会被失活。这就是潜在的自攻击T细胞在胸腺中被淘汰的方式,但淘汰过程会随着那些离开胸腺的T细胞而继续。当T细胞在血液中循环时,它们会接触到在胸腺中从未见过的蛋白质,比如说皮肤细胞表面上的蛋白质。当它们在没有第二个信号的情况下与这些蛋白质结合时,它们就会死亡。但如果它们确实接收到第二个信号,它们就会被激活并前往淋巴结——免疫系统的消防站——并激活其他免疫细胞。
但第二个信号的本质是什么?一直没有一个好的答案。不过,目前的共识是,它来自一类被称为抗原呈递细胞(APCs)的细胞。抗原是免疫细胞可以结合的分子,抗原呈递细胞包括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是清除细胞;它们在组织中游走,吞噬死细胞——但也吞噬细菌,它们会将细菌碎片显示在表面,T细胞可以在那里检测到它们。树突状细胞是最近发现的APC,也是最神秘的。它们被认为是抵御病毒感染的堡垒,散布在淋巴组织以及身体的其他组织中。
APC会在其表面产生某种能够激活T细胞的分子:这就是第二个信号。当T细胞与这样的APC结合时,T细胞会增殖并开始攻击那些显示MHC-蛋白质复合体的细胞——被病毒感染的细胞、外来皮肤细胞或其他细胞。在短时间内,被激活的T细胞可以在没有额外刺激的情况下杀死这些细胞;然后它们会安静下来。但只要病毒持续产生——并激活APC——这些T细胞就会持续被重新激活。最终,在病毒被清除后,病毒特异性T细胞会安静下来,这些细胞会作为记忆细胞存留。它们需要额外的刺激才能再次杀死,但下次遇到相同的病原体——或者像梅达沃观察到的,相同的异体皮肤——时,它们会更快地做出反应。
双信号理论听起来很不错。但正如马辛格所指出的,它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APCs到底如何避免启动自身免疫反应?与T细胞不同,它们没有经历过筛选过程;它们无法区分哪些抗原是自身,哪些是非自身。例如,巨噬细胞不断吞噬死亡的组织细胞。如果它们随后激活T细胞,我们就会面临持续的对自身组织的免疫攻击。马辛格说,这20年来一直是一个主要的症结。如果APCs无法区分自我与非我,那么它们就不能成为控制免疫反应的细胞。另一方面,如果你已经得出结论,免疫系统并非区分自我与非我,那么APCs的无差别性质就完全不是问题了。
马辛格并非在职业生涯之初就得出这个结论。有一段时间,随着她逐渐融入免疫学主流,她埋藏了对“自我/非我”模型的疑虑。后来在1989年,一位名叫埃弗拉姆·福克斯(Ephraim Fuchs)的年轻科学家来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邻近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福克斯现在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肿瘤学家,他最初也有与马辛格十年前同样的疑虑。马辛格回忆说:“那时我已经戴上了老学究的眼镜。但这里有一个聪明、训练有素的人,他对这个模型有着和我一样的问题。他不认为免疫系统能够区分自我与非我。这又重新唤醒了我所有的想法。”
福克斯提醒马辛格,所有证据都表明,如果免疫系统是为了抵御外来者而设计的,那么它就是一个相当松懈的边防卫兵。母亲不会排斥胎儿,更不用说她们自己的泌乳乳房;我们没有人攻击我们吃的食物,尽管食物中充满了异源抗原;我们也不会排斥寄居在我们肠道内的数百万细菌。事实上,有些细菌会产生帮助我们血液凝固的维生素K。福克斯认为,总的来说,感染并非总是坏事;例如,病毒可能会给我们提供我们否则永远无法获得的有用基因。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一个采取观望态度的免疫系统可能比一个彻底驱逐所有入侵者的免疫系统更有优势。
这让马辛格和福克斯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免疫系统不区分自我与非我,那它在做什么?马辛格回忆道:“就在那时,我们想到了一个想法,一个能区分危险与非危险的免疫系统,比一个区分自我与非我的系统要明智得多。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弄清楚它如何做到这一点。”
有一天,马辛格在浴缸里想到了答案。她意识到,免疫系统检测危险的一种自然方式,就是检测身体某个地方的组织细胞何时遭受了可怕的死亡。细胞“谋杀”与正常的细胞死亡不同。当细胞正常死亡时,它会萎缩并显示信号,邀请巨噬细胞吞噬它。死细胞的内容物永远不会释放到细胞外环境中。但当细胞被感染或以其他方式杀死时,它们会泄漏,将其内部物质散布到各处。这几乎是身体受到攻击的最好信号。
现在马辛格只需要某种能够检测到警报的哨兵。答案在马辛格训练她的一只狗时浮现出来——她至今仍在训练获奖的边境牧羊犬。在一次训练间歇,马辛格坐下来,看着她的学生卷起身体,鼻子埋在尾巴下睡着了。她想:我需要一只牧羊犬,当狼群袭击,羊群——受伤的细胞——开始咩咩叫时,它能醒过来。树突状细胞,这种最不为人知的抗原呈递细胞,正是为这种免疫哨兵的角色量身定制的。所有组织都布满了它们;它们长长的手指状延伸物——树突——伸入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形成一个网状结构。在正常情况下,它们静静地休息。但当树突状细胞被某种东西激活时,它们就会动起来:它们实际上会在组织中爬行。而它们的典型目的地是淋巴结。
很快,整个事情在马辛格看来都清晰了。她想,也许激活树突状细胞的是危险——由过早死亡的细胞在组织中漂浮所发出的危险信号。也许它们提供了促使树突状细胞发出警报的信号。这个场景不难想象。在某个组织中,一个细胞惨死——也许是一个被水痘感染撑破的皮肤细胞。病毒蛋白和皮肤蛋白都从细胞中溢出。附近的树突状细胞感知到危险,不知何故被激活,开始吞噬垂死细胞的内容物。然后它开始爬向最近的淋巴结。
在那里,像一个称职的APC,树突状细胞呈递抗原——它在表面展示病毒蛋白和皮肤蛋白。能够识别这些标志性蛋白质的T细胞会与之结合,从而获得第一个信号。但在前往淋巴结的途中,树突状细胞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其所吸收的细胞死亡证据的促使,在表面产生了另一种物质,这是一组身份仍在研究中的分子之一。这种物质为T细胞提供了第二个信号:它告诉它们“行动起来”。它们迅速增殖,然后分散开来,寻找被病毒感染的细胞进行杀灭。最终,它们消除了病毒。其中一些细胞作为记忆细胞保留下来,以便在病毒下次入侵时更快地做出反应。
马辛格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免疫反应必然会造成附带损害。一些T细胞——那些碰巧与树突状细胞表面上的皮肤蛋白结合而不是水痘蛋白结合的T细胞——不会前往受感染的组织;它们只是前往皮肤。它们甚至杀死了一些完全健康的皮肤细胞——但随后它们会安静下来。在这种状态下,除非再次受到第一和第二信号的刺激,否则它们无法杀死。只要感染持续,它们就很可能再次被激活。但一旦感染清除,它们就会安静下来。当它们在这种情况下与皮肤蛋白结合时,它们只接收到信号一而没有信号二。这会杀死它们。
在“自我/非我”模型中,T细胞也只接收到信号一而死亡,这就是自攻击T细胞被清除的方式。该模型与马辛格模型的区别在于清除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在“自我”模型中,大部分清除发生在生命早期,在胸腺中。在“危险”模型中,清除则持续发生。每当T细胞与组织中的蛋白质结合但未接收到信号二——即没有危险时——它们就会死亡。由于我们的组织持续提供大量的信号一,这种死亡在生命中不断发生,因为T细胞在血液和淋巴结中循环。马辛格说:“我们不断地对自身蛋白质产生耐受性。”换句话说,“自我”不断被重新定义——这又意味着它根本不存在。
说免疫系统只对真正的危险做出反应,这为它为什么不攻击胎儿、肠道细菌或其他应该被认为是“非我”的有用物质提供了自然的解释:这些东西不危险,它们不会使细胞破裂,也不会激活树突状细胞。但为什么它有时会攻击那些它应该认为是“无害”的东西呢?为什么会发生自身免疫性疾病?马辛格有一个答案,尽管这是一个推测性的。传统观点认为,自身免疫性疾病是由免疫系统的错误引起的——本质上是由于自我意识发育不完善。但马辛格认为,在免疫反应没有缺陷的患者中,有几种可能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方式。
一种可能性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难以检测、生长缓慢的感染。类风湿关节炎和多发性硬化症患者常有间歇性发作;这可能是病毒感染的结果,其中T细胞被激活对抗正常的身体蛋白质。当感染清除后,自身免疫反应就会平息。另一种可能性是,一个人的MHC的某个片段可能与病毒蛋白质不幸相似。因此,与病毒的搏斗可能会激活对个人MHC的持续T细胞反应。在这两种情况下,免疫系统都在响应真实的危险信号。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组织本身正在引发持续的免疫反应——可能是由于某种导致细胞异常应激或死亡的基因缺陷。马辛格指出,调节正常细胞死亡的基因缺陷会导致小鼠红斑狼疮。
那器官移植呢?为什么它们常常被排斥?马辛格说,有些人反对说我的模型行不通,因为移植的肝脏并不危险。但器官移植时会发生什么呢?它们被切割并重新连接。所有这些手术都会造成损伤。供体器官中的树突状细胞开始向淋巴结进发。在那里,它们与从未见过供体器官MHC的受体T细胞结合。T细胞被激活并开始攻击供体器官。
事实上,马辛格的理论可以解释近20年来一直困扰免疫学家的移植实验结果。在1970年代早期,两位研究人员成功地将一只小鼠的组织移植到另一只无关小鼠体内,而无需使用免疫抑制药物。为什么会成功呢?在移植之前,供体组织中的乘客白细胞已被清除,一些人认为这些细胞会激发宿主免疫反应。研究人员现在知道,这些细胞实际上是树突状细胞——它们于1973年首次由洛克菲勒大学的研究人员拉尔夫·斯坦曼(Ralph Steinman)和赞维尔·科恩(Zanvil Cohn)分离出来。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马辛格如何重新解读梅达沃的开创性实验。她解释说,梅达沃的轰炸机飞行员以及后来的兔子排斥皮肤移植的原因,并非仅仅因为皮肤移植是异体的,而是因为它含有活化的树突状细胞。皮肤中遍布着它们。马辛格说,如果你取一块皮肤放到培养皿中,仅仅是切口造成的淤青就足以激活局部树突状细胞,它们就会做它们该做的事情,那就是离开。事实上,那是一个很好的纯化它们的方法,因为它们会爬到你的培养皿里。
相反,马辛格说,梅达沃刚出生的小鼠之所以没有排斥他注射的白鼠血细胞,并不是因为它们的自我意识仍然可塑:而是因为注射没有给它们明确的危险信号,因为它没有包含足够的活化树突状细胞来唤醒刚出生小鼠体内少量T细胞。它所包含的是干细胞——产生所有类型血细胞的细胞——这些干细胞在棕色小鼠的骨髓中安家落户,为它们提供了终身供应的白鼠血液。刚出生的棕色小鼠对这种血液及其显示的MHC产生了耐受性,就像它们对自己的MHC产生耐受性一样——任何能够对其作出反应的成熟T细胞都只接收到信号一而没有信号二,并迅速死亡。当梅达沃将白色皮肤移植到它们身上时——从而以活化树突状细胞的形式向它们提供了大量的信号二——周围已经没有T细胞能够对其作出反应。所以小鼠耐受了移植。
但马辛格强调,这种耐受性并非它们在新生儿时期学到的。最近,她、福克斯和他们的同事约翰·里奇(John Ridge)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重复了梅达沃的实验。但他们没有像梅达沃那样向新生小鼠注射异体血细胞,而是注射了活化的异体树突状细胞——比梅达沃最初注射的量要大得多。如果“自我/非我”模型是正确的,这种改变不应该产生任何不同;如果给予得足够早,当小鼠的自我意识仍在发展时,任何异体细胞都应该被耐受。但事实并非如此。马辛格的小鼠排斥了树突状细胞。她说,实验表明新生小鼠的免疫系统并非天生具有耐受性。它们能够对危险作出反应。
波莉·马辛格正确与否,在实践中有什么区别吗?可能有的。一个可能受到影响的领域是移植生物学,正是这个领域激励了梅达沃。当前的移植程序,源于“自我/非我”模型,要求外科医生仔细匹配供体和受体的MHC,并用强力药物抑制免疫反应。但如果树突状细胞的激活能够被控制,有一天可能在不那么在意供体是谁的情况下进行器官移植,并且无需让患者承担高风险药物的副作用。
一种方法可能是在移植前耗尽供体器官中的树突状细胞——尽管这很困难,因为树突状细胞往往深埋在组织内部。另一种解决方案可能是制造能够与树突状细胞结合并阻止它们在受体中激活T细胞的抗体。一些研究已经表明,此类抗体可以阻断免疫反应——并促进接受移植组织的动物的长期耐受性。
危险模型也可能对癌症治疗产生影响。免疫系统对癌细胞的“失明”是出了名的,而马辛格认为,原因在于肿瘤生长并不会损伤组织。但癌变生长可以通过反复损伤癌组织来控制,从而不断重新唤醒免疫反应。事实上,研究人员目前正在开发一种含有热休克蛋白(细胞在受到应激时产生的一种物质)的癌症疫苗。通过将热休克蛋白注射到肿瘤中,他们希望刺激针对肿瘤的持续免疫反应。
然而,考虑到马辛格正在挑战一个根深蒂固了半个世纪的理论,人们对她的危险模型的反应褒贬不一,这并不奇怪。她说,移植生物学家和外科医生普遍给予好评。例如,澳大利亚约翰·柯廷医学研究学院院长凯文·拉弗蒂(Kevin Lafferty)就是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拉弗蒂是首批提出免疫反应双信号模型的人之一,他也进行了一些小鼠移植实验,这些实验可以通过危险理论得到很好的解释。
拉弗蒂说,免疫学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为“自我/非我”识别建立一个理论解释。但也许我们一直走错了路——如果事情不吻合,就该改变隐喻了。我认为我们在免疫学领域正处于这个阶段,我认为这正是波莉非常有价值的地方。不过,这还需要一段时间。人们不会那么快接受这一点。
事实上,许多免疫学家并没有完全接受它。有些人同意免疫系统可能对危险信号敏感,但指出马辛格尚未真正努力确定这些信号是什么。当然,一些激活T细胞的分子已经为人所知,但没有人知道受损组织中的哪些物质激活了树突状细胞。另一些人认为免疫系统没有理由不能两者兼顾:为什么它不能在生命早期通过胸腺中T细胞的仔细淘汰来发展基本的自我意识,同时在之后仍然对危险做出反应。还有一些人认为整个争论是语义上的——马辛格只是找到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免疫系统所做的事情,一种不会改变任何重要事物的方式。朗曼(Rod Langman),这位将马辛格引入该领域的索尔克研究所免疫学家,就属于这最后一批人。
马辛格觉得最后一批批评者最难理解。她说,至少没有人扔烂番茄。但是那些说‘哦,波莉没说什么新鲜事。她所做的只是将我们已知的一切很好地综合成一个有效的模型’的人——他们并没有真正和我一起跳下悬崖。他们没有说,‘这意味着自我/非我模型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