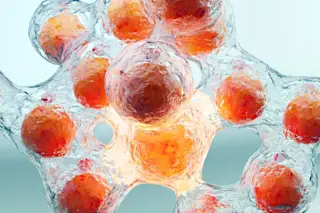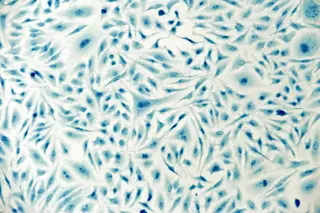1984年,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法医人类学家诺姆·索尔接到州警的电话。有人在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尸体。这具腐烂的尸体呈现出无名凶杀案受害者的典型沉默特征:现场没有衣物,没有个人物品,甚至没有足够的软组织可以轻易识别其性别。警方只知道这具尸体是人类。他们问索尔是否能恢复这个人的已分解的身份——将“它”变回“他”或“她”。
索尔开车来到停放尸体的医院。他检查了骨骼的形态和结构,重点关注头骨和骨盆,然后用卡尺进行了多次测量——例如,眼眶之间的距离、头骨的长度和宽度——并将它们输入标准法医方程。几个小时内,他能够告知警方,这具骨骼是一名黑人女性的,身高在5英尺2英寸到5英尺6英寸之间,死亡时年龄在18到23岁之间。她已经死亡六周到六个月之间。有了这些信息,警方能够将失踪人员档案的搜索范围缩小到少数几起案件。一些不寻常的牙齿修复完成了这个谜团:这具骨骼属于一名居住在两个县之外、失踪了三个月的女性。她身高5英尺3英寸,19岁,是黑人。
年龄、性别、身高和种族是初步法医报告的 cardinal points,是重建特定人类身份的基石。这四个特征中有三个 firmly anchored in empirical fact。一个人的性别、年龄和身高在任何特定时刻都是离散的数量,而不是需要解释、修订或分解为组成部分的问题。我身高6英尺1英寸还是5英尺3英寸,不取决于谁拿着尺子。如果我在密尔沃基是男性,我在莫比尔仍然是男性。我的年龄,不管喜不喜欢,是43岁;无论如何调查我的个人历史,都不会揭示我主要是43岁,混入了一些64岁,以及我母亲一方的微量19岁。
然而,第四个基石——种族——却深陷于生物、文化和语义的泥潭之中。在美国,大多数被认为是黑人的人的祖先都可追溯到西非;但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平均每个非洲裔美国人的基因物质中约有20%到30%是由欧洲或美洲印第安祖先贡献的。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对种族进行分类——不同的个体也是如此。大多数美国人可以决定在表格上勾选哪个种族选项,他们的决定可能取决于他们是在填写助学金申请表还是乡村俱乐部会员申请表。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在1970年代初期,连续两年参加人口普查调查的人中有34%在一年内改变了种族类别。
分类本身是显而易见的。负责监督联邦政府统计数据收集工作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最近举行了公开听证会,目前正在阅读关于人口普查局所用类别的书面意见。除了目前已有的种族类别——白人、黑人、美洲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亚洲或太平洋岛民,以及“其他”——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正在考虑增加夏威夷原住民、中东人和认为自己是多民族的人的选项。如果这些类别被添加,它们将在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启用。
“种族应该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学范畴,相当于动物亚种,”耶鲁大学人类学家乔纳森·马克斯说。“问题是人类也将其用作文化范畴,而将这两者相互分离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它有多重要?它是根植于我们文化中的观念,还是存在于我们基因中的现实?科学家是否应该放弃这个词,或者仅仅是抛弃它就会阻碍任何帮助公众理解人类多样性真正本质的尝试,迫使我们在街头,在充满偏见的民间传说中寻求我们的定义?
所有人都同意,所有人类都属于单一的生物物种,即智人。既然我们都是同一物种,根据定义,我们都能够与所有其他异性人类杂交,产生可育后代。然而,实际上,人们并非随机交配;他们通常在眼前的社会群体或人群中选择伴侣,而且已经这样做了几百年。因此,从不断扩展的父母和祖父母链(他们大多生活在同一地区)继承的基因的物理表现也倾向于聚集,导致皮肤颜色、发型、面部形态、身体比例以及许多不那么明显特征的地理区域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因此,粗略地说,种族是地理和遗传相互作用所创造的,一个人在人类主题上变化的一部分。
这个定义的问题在于人类变异模式的传统包装和感知方式。过去,大多数人类学家毫无疑问地接受了种族是固定实体或类型的概念,每一种都纯粹而独特。这些类型被视为巨大的遗传“蒲式耳筐”,人们可以被分类其中。诚然,蒲式耳筐的边缘可能不够坚固,无法阻止一些内容物溢出并与地理上相邻的筐混淆。在十六世纪,欧洲殖民主义开始将基因从一个筐弹射到世界其他地方;此后不久,大量非洲人被迫进口到美洲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但在最近几十年之前,人类学家认为,无论多少种族间混合都无法稀释种族理想本身的纯洁性。
在蒲式耳筐方案中,种族是由一组物理特征定义的,这些特征在特定地理区域内以某种可预测的程度聚集在一起。例如,亚洲人通常被认为是“黄色”皮肤,宽而扁平的颧骨,内眦赘皮(眼睛角落上的小皮褶),直黑发,稀疏体毛,以及“铲形”门牙,等等这些独特的特征。而且,如果你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时不时地窥视人们的嘴巴,你确实会发现这些特征的出现频率很高。
但在马尼拉、德黑兰或伊尔库茨克——所有这些城市都在亚洲——尝试同样的测试,你的亚洲蒲式耳筐就会开始瓦解。当我们想到“亚洲人种”时,我们实际上只想到那个广袤大陆的有限地区的人。当然,你可以用一系列更小的筐来代替那个破旧、超载的蒲式耳筐,每个筐代表一个更局部的区域及其人口。然而,快速浏览一些所谓的亚洲特征,就会明白为什么任何数量的次大陆筐都无法胜任这项工作。例如,远东的大多数居民都有内眦赘皮——但南部非洲的科伊桑人(“布须曼人”)也有。铲形门牙——这个词指的是前牙背面略微凹陷的形状——确实在亚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嘴中比其他人更常见,但它们在瑞典也经常出现,而瑞典很少有人有粗直黑发、内眦赘皮或身材矮小。
人类变异的直接生物学事实是,没有哪个性状是内在的、必然相互关联的。形态特征确实因地域而异,但它们是独立变化的,而不是成套出现的。“我告诉我的学生,我可以把整个世界分成两组:大鼻子的人和瘦鼻子的人,”诺姆·索尔说。“但接着我开始考虑其他特征,比如肤色、眼睛颜色、身高、血型、指纹等等。没过多久,班上就有人明白了,说:‘等等!很快你就会有一个只包含一个人的种族了。’”
事实上,尽管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存在明显的身体差异,但绝大多数人类遗传变异发生在群体内部,而不是群体之间。根据哈佛大学遗传学家理查德·列万丁在1972年进行的一项经典研究,只有约6%的变异可以归因于种族。换句话说,在遗传上将我与一个典型的非洲人或爱斯基摩人区分开来的,也同样将我与另一个具有欧洲血统的普通美国人区分开来。
但是,如果蒲式耳筐的种族观点站不住脚,那是否意味着种族的概念不具备生物学现实呢?“如果我从撒哈拉以南非洲找一百人,从欧洲找一百人,再从东南亚找一百人,剥去他们的衣服和其他文化标记,然后随机找一个人去把他们分类,我不认为他们会有任何困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文森特·萨里奇说,他自1960年代末以来一直是生物人类学界的争议人物,最近则是因为他对种族问题的看法。“现在流行说没有种族。但这很愚蠢。”
当然,土生土长的尼日利亚人与挪威人长相不同,而挪威人又与亚美尼亚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长相不同,这确实是真的。但如果能看到全人类的整个光谱,这些差异还会同样明显吗?由于人们倾向于与他们所在地附近的人交配,因此不同区域之间各种基因的频率以及它们所编码的形态特征应该只会逐渐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变异是跨空间遗传变化无缝连续的结果。另一方面,种族概念将人们归入清晰界定的群体。密歇根大学人类学家洛林·布雷斯说,这纯粹是一种历史现象。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远洋运输的发明,种族的概念才出现,”布雷斯解释道。即使是最爱旅行的世界探险家——像马可·波罗或十四世纪的阿拉伯探险家伊本·白图泰——也从未从种族角度思考,因为步行和骑骆驼旅行很少能让他们一天走超过25英里。“他们从未想过对人们进行分类,因为他们见过中间的一切,”布雷斯说。“当你能够登上船,航行数月,最终抵达一个完全不同的洲时,情况就改变了。当你下船时,天哪,每个人都看起来如此不同!我们传统的种族分类不是明确的人种类型。它们仅仅是旧商业贸易网络的终点。”
然而,萨里奇并不那么愿意将种族视为历史的偶然。“我不知道马可波罗是否提到了种族,”他说,“但我敢打赌,如果你能通过观察他们的身体特征来问他这个人或那个人来自哪里,他会告诉你。”
萨里奇补充说,如果世界各地人口密度均匀,那么人类多样性的所有表现形式确实会平滑分布,种族将不复存在。但人口分布并非如此均匀。在人口相对密集的大片区域之间存在地理障碍——山脉、沙漠、海洋——这些地方的人口密度必然较低。这些低人口区域充当了过滤器,阻碍了基因流动,并允许两侧形成独特、可识别的遗传模式——即种族。例如,撒哈拉沙漠对南北地区之间的基因流动构成了巨大的障碍。萨里奇指出,这些地理过滤器并未完全阻止基因流动——如果它们阻止了,就会形成独立的人类物种——但它们对人类变异模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围绕“种族”一词的层层困惑——以及其政治敏感性——难怪科学家们在定义和质疑其有用性上挣扎。“体质人类学家的调查发现,几乎一半的人不再相信生物种族的存在。”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道格拉斯·乌贝尔克说:“从历史上看,这个词的使用方式太多样化了,以至于在我们的科学中不再有用。我选择根本不定义它。我把这个词搁置一边。”
然而,另一半人认为,仅仅说你选择不定义种族并不能让它消失。“现在流行的政治言论是,‘不存在种族这种东西,’”科罗拉多大学体质人类学家爱丽丝·布鲁斯指出。“我想知道人们听到这话时会怎么想。他们会认为,如果演讲者被空降到内罗毕市中心,他将无法通过环顾四周来判断自己身处内罗毕还是斯德哥尔摩。这只会损害他的可信度。世界上不同人群之间明显的差异告诉所有人,那里确实存在一些东西。”
布鲁斯说,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讨论那“东西”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存在。“有些情况下你必须谈论一些事情,而且你必须有词语来做到这一点,”她说。“法医人类学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警察想知道,这是黑人、白人,还是印第安人?你必须使用词语。”
和索尔一样,执法机构也经常要求乌贝尔克辨认不明身份的人类遗骸。如果种族划分仅仅是文化产物,那么这两人如何如此轻易地从无肉头骨的纯粹物理证据中推断出个人的种族身份呢?他们说,答案在于地理和人口统计学。“我不认为人类变异是有系统的这种观点有问题,”索尔说。“我可以看到某人,然后说,‘你的祖先可能来自欧洲。’我知道他们不会来自南非或东亚。但这仍然不意味着将世界人口分成三组是合理的。”
索尔说,如果他1984年辨认出的那具19岁黑人女性尸体是在另一个国家发现的,他可能会得出不同的身份识别。但美国法医标准是专门设计来区分西非裔、欧洲裔、亚洲裔和美洲印第安裔的,因为这些群体构成了美国人口的大部分。考虑到骨骼的发现地点,索尔说,死者将自己识别为非洲裔美国人的可能性非常大。
“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将一个样本的地理来源缩小很多,”索尔说,“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警察有他们的表格,我希望我的表格与他们的表格匹配。”
埃默里大学人类学家乔治·阿梅拉戈斯是种族生物学概念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认为人类学家仅仅因为执法机构要求就继续使用种族类别是一种敷衍。“这在我看来不合理,”阿梅拉戈斯说。“如果我们要向人们普及种族概念,我们应该在各个层面进行。”
“让侦探参与关于人类地理变异真实性质的理论讨论并不能帮助他破案,”索尔反驳道,“我已经得出结论,如果警察想要种族,我就给他们种族。也许之后,当我们喝啤酒的时候,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种族到底意味着什么。”
与人类学家不同,研究人员似乎对种族类别的现实性几乎没有疑问。看来,种族在组织数据方面相当有用;每年都有数十篇健康期刊报告利用它来显示不同种族在疾病易感性、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和其他公共健康指标上所谓的明显差异。黑人男性患肺癌的可能性据说比白人男性高出40%,而最近一些关于乳腺癌的研究似乎表明,黑人女性往往会发展出比白人女性更恶性的肿瘤。在美国,黑人婴儿在出生后11个月内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婴儿的近两倍半。而且已经表明,美洲印第安人比黑人或白人更有可能携带一种酶,这种酶使他们更难代谢酒精;这会使他们在基因上更容易患酒精中毒。其他研究声称证明了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肾脏疾病、性病以及许多其他病理学上的种族差异。
这些研究是否指向了种族之间的基因差异,还是它们将种族作为健康缺陷的便捷替罪羊,而这些缺陷的原因应该在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环境中寻找?例如,肺癌的统计数据,确实应该与黑人男性吸烟的可能性远高于白人男性的数据一起考虑。
兰德尔·塔克特及其同事在佐治亚大学对美国黑人高血压进行的一项最新研究,就说明了试图对这类问题找到单一答案的困难。近30年来,众所周知,美国黑人患高血压(或高血压)的可能性几乎是白人的两倍——这种情况会增加心力衰竭、中风、动脉硬化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据报道,黑人男性死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比白人男性高27%,黑人女性比白人女性高55%。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仍然不明:一些研究人员将黑人高血压发病率较高归因于社会经济因素,如社会心理压力、不良饮食和医疗保健的可及性有限,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存在遗传易感性,这通常被解释为种族易感性。然而,试图追溯遗传原因已被证明比原本可能的情况更加令人困惑,因为高血压可能是多种因素的结果,从较高的膳食钠含量到增加的心理损伤暴露。
然而,去年六月,塔克特和他的同事报告了一种可能导致黑人高血压发病率较高的生理机制。他们将心脏搭桥手术中获取的静脉暴露于对组织造成压力并使其收缩的化学物质中,发现黑人静脉恢复正常大小的速度比白人静脉慢。对压力反应而持续收缩时间更长的静脉会减少血液流动,并要求心脏更努力地工作——这就是高血压的本质。“这是首次直接证明血管层面上存在种族差异,”塔克特说。
希望这些发现能促使医学界更加积极地治疗黑人高血压,从而挽救生命。但这些发现是否真正说明了种族在疾病中的作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塔克特的非洲裔美国人样本仅限于来自佐治亚州南部的22个人;来自洛杉矶或纽约的黑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和具有不同的遗传历史,是否会表现出相同的血管损伤?那些与美国黑人不同、通常高血压发病率极低的非洲本土居民呢?芬兰人和俄罗斯人呢,他们的发病率很高?这些发现对他们的种族说明了什么?即使美国黑人对高血压的易感性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血管,而不是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谁又能说这些不平等——美国白人从未面临的环境压力——不是导致长期、可能致命的血管收缩的触发因素呢?难道导致血管、血压和心脏病链式反应的锚点不是种族,而是种族主义吗?
毕竟,列万丁二十多年前的研究表明,种族概念并没有多少遗传上的影响力。“我不否认塔克特看到的差异是存在的,”阿梅拉戈斯说,“但种族只解释了人类生物变异的6%。他怎么能如此确定这6%就解释了病理学呢?”
自 Lewontin 1972 年的研究以来,基因分析技术已经大大改进;尽管种族只占遗传差异的一小部分,但现在通过查看 DNA 样本来区分不同人群并定位个体变得更容易一些。当然,仍然存在局限性。“如果你让我看一个样本,然后说它来自威尔士还是苏格兰,那会很困难,”罗格斯大学的人群遗传学家彼得·斯莫斯说。“但如果你问我一个人来自挪威还是台湾,当然,我能做到。地球上人类的基因变异非常巨大,几乎肯定反映了我们存在和传播的时间有多长。现在,这些堆积是否整齐就不那么清楚了;对于想堆积的人来说,它们可能没有那么整齐方便。”
斯莫斯说,归根结底,没有人会否认人群之间存在基因差异。但与例如黑猩猩和人类之间的差异相比,这些不同之处就变得“完全微不足道”了。这完全是个视角问题。
“你对种族的看法取决于问题是什么,”斯莫斯说,“以及谁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