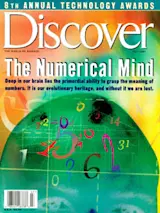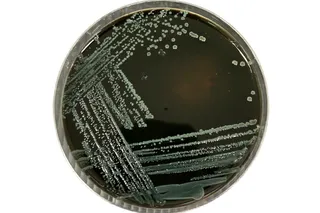医疗放行?我走进7号病房时停下了脚步。里面,一名儿童保护服务社工正在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男孩只穿着一件男士格子衬衫;女孩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白色套裙。有人一定举报了这两个孩子涉嫌被遗弃。他们来急诊室是为了做一次短暂的体检。
是疏忽还是虐待?我问道。
我们认为是疏忽,社工回答。妈妈把他们丢在了公交车站。
她说她会回来,但她再也没回来。社工伸出手去摸女孩。这是Tonya。她四岁。这是Raymond。他两岁。
Raymond仰望着我,一只手紧紧抓着社工的裤子。他似乎永远不会放手。我拉开他的衬衫,检查了他的胸部和背部,寻找伤痕。在我看到的最后一个虐待儿童案例中,一个小女孩的背部散布着圆形的一度二度烧伤。烟头烫的。不过这个孩子看起来没事,就是脏。
我跪下来看他的姐姐。你怎么样,小鬼?她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活泼开朗。
我四岁了,她说,并伸出了三根手指。
哦,那可真大了,我笑着说,对于大孩子我们有大惊喜。我们有姜汁汽水。你想要点吗?
她点点头,眼睛睁得大大的。
怎么说?社工提示道——一种本能的母亲行为。
小女孩笑得更灿烂了,害羞地低下头。闭嘴,她说。闭嘴,闭嘴,闭嘴。
我抬起头看向社工,惊讶得下巴都掉了。
你简直不敢相信这些孩子会说出些什么,她说。
小女孩转向她的弟弟,推了他一把。闭嘴,你这个笨蛋婊子,她说。给我拿瓶啤酒。
虐待儿童,遗弃儿童。对医生来说,诊断被虐待儿童最困难的部分之一就是简单地做出诊断。在急诊室,这可能更困难,因为诊断往往必须在观察一两分钟后才能做出。我学到的一条经验是,要对任何带着受伤的孩子来到急诊室并急于离开的父母保持警惕。
一个炎热的夏夜,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一位母亲拉着她大约五岁的儿子的胳膊——她把他拖到了我跟前。
还要多久?她问道。
很明显,我们都在尽力而为。我刚给一个药物过量服用抗抑郁药的人插了管,然后急忙去看一个心力衰竭的女人。从我站的地方,我可以看到那个女人躺在床上挣扎呼吸的房间,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坐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
女士,我说,还要等一会儿。
好吧,我没时间了。我儿子受伤了。她语气中的某种东西让我停顿了一下,看了看她。
亲爱的,我说,今晚这里的每个人都很不舒服。
别叫我“亲爱的”。我要去另一家急诊室。我等了两个多小时了。我要得到服务。
值班护士Ed急匆匆地走了过来。我十分钟前才把你安排到那个房间。他强调地指了指他的手表。所以别跟她说你等了好几个小时。他走到我身边,在我耳边低语,我担心这个孩子。
我跪下来看那个哭泣的孩子。他的前臂显然骨折了——桡骨。桡骨中段有肿胀,远端的胳膊以一个角度倾斜。这很奇怪。人们摔倒时,通常会在手腕附近骨折前臂。骨头中间的骨折更为罕见,通常是钝器造成的。它们被称为警棍骨折,因为人们在自卫时会被警察的警棍打伤。这个孩子就有这样的骨折。
这怎么发生的?我问那个男孩。
他看了看他的母亲,又看了看我,然后默默地退开了。
我要走了,母亲说,一边拉着孩子另一只胳膊。他只是站在那里,双脚像生根一样钉在地上。
等等,我说。我需要知道。
别跟我说什么“等等”。我要带走我的儿子,我要走了。
我看着她。我见过上千个好母亲,她们看起来都像她一样,但外表什么都说明不了。当我从跪着的地方抬头看她时,我确信——嗯,大概确信——她伤了她的孩子。
我跪在那里片刻,犹豫着。毕竟,我有什么证据?再说,她要去另一家急诊室。她是这么说的。但我很生气。我生她的气,因为她扯扯她的孩子,而且如此不讲道理。
对不起,我说,站了起来。我意识到我正站在这个女人和出口之间。你不能带那个孩子走。
她瞪着我。什么意思?
你不能走,我说。任何父母,无论是虐待儿童的还是圣人,都会对这个命令感到愤怒,但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我已经表明了我的立场。
你的意思是,我不能走?
你可以走,但孩子不能。
你疯了。她在我面前摇晃手指,用力拉扯着男孩的胳膊。
我更生气了,非常生气——仿佛整个场景都被鞭炮照亮了。
这孩子留在这里,我说。
你,她强调地重复道,疯了。她又一次用力拉扯儿子的胳膊,但这次他从她身边挣脱开,惊恐地看着我们俩。
你不能走,我大声说。在我们弄清楚这里是怎么回事之前,你不能走。
她试图从我身边经过。
叫保安,我说,转向Ed。我没注意到他已经去处理一个头部受伤流血的醉汉了。我在走廊里孤身一人,没有支援——计划非常糟糕。如果我跑向柜台,她在我找到人之前就会跑出去了。
Maggy,我对着值班员大喊,叫保安。
这是我儿子,女人喊道。我怎么对他都可以。
男孩在哭,试图躲避她。她又一次拉扯他的胳膊。
我告诉你。我花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是我在喊。我告诉你,你什么都不能做。你不能伤害孩子,在我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前你不能走。如果你走了,我就让警察来抓你。
警察!她喊道。你根本不知道。所以别想威胁我。
她向我打来,我躲开了。在那一刻,鞭炮熄灭了。我愿意引起骚动,但我没准备好被袭击。我退后一步,但她跟着我,挥舞着空闲的手,试图抓住我的衣服。她踢了我,刚好踢到我膝盖侧面。当我倒下时,我看到她伸出的脚踢向我的脸。当我抬起头时,我看到那个和他的母亲坐在一起的魁梧男人将她按在墙上。我站起来,开始掰开她搂着男孩前臂的手指。当我把他拉出来时,保安,就像德克萨斯骑警一样,飞奔而至。
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孩子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我把他从他母亲身边拉开。
她抢了我的宝贝,女人尖叫道。那个贱人抢了我的宝贝。
她必须离开,我对着保安大喊。她不能留在这里。
走吧,Lenny说,一个保安。那个“贱人”是医生,她说的算。你得走了。
女人站着,双手抱胸,盯着我。Ed又跑了回来——他是个大块头,不好忽视。
医生说你得走了,他说,俯视着她。我送你到候诊室,然后我们会谈谈你下一步需要做什么。
她允许Ed搂着她,但回过头来看着我说,我会找到你的,贱人。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门关上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急诊室,挤满了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沉默着。但过了一会儿,男孩开始哭泣,房间里爆发出嘈杂声。
Lenny把孩子抱回了一个隔间。我的脚踝受伤了,我一瘸一拐地跟在他们后面。
你还好吗?Lenny问我。
嗯,没事,没事,我说,但我的脚踝疼得厉害。
Lenny把孩子放在检查台上。他还在哭。
我们把这件衬衫脱下来,我说。我以为在和母亲搏斗时看到了伤痕。
我看到了。男孩的脸上有两个瘀伤,两条胳膊上都有瘀伤,椭圆形的瘀伤,大小和拇指印一样。他的背上有几十道细长的椭圆形痕迹——有些是疤痕,但有些是新鲜的,鲜红色的。那是绳索痕迹,被电线绳击打赤裸的背部和臀部造成的擦伤。毫无疑问的虐待迹象。
我用手指描摹着那些疤痕,感受着那些隆起的纹理。孩子现在只是呜咽着。一位护士给了他一个毛绒玩具。
甜心,我说,在我跪在他面前。你的胳膊是怎么骨折的?
他盯着我,一动不动。
你能告诉我吗?你不用害怕。我保证没有人会伤害你。
他的下巴在颤抖。他移开视线,说,d-d-d-d。
谁?
d-d-d-d……他放弃了,用他那只好的胳膊腕子揉了揉眼睛。
他就只说了这么多。
第二天下午,负责调查的警官Tiny过来给我做了个陈述。Tiny体重超过350磅。我几次处理过他的哮喘发作。
你觉得发生了什么?我问他。
我不能评论正在进行的调查,他告诉我。但你我之间,可能是这位太太被她丈夫打过几次,我怀疑那家伙没少动手打孩子,尤其是这个。
她为什么没有提出家庭暴力投诉?
Tiny摇了摇头。他会丢掉工作的。事实上,他已经被停职了。他是一名警察,而且车站那边出了大麻烦。显然有些人知道事情的经过,但他们什么都没说。
为什么呢?
Tiny皱起了眉头。我猜,你们会保护自己人。
会发生什么?
如果他们给他定罪——很有可能——如果他被判有罪,他就会丢掉工作。那样的话,就剩下三个孩子和妈妈了……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
我靠在椅子上,研究着天花板。救了孩子却毁了这个家有什么意义?我看了看Tiny。这是怎么发生的?谁会对孩子这样做?
嗯,Tiny耸了耸肩说,这孩子的爸爸……他是个好人什么的。我在高中时认识他。但他喝酒,一旦喝了酒,他就变得很坏。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耸了耸肩。人们有很多其他原因会打孩子,但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当涉及酒精时,人们会像任何动物一样行事。
凭着一种预感,我调出了那位警官妻子的病历。果然,有多次急诊室就诊记录,显示有轻微创伤,最后一次是在大约六个月前,因多处面部挫伤和从楼梯上摔下造成的鼻骨骨折。配偶虐待。很明显。问题是——虽然我毫无印象——但我见过她。我看过X光片;我缝合过她的伤口。但我错过了诊断。我的记录中 nowhere 提到了家庭暴力的可能性。如果我当时就做出诊断,也许有人就能在孩子受伤前进行干预。在走廊里发生这件事很久以前,我本来有机会的,但我错过了。我只能怪自己。
接下来的日子,然后是几周,我试图找出那个孩子和家人的情况,但我总是遇到死胡同。Tiny不给我任何信息。我问过的人,没有人认识这个家庭,或者承认认识。
我想知道那个男孩是否被寄养给了亲戚。他还会记得那场争吵和他的骨折吗?他的母亲呢?她是受害者吗?当我第一次看到她摔倒后,她无疑是受害者,但那天我看到她和她儿子在一起时,她是什么呢?受害者还是同谋?
那我呢?我第一次漏诊,是否也成了不知情的同谋?而我下午为那个小男孩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最终是否让事情变得更糟?我是否毁了一个家庭?一定有更好的办法,但那是什么?
那天,我采取了行动。我做了我认为必须做的事。但正如急诊医学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我永远无法真正知道我是否做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