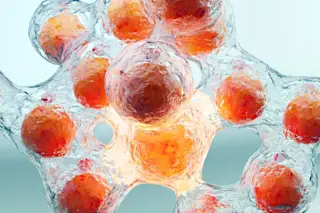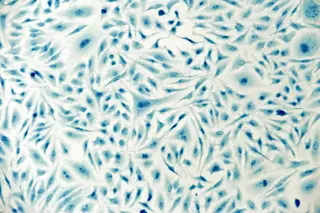“条条大路通向我,”南希·西格尔说,汽车驶入洛杉矶南部的一条居民街。在去探望一对她最喜欢的同卵双胞胎的路上,她并不是在吹嘘自己的地位。如果你是一位科学家或记者,正在研究双胞胎的特征,迟早你会遇到南希·西格尔,这位美国双胞胎学界的权威人士。
这位53岁的心理学教授是《缠绕的生命:双胞胎及其对人类行为的启示》一书的作者,书中包含了你所有想知道的关于双胞胎的信息。她为《双胞胎研究》杂志撰写每两个月一期的专栏,介绍学术界、艺术界和体育界引人注目的双胞胎,并亲自在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的双胞胎研究中心指导自己的双胞胎行为研究。
西格尔的权威部分来源于她自己也是双胞胎。她的姐姐是一位律师,住在纽约市的另一个海岸。她们是异卵双胞胎,彼此不太相似。
“啊,这一定是正确的房子,”她指着停在车道上的小货车说,“双胞胎妈妈总是有厢式车。”
房子里住着9岁的凯西和凯拉·海姆以及她们容光焕发的父母。这两个基因完全相同的女孩为了这次场合穿着相同的衣服。同卵双胞胎很容易让陌生人混淆,但有时线索在于她们的镜像特征,比如发旋方向相反或脸部两侧胎记位置相反。凯拉左脸颊上有一颗痣,凯西脖子右侧也有同样的痣。被问到时,双胞胎几乎同时说话,仿佛房间里有回声。
“你们生日是什么时候?”她们被问到。
“11月11日,”她们回答道。连月份和日期都是双胞胎。
专业人士和双胞胎父母经常谈论同卵双胞胎之间特殊的纽带——她们小时候如何在同一个无形波长上行动和交流。她们甚至可能用一种私密的语言互相交谈。西格尔和一位助手坐在海姆双胞胎对面的餐桌旁,通过名为“孤岛生存”和“囚徒困境”的游戏测试姐妹俩的合作能力。
在第一个游戏中,一道屏障放置在她们之间,每个女孩被困在自己的“岛屿”上,从一副牌中选择三张卡片。卡片描绘了她们认为生存所需的物品,比如食物或火柴。双胞胎没有选择相同的三个物品。但在游戏的第二部分,即谈判环节,这是测试谁主导谁的环节,凯西和凯拉很快就三个选择达成了一致。
在接下来的游戏中出现了非同寻常的结果。在西格尔的指示下,女孩们背对背坐着。游戏的每一轮,她们都被要求举起红色或蓝色旗帜。目标是赢得最高分。如果两人都举起相同颜色的旗帜,每人获得相同的分数。两面红旗各得一分;两面蓝旗各得三分。但如果一面红旗对一面蓝旗,举红旗的双胞胎得五分,而举蓝旗的姐妹则一无所有。因此,游戏允许竞争(如果举红旗的双胞胎出其不意地击败了举蓝旗的),或平淡的合作。
凯西和凯拉一次又一次地举起红旗。(正如她们事后回顾时承认的,她们打算互相打成平手,或者让对方赢。)但突然,在连续举起十二面红旗之后,每个女孩都举起了蓝旗。房间里的人都惊呆了。她们是怎么做到的?当游戏在25轮后结束时,她们的分数完全相同。
西格尔没有试图解释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同步结果,但她的研究表明,同卵双胞胎之间的和谐很大程度上源于共同的基因身份。也就是说,她们的合作既是习得的,也是遗传的。其他双胞胎研究者也发现了行为、个性和智力的强大遗传成分。双胞胎还揭示了心脏病和体育锻炼能力等更客观条件的遗传性。简而言之,几乎任何人类特质,当通过双胞胎的双重视角聚焦时,都可以追溯到基因的内在联系。
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的理查德·法布西茨说:“它们是大自然中一个美丽的实验。”法布西茨一直在追踪一组参加过二战的双胞胎患心脏病、中风以及现在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他们同一天出生,”他说,“在同一个家庭长大。当你研究双胞胎时,你就排除了无关因素。”
双胞胎以科学家可以剖析的方式既相似又不同,为关于先天与后天之争的长期辩论提供了素材。使用双胞胎的想法于130年前在英国萌芽,当时达尔文的表兄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写道:“他们的历史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区分出生时获得的倾向与后期生活环境强加的倾向之间的影响;换句话说,区分先天与后天之间的影响。”
“双胞胎告诉我们哪些可能受基因控制,哪些可能不受基因控制,”法布西茨解释道。“在我们拥有分子生物学工具之前,双胞胎就是早期的基因研究。”然而,作为一项工作,它有一个可怕的秘密。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纳粹扭曲了双胞胎科学,以推进他们的种族主义议程。多年来,遗传学家一直在努力克服那些怪诞实验带来的污名。
如今,在美国至少有十几个双胞胎注册机构,研究人员可以从中获取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数据。世界上最大的藏品在瑞典,存有14万对双胞胎的档案,包括已故和在世的双胞胎。丹麦国家双胞胎注册中心今年夏天正在庆祝其成立50周年,其中包括最早可追溯到1870年出生的双胞胎的健康记录。在澳大利亚,另一个双胞胎研究的领导者,研究人员对3万对双胞胎进行了调查,研究范围从她们的饮酒习惯到男性型脱发再到黑色素瘤的发病率。斯里兰卡、意大利、韩国和中国刚刚开始建立双胞胎注册机构。

11岁的杰森(左)和丹尼·巴雷特是一对患有自闭症的同卵双胞胎。两人都正在参与一项关于这种疾病的研究。
21世纪的双胞胎研究得益于新的分子技术而大放异彩。通过将国家样本整合到一个国际DNA数据库中,双胞胎研究人员希望不仅能找出人类常见疾病的基因基础,最终还能找到海姆家族独特合作方式等特质的根源。
同卵双胞胎之所以被称为单合子,是因为它们源自一个受精卵的学名——合子。受精卵结合了母亲卵子的基因和父亲精子的基因后,便开始发育成胚胎。在受孕后的两周内,一个受精卵可能会分裂成基因相同的两半。这些继续生长成为双胞胎。任何进一步的分裂都会导致单合子三胞胎、四胞胎等等。
异卵双生是由于同时排卵,两个卵子分别受精,导致两个受精卵同时发生。从基因上讲,一对异卵双胞胎的关系与普通兄弟姐妹的关系相同。唯一的区别是异卵(两个受精卵)双胞胎同时开始生命。异卵双胞胎可能是异性;同卵双胞胎在极少数情况下才是异性。
对于先天与后天研究人员来说,重要的是异卵双胞胎平均只共享同卵双胞胎一半的DNA。这允许进行一个简单的练习,称为经典双胞胎方法,科学家通过该方法比较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假设两种类型的双胞胎对同一测试显示出不同的反应,就可以计算出所研究特征的遗传和环境影响之间的比率。
该方法首次公开发表的应用是一项关于皮肤痣的研究。1924年,德国人赫尔曼·维尔纳·西门子提出理论,认为任何可遗传的疾病在同卵双胞胎中的一致性应高于异卵双胞胎。一致性是衡量两个个体相似度的一种指标。如果基因决定了皮肤痣的形成,那么拥有相同基因的兄弟姐妹在痣的数量上应该比基因混合不同的兄弟姐妹更一致。事实上,在西门子对双胞胎的调查中,同卵双胞胎——无论每个双胞胎显示出多少痣——在数量上都比异卵双胞胎更接近。这种差异被认为是痣可遗传性的证据。
正是由于环境的介入,同卵双胞胎才没有完全相同数量的痣。广义上说,“环境”是一种表达方式,说明同卵双胞胎过着非同卵的生活。细微且不平等的压力,甚至从子宫内就开始,都会导致它们产生差异。
自从比较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的方法普及以来,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在估算基因和环境对人类特质形成的相对贡献方面大显身手。因为先天与后天范式中的这两种力量可以相加来解释整体,如果你确定了其中一种,你就可以同时推算出另一种。以下是文献中任意挑选的一些结果。重要的是要记住,所有数字都来自数十或数百对双胞胎,并不描述任何一个个体。
身高据说有90%的可遗传性,这意味着环境,例如儿童时期的营养,对你长高还是长矮只有10%的影响。一般智力大约有50%的可遗传性,各种人格类别也是如此。患哮喘的风险具有一定的遗传性,这可能会让那些在环境中寻找罪魁祸首的人感到惊讶。根据一项研究,患自闭症的风险超过90%是可遗传的,因为自闭症在同卵双胞胎中的一致性很高,在异卵双胞胎中则很低。癌症的遗传成分相当低,尽管发现了特定肿瘤的基因。在经历可怕事件后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有30%与你的基因构成有关。
甚至连工作满意度这样主观的特质也受到基因的影响。你在工作中是否快乐,有70%取决于你的工作性质以及你出生以来对工作的才能和态度。但你的DNA可能会影响你对工作的看法的30%。
为了衡量先天-后天等式中环境一半的影响,双胞胎研究人员使用了第二种技术:同胞对照法。这些研究假设,如果同卵双胞胎的基因相同,但个体却有所不同,那么环境必然是决定性因素。某种疾病或关键经历发生在一个姐妹的生活中,而没有发生在另一个姐妹的生活中。
在对慢性疲劳综合征(一种主要影响女性的疲劳和疼痛疾病)长达十年的研究中,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Dedra Buchwald和Jack Goldberg将二十多对同卵双胞胎带到西雅图进行检查。研究团队此前通过一项经典双胞胎研究证实,慢性疲劳具有遗传成分。(同卵双胞胎在患病方面表现出更高的一致性。)然而,在这组特定的同卵双胞胎中,一个姐妹有症状而另一个没有。为什么?
塔米·斯潘格勒和帕姆·朱迪,她们的娘家姓是奈博格,于去年二月抵达进行测试。42岁的塔米和帕姆仍然生活在她们长大的同一个爱达荷州小镇,几乎每天都见面或通话。她们可能就是长大后的海姆姐妹。对于任何一个话题,每个女人似乎都知道对方即将说什么,情感的电流,主要是笑声,也有泪水,神秘地穿透她们对话的表面。像其他同卵双胞胎一样,她们有一个最喜欢的双胞胎故事要讲:当帕姆生第一个孩子时,身在数英里之外,对姐姐状况一无所知的塔米感到胃痛。

78岁的同卵双胞胎西摩(左)和马丁·阿萨尔诺是美国二战老兵双胞胎登记处的成员,该登记处包含26,894名老兵双胞胎的数据——11,832名同卵双胞胎和15,062名异卵双胞胎。
尽管纽堡双胞胎没有各奔东西——远非如此——但生活还是介入了她们之间。帕姆约会更多,结婚更早,辍学,先有了孩子,更注重自己的外表和穿着。塔米则继续上大学,更严肃一些,社交少一些,并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听她们讲述,两人都是精力充沛的母亲,同时处理着无数的事情。两人臀部都增重了,帕姆比塔米更多。尽管遭遇挫折,两人都很开朗。帕姆是患上慢性疲劳综合症的那位双胞胎。
在一周的时间里,双胞胎接受了医学检查和心理访谈。她们穿着肺部监测器骑固定自行车,睡觉时头骨上连接着电极,并将手臂浸入冰水冷却器中(每个双胞胎都听不到对方的声音),并报告疼痛程度。帕姆似乎对疼痛更敏感。
同胞对照法的优点在于,健康的双胞胎可以作为患病双胞胎的对照。在这种情况下,“对照”意味着将基因从等式中移除,就像两个相等的量互相抵消一样。此外,双胞胎童年环境的差异也被移除,因为假设两个女性都是以相同的方式抚养长大,吃相同的食物。首席研究员布赫瓦尔德解释道:“对于慢性疲劳综合症,哪一组是最好的对照一直很不清楚。每个人都为此挣扎。其他研究人员使用过健康人、抑郁症患者,甚至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没有人知道该用哪一组进行比较。而且这些组都没有控制环境或遗传因素。”
最终目标是掌握这种疾病的基础。如果慢性疲劳综合征有信号——一种独特的生物学或心理学特征——Buchwald和Goldberg希望同胞实验能在人类变异的噪音中检测到这个信号。迄今为止最具启发性的发现是运动时消耗氧气的能力。研究人员了解到,这对双胞胎中生病的那一个骑自行车的时间没有另一个长。当然,个人体能有影响,但一个人的最大摄氧量在很大程度上是遗传的,根据——还有什么呢?——双胞胎研究。
令人惊讶的发现是,平均而言,华盛顿大学研究中的同卵双胞胎,无论是患有慢性疲劳的还是没有患病的,其运动能力都低于正常水平。固定自行车测试提供了一个生物学线索,但它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每对双胞胎中只有一个生病。
Buchwald和Goldberg的研究是实践性实验,涉及对双胞胎的身体操作,而不是简单地观察她们的行为或询问她们的健康状况。研究人员清楚地知道双胞胎实验的丑陋历史。
二战前,苏联、英国和美国都进行过双胞胎研究,但德国是进行最先进研究的地方。当时世界上领先的双胞胎科学家是奥特马尔·冯·费尔修尔。他写了一本关于结核病双胞胎的书,认为对疾病的易感性有遗传基础。冯·费尔修尔在柏林地区建立了大量的双胞胎档案,实际上是第一个双胞胎注册处,他比较了这些孩子在肺活量和智力等方面的特征。
在20世纪30年代,冯·费尔施尔领导法兰克福遗传生物学和种族卫生研究所,他最喜欢的学生是约瑟夫·门格勒。德国科学家相信优生学。阿道夫·希特勒的狂热优生计划要求改善所谓的雅利安人种,并清除其他被认为是劣等的“人种”,尤其是犹太人。因此,冯·费尔施尔、门格勒和他们的同事受命寻找可衡量的方法来区分不同人种。
1943年和1944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进行的双胞胎研究成为这项工作的核心部分。门格勒亲自从新来的囚犯中挑选出双胞胎,并对他们进行可怕的实验。他会对其中一个双胞胎进行X光照射、输血或细菌注射,而另一个则不进行,然后寻找他们器官上的差异。他列出了不同国籍双胞胎的眼睛颜色和其他特征,试图区分哪些特征是基因固定的,哪些可能是可塑的。遗传学家现在知道这是一个注定失败的科学项目,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内部的基因变异都远远超过不同民族之间的变异。
门格勒的笔记和发现丢失了。今天从事双胞胎研究的人都说,这真是个好消息,他们大多数人都不愿谈论门格勒。二战结束后,科学家们避开了从生物学或遗传学框架来解释人们的差异。先天与后天的摆锤转向了疾病的环境原因——例如,工业污染导致癌症。自闭症被认为是糟糕的育儿方式造成的——是家庭环境的失败,而不是先天缺陷。学习和条件反射被认为是所有行为的来源,而不是基因。统计学家重新审视了关于遗传性的一系列研究,并宣称样本量过小,不足以支持先天与后天的统计数据。更糟糕的是,欺诈似乎玷污了一项著名的英国双胞胎智力研究。
双胞胎研究直到1979年才恢复。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家托马斯·布沙尔,为避免与门格勒相提并论,创立了明尼苏达异地抚养双胞胎研究。布沙尔通过系统地寻找和追踪从小分离的成年双胞胎,帮助引入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第一对受到详细审查的是著名的“吉姆”双胞胎,两兄弟于1979年重聚。他们不仅都叫吉姆(这是他们收养巧合),而且都喜欢木工,把指甲咬到最短,儿子名字相同,抽同一种香烟,开同一种车,从事同一种工作。这些双胞胎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共同经历,但他们却出奇地相似。
明尼苏达州关于智商和其他特质遗传性的研究“对于改变人们对基因和环境作用的看法至关重要,”澳大利亚人尼克·马丁(他编辑《双胞胎研究》杂志)说。“这些研究具有巨大的累积影响力。”曾受布沙尔培训的南希·西格尔指出,目前这项研究包括134对双胞胎,其中80对是同卵双胞胎。有时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来自同一家庭的双胞胎并非天生相似,而仅仅是互相模仿或从父母或同伴那里习得相似行为。明尼苏达州的设计排除了模仿和学习的可能性。
在她最近在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的研究中,西格尔比布沙尔更进一步。她组建了一组她称之为“虚拟双胞胎”的群体。这些是年龄相同但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通常都是被收养的——他们一起长大。“虚拟双胞胎共享环境但不共享基因,”她说,“这使他们成为异地抚养的同卵双胞胎的镜像。”两种类型的双胞胎——异卵双胞胎以及像海姆姐妹这样的同卵双胞胎——都与虚拟双胞胎进行比较。
在她的研究中,西格尔发现虚拟双胞胎在智商和气质上差异最大,尤其与生物学上相同的双胞胎相比。“基因与环境——人们说这个问题已经问过无数次了,”西格尔说,“但以前从未以这种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
进入新世纪,基因再次高歌猛进。如果双胞胎研究者要确定人类特质的遗传性,他们必须发现特定的基因:DNA分子中对利他主义和合作很重要,或者决定我们血压和脱发模式的片段。芬兰遗传学家莉娜·佩尔托宁说:“双胞胎研究者是一个独特的物种,他们与分子遗传学家的融合程度还不够。他们一直在单合子与双合子差异上做文章。这有点微不足道。”
南希·西格尔和尼克·马丁承认,通过双胞胎研究发现基因的进展几乎为零。因此,他们将目光投向人类基因组计划和像佩尔托宁这样操纵DNA的科学家。他们传统的低预算科学,在经典双胞胎研究中只需纸笔即可统计共同特征,现已进入基因流行病学的高科技世界,该领域追踪基因影响人群健康的能力。“我们的工作将变得不那么推论性,”西格尔说,“但这还需要一些时间。”
这种演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从吸烟方法中看出。瑞典和美国的双胞胎研究人员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吸烟行为,并适时证明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更有可能在吸烟或不吸烟倾向方面具有共同点。这是行为基因在起作用的简单证据。随着他们继续追踪数据库中的双胞胎,研究人员发现吸烟的双胞胎可能比不吸烟的双胞胎寿命更短。无论是同卵双胞胎还是异卵双胞胎都没有影响;无论共享多少基因,吸烟通常都会加速死亡。这表明环境,以香烟的形式,可以战胜任何长寿基因。
在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的SRI国际,双胞胎研究人员深入研究了吸烟的生理学,依据的理论是某些人代谢尼古丁的速度比其他人快。其理念是,快速代谢者可能更容易上瘾。根据SRI研究中不同双胞胎的反应,这种特质的大约70%被确定为可遗传的。
并且发现了一些相关的DNA。弗吉尼亚联邦大学里士满分校的一个团队最近发现,三种基因多态性——某种基因“拼写”中的变异——与尼古丁成瘾有关。作为原始材料,该团队分析了来自美国历史悠久的藏品之一——中大西洋双胞胎注册中心——的688对双胞胎的DNA。
弗吉尼亚研究团队所识别的基因并非尼古丁成瘾背后的全部故事,因为所有此类病症和大多数常见疾病都涉及多个基因以及与环境的多种相互作用。然而,作为吸烟生物学的一个小而离散的部分,这一DNA发现使得双胞胎研究远远超越了诸如“你父亲吸烟吗?你母亲吸烟吗?”之类的调查问题。
异卵双胞胎是分子分析的最佳选择。假设一对异卵双胞胎在吸烟方面存在差异。生物学家将把基因搜索集中在两兄弟姐妹不同的DNA区域。当然,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基因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但是,如果一项有希望的基因在异卵研究中脱颖而出,那么在同卵配对中寻找相同的基因就足够简单了。
这就是欧洲正在进行的全球最大双胞胎扫描背后的策略:GenomEUtwin,它自豪地被称为,中间的字母代表欧盟。这项研究由佩尔托宁指导,代表了丹麦、芬兰、意大利、荷兰、挪威和瑞典等国家双胞胎登记处的整合。最近来自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加入使双胞胎总数达到80万。双胞胎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将进一步扩展健康数据库。GenomEUtwin的首次运行将寻找控制身高的基因,身高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特征,但人类常见疾病的基因才是真正的奖品。到2010年,科学家们希望能够获得其中一些基因。
关于双胞胎的一个普遍真理是,他们似乎喜欢科学家的关注。没有哪个国家要求他们参与研究或提供DNA和家族史,但多年来,大多数双胞胎都乐于提供帮助。《双胞胎研究》的编辑马丁说:“双胞胎足够稀有,让他们觉得自己很特别,并且很高兴研究人员对他们感兴趣,但又不是稀有到令人怪异。所以他们的合作通常出奇地好。”再说,合作本就在他们的基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