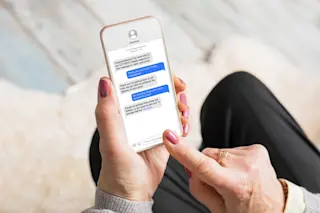时不时地,有人因医疗问题需要进行脑部CT扫描或MRI检查。幸运的是,检查排除了威胁性疾病,在随之而来的宽慰中,医生向病人展示了扫描结果。如果这是他或她的第一次,病人可能会感到毛骨悚然。与激起一种好奇反应(“嘿,看这里,那是我的肝脏”)的其他器官图片不同,脑部扫描会引发敬畏。那里面是您的大脑,有着复杂的表面和所有那些神秘的子区域。当新手医学生第一次手持尸体大脑时,在解剖课上也会感到同样的忐忑不安。同样的担忧让神经外科医生在切入灰质时开玩笑说:“钢琴课泡汤了。”毕竟,大脑是灵魂的栖息地,意识的“大老板”,自我感的器官。从这团酷似腌制豆腐的组织中,一个人得以诞生。
当孩子的身体停止生长时,大脑早就已长成成年人大小。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成年人大脑的某个部分大小发生显著变化时,会非常有趣。看看慢性酒精中毒者的大脑,您经常会发现某个特定区域严重退化;对暴露于大量有机毒素的人进行尸检,您会看到另一个大脑区域受损。而最近第三个大脑区域引起了很多关注,因为它可能会因某种严重的压力而萎缩。
想象一个青涩的18岁年轻人,穿上军装,被派往战场,并暴露于即使以人类暴力标准衡量也真正骇人听闻的事件中——比方说,一场战斗中,他是他所在整个部队唯一的幸存者。一些罕见的、无法解释的超人可能毫发无损地走出这种经历,甚至因此变得更强大,在世界崩塌的那一刻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但普通人会变得糟得多。他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遭受噩梦困扰。他可能会感到与无法理解他经历的亲人疏远。这还是他幸运的情况。有些幸存者显然会受损数十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现象被称为炮弹休克症;它导致一些人即使到了八十多岁,当门砰地一声关上时,也会颤抖并寻找掩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类似的现象被称为“战斗疲劳”。而在现代精神病学中,恐怖的长期残留被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它也不仅仅局限于战斗创伤。轮奸、童年性虐待、又一个隔壁的唱诗班男孩持自动武器发狂的屠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禁——所有这些经历都产生了被贴上PTSD标签的破碎之人。
根据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说法,PTSD患者会遭受闪回、噩梦和其他睡眠问题、情感麻木或爆发、失去快乐、不恰当的惊跳反射以及记忆和注意力问题。最后两个症状促使了最近的脑成像研究。
记忆问题可能源于微妙的微观状况:少数关键神经元产生或使用特定神经递质的方式出了问题,或者降解神经递质的酶出了问题,或者其受体或它触发的细胞内信使出了问题。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一些神经科学家开始关注更宏观的层面,他们生成了PTSD患者大脑的磁共振图像,并仔细测量了器官许多令人困惑区域的体积。研究人员像优秀的科学家一样,仔细核对,控制了经常伴随PTSD的抑郁症和药物滥用,并控制了总脑容量、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最近,在耶鲁大学医学院、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退伍军人事务医疗中心和哈佛大学、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独立工作的研究小组报告称,受影响个体的大脑中一个名为海马体的重要区域比平均水平小。
对于内行人士来说,这可是大新闻。与某些大脑区域不同,海马体是经过充分探索的区域,而其他大脑区域几十年来一直像流沙一样吞噬着勤奋的研究生,却未揭示其功能。我们用它来形成长期记忆,提取旧记忆,并管理明确的、有意识的记忆。当海马神经元及其连接被反复刺激时,它们会变得更强、更兴奋:瞧——这些神经元已经学到了东西。如果通过手术破坏海马体,就像对数以亿计的实验室大鼠以及一位仅以HM闻名的著名神经学患者所做的那样,一些主要的记忆类型将永远消失。阿尔茨海默病侵蚀海马体时也会导致类似的问题。
最近大多数PTSD影像学研究仅发现海马体萎缩;大脑其余部分正常。然而,损伤并非微不足道。例如,Tamara Gurvits、Roger Pitman及其在曼彻斯特退伍军人事务医疗中心和哈佛医学院的同事研究了战斗PTSD患者,并报告称海马体的一侧比预期小约25%。百分之二十五!这就像报告情感创伤导致心脏四个腔室中的一个消失一样。这些海马体严重失衡。J. Douglas Bremner及其在耶鲁大学医学院的同事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通常,当一个人进行记忆任务时,海马体的代谢率会增加,反映了该大脑区域启动所需的能量。然而,在PTSD患者中,相同的记忆任务未能加速海马体代谢,这一发现与PTSD患者典型的记忆缺陷相符。
尽管神经科学家们一致认为海马体萎缩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相关,但对其原因却存在诸多争议。布雷姆纳(Bremner)偏爱的一种可能解释涉及一类被称为糖皮质激素的类固醇激素;大多数人都熟悉人体中发现的糖皮质激素——氢化可的松。在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的压力下,人体的肾上腺都会分泌大量的这些化学物质。糖皮质激素对于在有饥饿豹子追逐的稀树草原上进行紧张冲刺以求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它们有助于将能量输送到大腿肌肉,并关闭生长或繁殖等非必需功能,这些功能可以在更有利的时机再进行。然而,尽管糖皮质激素在应对急性身体应激源时非常有用,但过多的激素——例如在慢性心理应激期间——可能引发各种与压力相关的疾病,包括高血压。
因为海马体含有大量的糖皮质激素受体,它是大脑中对这些激素最敏感的部分。糖皮质激素可以损害啮齿动物和灵长类动物海马体中的神经元。我的实验室和其他地方的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这种损害发生的多种方式。首先,几天内糖皮质激素水平升高可能会危及海马神经元,使其在癫痫发作、缺氧和缺糖(如心脏骤停时发生)期间存活的可能性降低。其次,在几周或几个月内,糖皮质激素会使海马神经元之间的树枝状连接萎缩;一旦压力或糖皮质激素暴露结束,这些分支会缓慢再生。最后,当糖皮质激素水平持续足够高且时间足够长——数月或数年——它们可以摧毁海马神经元。
这些发现让一些临床医生感到不安,因为各种疾病的患者都会长期接受大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尽管已知这种治疗会导致记忆问题),而且身体本身在神经危机期间也会分泌大量的这些激素。过量的糖皮质激素会损害人类海马体吗?也许会。
考虑库欣病,其中几种类型的肿瘤会产生极高的糖皮质激素水平。密歇根大学的Monica Starkman和她的同事们在患有这种疾病的人的MRI扫描中发现了萎缩的海马体。大脑的其他部分是正常的,但是血液中糖皮质激素水平越高,海马体就越小,患者经历的记忆问题也越多。当肿瘤被纠正,糖皮质激素水平恢复正常时,海马体也慢慢恢复到正常大小,这表明萎缩是可逆的,并且分支重新长回来了。
这就是PTSD中发生的情况吗?如果我们将神经元丢失(而不仅仅是萎缩)考虑在内,该模型最契合,因为萎缩可以在创伤后持续数年或数十年。然而,没有人真正知道是否正在发生这种情况。研究人员需要研究实际的脑组织,而不是图片,以确定PTSD患者的海马体中是否真的比健康个体拥有更少的神经元。此外,没有人知道强奸或爆炸期间糖皮质激素水平会达到多高。
我们大多数人将免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困扰。相反,我们的记忆问题将受到日常压力的影响,这些压力会改变记忆的准确性、强度、持久性和提取的容易程度。令人困惑的是,压力也能帮助记忆。我们记得挑战者号爆炸时我们在哪里;我们能回忆起与劫匪短暂遭遇的细节,仿佛它发生在昨天。然而,我们大多数人也都经历过压力会扰乱记忆的方式——例如,发现通宵学习的压力会对第二天早上期末考试时的记忆提取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我们可以通过理解“正常哺乳动物应激”(持续时间短的身体危机)和“人类应激”(例如,30年房贷期间)之间的区别来调和这种矛盾。在前一种情况下,应激反应具有高度适应性,有助于挽救您的生命;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应激反应的无情性质使您容易患病。
这种差异有助于解释关于压力和记忆的数据。持续不到几个小时的压力源往往会使记忆更清晰,这主要是肾上腺素的作用。如果压力源持续存在,这种增强就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健忘,这主要是糖皮质激素的作用。所以,如果您要为那场期末考试感到压力,请确保紧张情绪在您坐下时才开始,而不是前一天晚上。——R.S.
另一种模型来自西奈山医学院和纽约布朗克斯退伍军人事务医疗中心的雷切尔·耶胡达及其同事。他们研究了创伤后问题出现时患者的糖皮质激素水平。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们和其他人观察到,水平并没有高于正常值,反而更低。他们细致的工作表明,这可能是因为大脑对糖皮质激素的调节作用更敏感,导致分泌减少(有点像使恒温器对温度微小变化更敏感)。因此,他们解释这种综合征并非由于创伤期间过多的应激激素,而是由于创伤后对这些激素的过度敏感。在这两种模型中,有趣的是科学家们已经确定了一个可能的罪魁祸首,一种已知的在其他情况下会对海马体和记忆造成不良影响的应激相关激素。
当然,创伤可能导致大脑萎缩的观点可能完全是错误的,这是一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境,科学家们往往在认为找到线索时被绊倒。让一群士兵经历难以言喻的战场地狱,通常只有其中一小部分人(15%到30%)会患上PTSD。也许我们把故事弄反了。也许是那些海马体较小的人,在经历创伤时更容易患上PTSD。也许这些人处理信息的方式不同,形成记忆的方式不同,因此更容易出现闪回。皮特曼和他的同事报告说,最终患上PTSD的士兵很可能在入伍前就存在高于平均水平的“软”神经系统症状——不是彻底的神经系统疾病,而是一些轻微的危险信号,如发育里程碑延迟或学习障碍发生率高于平均水平。
一些研究人员正试图弄清海马体较小是否会使人易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皮特曼(Pitman)、沙莱夫(Arieh Shalev)及其同事正在进行一项前瞻性研究,对刚经历创伤的人进行核磁共振成像检查,并进行后续扫描。神经科学家将检查前后图像,以确定海马体较小是否真的预示并预测谁会患上PTSD,或者海马体体积是否会在后续图像中减小。
与此同时,北小石城退伍军人事务医疗中心的精神病医生托马斯·弗里曼(Thomas Freeman)正在采取另一种方法来解开因果关系的问题。如果海马体在创伤后萎缩,特别是如果它在创伤后持续萎缩,那么对于较早灾难的幸存者来说,萎缩的程度应该比最近灾难的幸存者更显著。弗里曼和他的同事正在比较来自海湾战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等PTSD受害者的脑部扫描结果。
所以,我们有科学家们存在分歧,有待完成的实验,有待撰写的拨款申请。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让我们从它不意味着什么开始。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日常压力——交通堵塞、金钱烦恼、糟糕的老板、不愉快的关系——会导致神经元死亡。这些压力源对血压等健康状况不利,并可能导致海马体神经元无法发挥最佳功能,但神经元几乎肯定保持完好。
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将创伤后应激障碍定义为“一种极度虚弱的疾病,可能发生在暴露于可怕事件或磨难之后,其中发生了或威胁到严重的身体伤害。”
美国每年至少有4%的成年人(570万人)患有PTSD。一百万越南退伍军人患上了这种疾病,几乎三分之一在战区待过的人也患上了这种疾病。
触发因素包括军事战斗、暴力人身攻击(强奸、折磨、身体或性虐待)、事故(车祸、飞机失事)、自然灾害(洪水、飓风、地震)。受害者的家属也可能患上PTSD。
PTSD患者可能会经历闪回,感觉自己正在重温磨难。他们可能难以入睡,或因夜复一夜的噩梦而无法安眠。他们可能感到情感麻木,与最亲近的人疏远。他们可能遭受可怕的侵入性想法或记忆。他们可能会转向药物或酒精来抑制自己的思绪和情感。他们可能会变得抑郁、焦虑或易怒,对周围的人大吼大叫或发脾气。他们还可能遭受极端的内疚感,仿佛他们应该或能够阻止灾难的发生。
任何经历过严重磨难的人都有发展这种疾病的风险,但对于那些有先前创伤经历的人,特别是那些在童年时期遭受过性、身体或情感虐待的人,风险最大。
PTSD患者通常会服用抗焦虑药或抗抑郁药,如萘法唑酮和曲唑酮,以治疗抑郁、焦虑和失眠等症状。行为和认知行为疗法也可能有用。例如,治疗师可以教导患者通过缓慢深呼吸来避免恐慌发作。治疗师可能会逐渐让患者接触提醒他们创伤的图像或感觉(战场照片、巨大噪音),然后帮助他们处理随之而来的恐惧。
另一个警告:海马体中连接神经元的树突因压力而萎缩随后恢复的说法,为一些相信“恢复记忆”的人提供了一个难以抗拒的隐喻。这个词描述了一个有争议的情景,即可怕创伤的受害者完全压抑了对经历的所有记忆,却在数年或数十年后将其恢复。围绕这个煽动性问题,生命被毁——要么是创伤受害者的生命(一种解释),因为记忆的作用而等待数十年才能伸张正义;要么是虚假指控受害者的生命(另一种观点),在本季的“女巫审判”中被吞噬。神经心理学家之间几乎因此爆发了内战,所以让我在此轻描淡写——我只会说,我没有看到任何科学证据表明这种恢复记忆是如何运作的,也没有看到任何被严格科学家认为合法的所谓案例,反而有很多科学解释说明为何各种主张不合法。
尽管最近的海马体研究对日常压力和恢复记忆没有太多可说之处,但它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实际教训。如果海马体较小确实是PTSD的风险因素,那么在决定派遣谁上战场时,就应该考虑神经解剖学,就像我们会考虑是否存在心脏杂音一样。如果萎缩是创伤或创伤后期的结果,科学家们就会有他们常规的行动指令:弄清楚这个过程是如何运作的,以便我们学习如何预防它。
但这些发现也应该意味着更宏大的事情。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世界上所有关于我们正在危及环境的警示讲座,都比不上那第一张来自月球的地球标志性照片——渺小、孤寂、脆弱。阅读纳粹的故事无法像参观美国大屠杀纪念馆那样令我们窒息,纪念馆里挤满了无数遇难者的鞋子。当我们试图理解不可理解的事物时,我们需要具体的图像。因此,一千个人各自写一千字关于人类暴力的后果,可能不如一张照片,比如一张脑部扫描图,来得有冲击力。看看他们对我的大脑做了什么。看看他们对我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