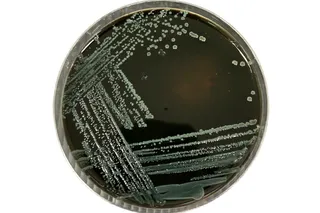一位女士冲进急诊室大喊:“我的儿子在哪儿?”
“在这儿,”我被她的突然闯入吓了一跳,脱口而出。她身材矮小精干,从急救人员身边挤过,来到她一动不动的、体格健壮的25岁儿子道格身边。然后,她转向我,踮起脚尖,压低声音说:“我告诉那些医生他需要核磁共振!”
“他有癫痫吗,女士?”我小心翼翼地问道。“任何类型的癫痫病史?”
“他以前有过一次,”她继续说道,好像没听见我的话。“那些在城外的蠢货查不出他到底怎么了。三个月前他有过一次……发作。和今天一样。他们让我们去看神经科医生。但该死的保险公司不批准核磁共振。”
为了控制局面,我把带头的急救人员拉到一边。“再说一遍——你为什么给他插管?”
“他处于昏迷状态,”那个穿着蓝色制服的粗壮男人说。“纳洛酮没有反应,”纳洛酮是一种用于治疗阿片类药物(如海洛因)过量的解毒剂。“然后他就开始抽搐了。”
“全身抽搐?”我问道。
“很难说,”急救人员回答,擦了擦额头。“他手脚抽搐,呼吸不畅。我们决定不等了,就给他镇静了——这就止住了抽搐——然后我们就给他插了管。”
昏迷的病人容易将胃内容物呕吐到肺部。带套的呼吸管可以防止这种情况。“听起来很合理,”我说。“当家属打电话叫救护车时,他们具体说了什么?”
“他妈妈发现他躺在床上,怎么都叫不醒。”
躺在担架上的年轻人看起来异常平静——除了他嘴里那根拱起的塑料呼吸管。我转过身问他母亲:“第一次发作时他做过 CT 扫描吗?”
她嗤笑一声。“结果正常。”
一位年轻女子走到我们站的地方。“我是他姐姐,”她说。
看到新的信息来源,我问道:“你知道他用什么药吗?药物?”
母女俩都断然摇头。“他是个好孩子。不喝酒,不乱来,”妈妈抢着说。
“昨晚他有一些朋友过来玩。他们在楼上聚会,”姐姐补充道。“可能喝了几杯啤酒。仅此而已。”
年轻人的体格检查没有提供任何线索。他的生命体征完美;瞳孔略小但对光反应良好;捏他时,他的四肢几乎不动,但肌肉张力很好,而不是瘫痪时的松弛状态。我开始进行鉴别诊断。药物过量?这在三个月前第一次发作时就已经可以发现了。脑出血或脑膜炎?这些显然是最糟糕的可能性,但我的警报并没有响起;除了昏迷,道格看起来状态太好了。持续性癫痫?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像尊雕像(尽管大脑可能存在癫痫样电活动,但没有明显的肌肉收缩)。
我掌握的最好线索是这次发作是重复的。但重复的是什么?复发性脑炎?嗜睡症?退行性神经元疾病?一种新型的疯牛病?我想象着答案藏在一本厚厚的、名为《你无法想象的神经系统疾病》的书里。
道格的母亲抓住了我的胳膊。“他到底怎么了?”她恳求道,眼泪开始涌上来。
“别担心。我们会做他需要的检查。”
CT 扫描什么也没显示(又一次)。几分钟后,道格开始剧烈抽搐并快速呼吸,好像呼吸管在噎着他。这是个好迹象。他要醒了吗?我给气囊放气,拔掉了管子。他咳嗽着,脸涨得通红,试图坐起来,睁开眼睛,然后又倒了下去。他突然又开始快速呼吸,停顿了一整分钟,然后又加速起来。
“这是陈-斯托克斯呼吸吗?”护士问我。这种不规则的、时断时续的呼吸模式——如此独特以至于有自己的命名——表明脑干呼吸中枢功能失调。我最近在一名患有狼疮引起的脑炎的病人身上看到过。他去世了。
毒理学筛查结果显示正常:没有酒精、没有安定、没有可卡因。道格的其他血液检查结果也完全正常。我感到困惑,于是给重症监护团队的一名成员打了电话。“一个25岁的男人,”我开始说。“原因不明的昏迷,可能伴有抽搐。可能需要做腰椎穿刺。好消息是,颈部柔软,无发热,白细胞计数正常。无论如何,他需要进重症监护室。”
“好的,”一位年轻的住院医生说。“但请给我们的主治医生打电话。她需要批准。”
两分钟后,我接通了主治医生的电话。“我是莎拉。”
“抱歉听起来这么含糊,”我说,然后复述了情况。
电话那头沉默了。终于她问道:“这孩子在用 GHB 吗?”
“家属否认用药,”我说,立刻听出这话多么苍白无力。“白痴!”我对自己说。“我再给你回电话,”我大声回答。我想把电话挂断。
我把妈妈和姐姐叫到一边。“抱歉,但我们必须知道:道格昨晚用了 GHB 吗?”
妈妈瞪大了眼睛:“什么?”但姐姐的脸上闪过一丝表情。
“请特别问问他的朋友们。告诉他们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γ-羟基丁酸(GHB)——俗称 G、液态摇头丸、乔治亚家乡客或樱桃冰毒——在 21 世纪的狂欢派对中的地位,如同 20 世纪 80 年代可卡因在华尔街的地位。GHB 是一种天然的大脑神经递质,少量使用有兴奋作用。据说再多服用一点会带来温暖、梦幻的感觉,并伴有性唤起。作为一种娱乐性药物,它能增强狂欢派对特有的、由电子舞曲驱动的、令人晕眩的状态。
问题是什么?在高浓度下,GHB 会像安定一样与 GABA 大脑受体结合。这种相互作用会产生 GHB 特有的效果:瞬间昏迷,就像被泰森的勾拳击中一样。更糟的是,GHB 的剂量效应极其不可预测。稍微多一点,你就可以从派对的焦点变成需要拨打 911 呼叫急救。(GHB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用作麻醉剂,但由于剂量控制过于棘手而被淘汰。)难怪它已成为药物诱导昏迷的主要原因,并且在所有非法药物中,它需要紧急会诊的排名第二。如果再掺入酒精——酒精会与肝脏代谢 GHB 的酶竞争——这种药物的效果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会直线飙升。
GHB 过量的副作用多种多样,从呕吐、肌肉痉挛、抽搐到心率缓慢和心脏骤停。自 20 世纪 90 年代流行以来,GHB 已导致数百人死亡。并且它极易上瘾:一些滥用者每两个小时就需要服用一次。慢性使用后的戒断症状尤为难受。戒断 GHB 数周后,可能会出现谵妄和危及生命的心情激动。
GHB 还因其“约会强暴药”的恶名而臭名昭著。它是一种无味、无色的液体,很容易被鸡尾酒掩盖,且代谢迅速,常规的血液和尿液检测无法检测到。专门的实验室可能会检测出来,但前提是必须立即分析尿样。GHB 甚至不需要让受害者失去知觉。在低于昏迷剂量的作用下,它可以引起失忆、唤醒和一种被动、顺从的心态。
姐姐回来了。“朋友们招了,”她用干脆、严肃的点头说道。“他们昨晚用了 GHB。”
妈妈只是盯着。然后她的肩膀垮了下来。
我给莎拉回了电话。“猜对了。谢谢你让我脑子转过弯来。那‘第二次发作’的鬼话差点把我绕晕了。”
“不客气,”她宽厚地回答。“我丈夫是个警察。他最近见过很多这种事。”
我转过身对家人说。与保险公司为做核磁共振而进行的斗争?儿子看着他妈妈为他——为了一个谎言——据理力争?然后又重蹈覆辙?
我挑了挑眉毛看向姐姐。她的目光变得空洞。我不知道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消息是,道格没有表现出长期使用 GHB 的迹象,一旦体内的这种药物剂量排出体外,他就会安然无恙。
“他应该在几个小时内醒来,”我安慰他母亲。“他会没事的。”
“他不会没事的,”她咕哝道,声音又变得激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