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atthew D. Lieberman

喜剧演员杰瑞·宋飞曾讲过一个笑话:“根据大多数研究,人们最害怕的是公开演讲。死亡排在第二位。听起来对吗?这意味着对普通人来说,如果你去参加葬礼,坐在棺材里比做悼词要好。”这个笑话是基于1973年一项对2500人进行的私人调查,其中41%的受访者表示害怕公开演讲,只有19%的受访者表示害怕死亡。虽然这种不太可能的排序在其他大多数调查中并未得到重复,但公开演讲通常是我们最深层恐惧清单中的靠前位置。“恐惧排行榜”的前十名通常分为三类:与严重身体伤害或死亡相关的事件,亲人的死亡或失踪,以及公开演讲。令人好奇的是,演讲者可能并不认识或不在乎在场的多数人。那么,为什么他们的想法如此重要呢?答案是,被拒绝会让人痛苦。问问自己,你人生中最痛苦的一两次经历是什么?你会想到腿断了或摔得很重的身体疼痛吗?我猜至少你最痛苦的经历之一与我们所谓的社交痛苦有关——亲人去世的痛苦,被所爱之人抛弃的痛苦,或在他人面前遭受某种公开羞辱的痛苦。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事件与“痛苦”一词联系起来?当人类经历社会联系的威胁或损害时,大脑的反应与对身体疼痛的反应非常相似。
调查社交痛苦
动物研究表明,社交痛苦与身体疼痛的体验有关。大约在2001年,我和Naomi Eisenberger决定尝试在人类身上进行调查。我们让人们在fMRI扫描仪中玩一个名为“网络球”(Cyberball)的游戏。受试者相信他们和另外两个人同时在接受大脑扫描,同时通过互联网玩这个电子游戏。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对大脑如何协同工作来完成像抛球这样简单的任务感兴趣。这些人并不知道他们即将在扫描仪中被拒绝。但在玩了几分钟抛球后,其他“玩家”停止向实际参与者抛球。在参与者被拒绝后,他们走出了扫描仪,被带到一个房间回答关于他们经历的问题。通常,这些人会自发地与我们谈论他们刚刚经历的事情。他们对所经历的事情感到非常愤怒或悲伤。这在当时的fMRI研究中很不寻常,因为大多数任务都不会产生个人情感反应。我们不得不假装没有注意到扫描仪里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想让他们即将回答的问题受到我们可能说的话的污染。
顿悟的时刻
我们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分析数据,但有一个时刻,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发现了有趣的东西。我和Naomi深夜都在实验室里,而我的研究生Johanna Jarcho正在隔壁电脑上分析她关于身体疼痛研究的数据。我们来回查看两组数据,注意到结果惊人地相似。在身体疼痛研究中,经历更多疼痛困扰的参与者激活了dACC(前扣带皮层)更多。在社交痛苦研究中也是如此,当被拒绝时,经历更多社交困扰的参与者激活了dACC更多。在身体疼痛研究中,激活了右侧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参与者经历了较少的身体疼痛。同样,在社交痛苦研究中,激活了右侧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参与者经历了较少的社交痛苦。最后,在两项研究中,激活了更多前额叶区域的参与者激活了较少的dACC。两项研究都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当你经历更多痛苦时,dACC的活动就越多。在此之前,有许多研究都显示了这一点——但我们的研究是第一个表明这不仅适用于身体疼痛,也适用于社交痛苦的研究。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个人调节疼痛困扰方面能力与腹外侧前额叶活动的增加有关,而这似乎又会减弱dACC的反应。看着屏幕,并排比较,如果你不知道哪一个是身体疼痛的分析,哪一个是社交痛苦的分析,你就无法分辨出区别。
爱与失去
纵观我们的一生,我们注定会经历各种形式的社交排斥和失落。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多次关系的破裂,而且通常我们都曾处于被抛弃的一方,而不是主动离开。这种破裂常常让人难以忍受,并且会长期深刻地改变我们看待自己和生活的方式。我们人类在子宫外缓慢发育、适应特定文化和环境、以及拥有地球上最大脑容量的“浮士德式”进化交易。但它要求我们为此付出代价,每次与可能离开我们或拒绝给予爱的人类建立联系时,都要承受真实的痛苦。进化打赌,为了人类的所有回报,承受痛苦是可以接受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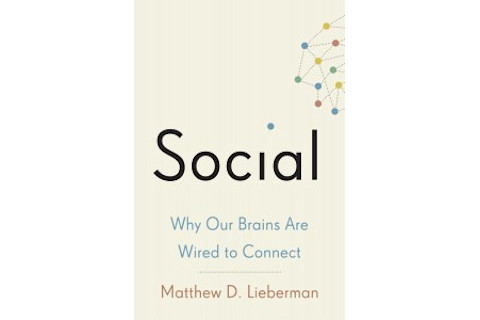
改编自马修·利伯曼(Matthew Lieberman)的著作《SOCIAL》。版权所有 © 2013,Matthew Lieberman。由Crown出版社出版,隶属于Penguin Random House Company下的Random House LLC。
在Twitter上关注Matthew:@social_brains
顶图由gpointstudio / Shutterstock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