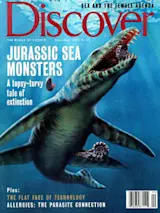莫克岛这个热带小岛,地理位置上几乎是世界上最偏远的地方,同时又像天堂般近在咫尺。它是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点,长四英里,宽两英里,周围环绕着被风吹拂的棕榈树和古老的珊瑚石灰岩礁。莫克岛是库克群岛之一,以探索该群岛的十八世纪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命名。它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是每周三次从100英里外该群岛最大的岛屿拉罗汤加飞来的飞机。
莫克岛上几乎所有600名居民都是波利尼西亚人。他们捕捞当地水域的鱼类,种植芋头、香蕉和面包果,并种植芒果等经济作物出口到新西兰。周日,他们聚集在传教士建造的教堂里,举行欢快的毛利歌唱庆典。
但岛上也有不那么友好的居民。其中一种是线状寄生性蛔虫——丝虫——它由蚊子(岛上另一种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居民)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蠕虫在微小的幼虫阶段,通过蚊子叮咬造成的穿刺进入受害者的皮肤,迁移到淋巴结,然后交配并产生更多微小的后代,这些后代进入血液。在这个过程中,蠕虫破坏了淋巴系统,淋巴系统负责排出身体组织中的液体,导致大量液体积聚,从而产生象皮病患者痛苦肿胀的四肢。
寄生虫并非只在莫克岛不受欢迎。各种丝虫及其各种近亲——钩虫、鞭虫、蛲虫和扁形虫——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它们影响着20多亿人,导致从象皮病到失明,再到严重的肠道问题等疾病。埃里克·奥特森说,世界上至少有40%的人口感染了蠕虫。
奥特森应该知道——他是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临床寄生虫学部门的负责人。但奥特森不仅是一名寄生虫学家;他还是一名过敏症专家。正是这种学科的交汇,使得他与莫克岛居民的接触变得非常有趣。十九年前,31岁的奥特森刚开始他的双重职业生涯时,曾访问莫克岛,研究丝虫的流行情况,并开始治疗岛民的感染。去年夏天,他回到了岛上。但这次他不仅仅是寻找寄生虫;他还发现自己正在追寻他怀疑可能是过敏症根源的线索。
“这很有趣,”他说。“我们第一次去莫克岛检查丝虫时,也检查了过敏症。但很难找到有抱怨过敏的人。现在,近二十年后,岛上的寄生虫感染大大减少了,但有趣的是——”他向前倾身,用一种坚定的耳语说:“过敏症却多得多。”这一观察结果,以及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类似披露,使奥特森考虑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可能性——过敏症与寄生虫的存在之间存在反向关系。
奥特森并非第一个怀疑这种关联的人,尽管他在寄生虫学和过敏学方面的综合专长可能使他成为最有资格这样做的人。这想法并非初看起来那么奇怪。我们的过敏反应和对寄生虫的反应都是免疫系统反应,两者都依赖于同一种相当不寻常的免疫机制。当身体清除蠕虫的机制以某种方式被误导时,会不会导致过敏呢?奥特森说:“必须有导致过敏机制的原因。”它可能最初是为了对抗寄生虫感染而进化的。但是当没有寄生虫存在时,你就会留下一个经过磨砺的免疫系统,它正在寻找攻击目标。所以那些本应在丛林中受到寄生虫保护的人,现在却困在纽约或其他寄生虫稀少的地方,他们因为街上飘散的花粉而哮喘和咳嗽。
如果真是这样,这对于大多数过敏患者来说是个新闻,仅在美国,过敏患者就多达约5000万人——也就是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美国人每年至少花费50亿美元来应对这种看似无用的疾病。在大多数研究人员看来,过敏症是身体对通常无害的入侵者进行的毫无意义的防御动员。花粉等致敏物质肯定不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太大威胁;猫皮屑和尘螨也一样。然而,与这些过敏原接触会导致数百万人肿胀、喘息、抓挠和打喷嚏,仿佛受到了围攻。在极端情况下,对昆虫叮咬和某些食物(如花生)的反应,一种压倒性的过敏反应,称为过敏性休克,甚至可以杀死我们的免疫系统原本旨在保护的身体。
免疫系统为何会以这种误导的方式运作?过敏症专家并不真正清楚;该领域充满了争议,也充满了坚实的科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过敏是由一种不同于其他任何免疫反应引起的——除了抗寄生虫反应。
通常,当身体面临外来病毒或细菌入侵时,它会通过产生数十亿个Y形抗体来做出反应。这些抗菌蛋白质属于称为IgG的抗体家族,IgG是免疫球蛋白G的缩写。IgG抗体在血液中自由漂浮,寻找微生物表面独特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将它们标记为外来物;当它们遇到入侵者时,Y形分子会抓住它们并将其固定住,供免疫系统的杀伤细胞处理。奥特森说:“这些抗体就像外来颗粒和杀伤细胞之间的桥梁,将它们连接起来。”
但正如研究人员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现的那样,当我们受到寄生虫入侵时——例如,蠕虫钻入皮肤时——会激活一种不同的机制。免疫系统再次产生Y形抗体来对抗蠕虫脱落的外来蛋白质,但这次的抗体是一种叫做IgE的类型。IgE没有直接攻击外来入侵者,而是尾部朝下地附着在称为肥大细胞的特殊细胞表面。这些细胞存在于身体与外界接触的所有地方,因此也存在于与寄生虫(或过敏原)接触的地方——皮肤、眼睛、鼻子和喉咙的粘膜,以及肺部和肠道的内壁。当最初的IgE反应完成时,每个肥大细胞的表面都有10万到50万个Y形抗体伸出双臂,像一片矮小的树林。
此时,通常在蠕虫最初入侵后的14天内,免疫系统就已准备就绪。每个肥大细胞都含有一千个或更多的大型球状颗粒的“武器库”。现在,当蠕虫蛋白粘附在两个相邻IgE抗体的“手臂”上时(考虑到肥大细胞表面抗体的巨大密度,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就好像一个生化回路被关闭了。一系列爆炸性事件被启动,最终导致肥大细胞破裂,并喷射出其腹部的所有颗粒。
“IgE与其他抗体非常不同,”奥特森说。“你取这些小分子,将它们粘附在肥大细胞上,给它们一个信号,它们就会引发一场大爆炸——气球爆炸,所有颗粒都倾泻而出。”
这些颗粒反过来又含有药典中的组胺和其他化学物质,它们会渗入皮肤和激活肥大细胞附近的其他组织。这些化学物质导致所有炎症症状——瘙痒、血管扩张和渗漏、肿胀、粘液分泌过多。虽然没有人确切知道这种IgE反应如何防御寄生虫,但奥特森根据他的实验室和其他地方的实验,有一些很好的猜测。例如,丝虫和钩虫通过皮肤进入人体。引起该区域发炎和肿胀的免疫反应可能会将蠕虫隔离起来,并阻止它们进一步钻入。更重要的是,肥大细胞反应会将其他细胞吸引到现场,这些细胞会将自己的有毒化学物质倾泻到被困的蠕虫上。“你需要对寄生虫产生炎症反应,以保护自己免受侵入,”奥特森断言。
另一方面,肠道蠕虫如蛲虫通过口腔进入人体——通常随受粪便污染的食物或水进入——然后进入肠道。腹泻是由于发炎的肠道排出液体和粘液造成的,它可能会在蠕虫侵入肠壁之前将其冲走。许多此类蠕虫,包括那些导致流行热带病血吸虫病(有时称为蜗牛热,因为血吸虫是由水蜗牛传播的)的蠕虫,其复杂的生命周期中也有一部分在人体肺部度过。气道炎症引起的咳嗽和打喷嚏可能是免疫系统试图驱逐进入呼吸道的蠕虫。这些炎症反应在初次接触寄生虫的热带地区居民中往往比以前接触过蠕虫的人更为明显。而且它们绝非万无一失——有些蠕虫仍设法在人体内安家落户,建立慢性感染。但总的来说,IgE反应似乎在抑制蠕虫世界方面做得很好。
一切都很好。但正是这种免疫过程,却给我们带来了完全无用的过敏。当我们第一次遇到过敏原——比如空气中的豚草花粉粒时——它的异源蛋白质也会激活免疫系统的IgE分支,IgE抗体迅速被安置在易受花粉影响区域(如鼻子、呼吸道和眼睛)的肥大细胞上。不幸的是,当我们再次遇到豚草蛋白质时,我们的肥大细胞已准备就绪。细胞上的IgE抗体捕捉异源蛋白质,细胞喷出组胺,组胺引起炎症,我们就会遭受熟悉的花粉症折磨——流鼻涕、打喷嚏、咳嗽、眼睛发痒和流泪。同样,如果入侵者是进入肺部的尘螨,过敏反应可能会引发与哮喘相关的喘息和呼吸急促。而一顿海鲜餐则可能导致食物过敏引起的胃部不适和腹泻。
然而,正如奥特森指出的那样,自然界不会把能量浪费在一个完全无用的过程中。进化论表明,动物会保留那些对生存有用的性状,并抛弃那些无用的性状。奥特森说,引起过敏的反应如此普遍,它肯定在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它之所以能存在,唯一的解释是拥有它比没有它更好。在奥特森看来,拥有它更好,因为它能保护我们免受蠕虫寄生虫的入侵。这就是它的作用。
因此,奥特森认为对抗寄生虫必然是IgE反应的真正目的,而多余的过敏症则是其被误导时发生的。这让他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假设。如果他是对的,那么环境中寄生虫越多,人们患过敏症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当IgE抗体忙于对抗致病蠕虫时,这种独特的免疫系统分支不太可能同时攻击花粉和尘螨。同样地,要应对的寄生虫越少,闲置的IgE就越有可能转而攻击花粉和其他过敏原。
这就是奥特森去年夏天想在莫克岛探索的联系。1992年5月,奥特森和他的免疫学家、寄生虫学家和医生团队带着两吨实验室设备、自己的发电机和一台宝丽来相机登上该岛,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停留。“就像上次一样,我们为所有病人拍照,”奥特森说。“岛上几乎没有照片。很多人还保存着我们多年前为他们拍的原始照片。他们非常珍惜。他们很高兴再次见到我们。”
在当地一位受人尊敬的苏格兰医生阿奇·几内亚的帮助下,他们开始检查岛上的每一位居民。他们抽血,插入压舌板,用灯照射耳朵和眼睛,并详细记录个人病史。奥特森回忆道:“太棒了。岛上没有人拒绝。这成了一件社区的事情——没有人想让任何人失望。”
奥特森发现,与19年前相比,莫克岛上的丝虫感染大大减少了。只有16%的人口携带这种微小的蠕虫,而他首次访问时这一比例为35%。这种减少主要归因于用抗寄生虫药物二乙基卡巴马嗪治疗岛民,这种治疗是奥特森在早先访问期间开始的。那么过敏症呢?奥特森说:“毫无疑问,这次过敏症要多得多。”19年前,只有不到3%的人有过敏症。这次至少有15%。症状包括湿疹、花粉症、哮喘和食物过敏。更重要的是,主要问题是19年前没人听说过的:章鱼过敏。“这是头号罪魁祸首,”奥特森说。“人们身上出现皮疹、荨麻疹、喉咙肿胀。然而,章鱼对他们来说并不新鲜——我们上次在那里时他们就在吃章鱼。现在有什么不同呢?”奥特森回答了他自己的反问:也许IgE防御机制不再忙于攻击蠕虫,现在正在攻击章鱼蛋白和其他新目标。
问题是,这很难证明是哪一种情况。我们免疫防御的范围和有效性是由遗传决定的;它们因人而异。过敏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人可能对章鱼产生使人衰弱的IgE反应,而另一个人可能反应轻微,甚至根本没有反应。(也不是每个人对相同的蠕虫都有同等强度的反应。)这使得确定寄生虫与过敏症之间的确切关系变得困难。奥特森说:“设计一个能够证实反向关系的实验极其困难。变量太多。没有两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免疫反应,也没有两个人对过敏原或寄生虫的接触相同。所以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治愈一些人的寄生虫,然后看看他们是否会发展出过敏症。要获得任何接近有意义的结果,你必须长时间跟踪大量人群,或者以某种方式在动物身上模拟人类情况。”
然而,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在过去的十年里,对大鼠的实验表明,感染蠕虫的动物过敏反应较弱,就好像它们与寄生虫的斗争使得IgE反应几乎没有多余的“弹药”来对付过敏原。在人类中,对来自菲律宾、中国和西印度群岛(寄生虫感染率高)移民的研究表明,这些人几乎没有过敏症——而他们在美国和英国出生的无寄生虫后代却因此痛苦不堪。
然而,并非所有研究都指向同一方向。例如,在新几内亚农村地区,持续的寄生虫感染似乎对至少一种过敏状况(哮喘)的流行没有影响。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免疫系统,无论多么闲置和误导,会以尘螨和花粉等无害的入侵者为目标。奥特森说,也许过敏原,像寄生虫一样,向免疫系统呈现出某种特征性分子成分或形状,从而引发IgE反应。或者,过敏原被免疫系统处理的方式导致系统进入IgE而非IgG模式。但目前还没有人真正掌握这一点。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理论生物学家玛吉·普罗费特(Margie Profet)认为,这些不确定性足以让她完全否定寄生虫联系。她断言:“如果过敏症是因为寄生虫而存在,那将是荒谬的。自然选择绝不会产生如此有缺陷的设计。”事实上,普罗费特认为过敏症并非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毫无用处。在她非传统的观点中,过敏症可以防御常常由引起过敏的物质传播的毒素。例如,某些致敏食物如花生可能含有有害霉菌,如黄曲霉毒素。普罗费特认为,过敏反应的爆发性——所有这些肿胀、打喷嚏、咳嗽、腹泻和呕吐——可能有助于阻断或清除系统中的毒素。
对于普罗费特的理论,奥特森耸耸肩。他认为,虽然少数观察结果似乎支持她的观点,但支持她的生物学证据不如支持他的多。无论如何,他没有时间或兴趣争论这两种理论的理论价值。他更感兴趣的是利用他自己假说中一个无可争议的证据:过敏与我们的寄生虫防御之间的相似性。因为如果过敏反应确实是寄生虫反应失控,那么奥特森可能发现了一些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有趣之处。他可能已经找到了一种阻止过敏的方法。
与难以捉摸的致敏物质相比,寄生虫就像一本打开的书——易于识别,并且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几乎无处不在。同样,IgE对寄生虫的反应比对过敏的反应更明显,也更适合研究。奥特森解释说,在丝虫感染中,蠕虫会爬入体内并在血液中循环。你甚至可以在显微镜下看到它们蠕动,每立方厘米血液中有数千条。你有大量的IgE针对寄生虫,是过敏症的十倍,所以你拥有引发巨大炎症反应的条件。
但正如奥特森和其他人所发现的,你并不一定会得到巨大的反应:它通常会受到调节。事实上,当寄生虫感染变得慢性时,就像在许多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身上最终发生的那样,感染是相当低调的——它们依赖于相互容忍,客方和宿主之间可控的“自由放任”。奥特森说:“世界上有数十亿人感染了寄生虫,但他们带着它们生活了几十年。”毕竟,如果蠕虫成功进入你的身体——如果它通过了你最初的免疫防御——那么你就想与你的寄生虫和平共处。你不想让你的整个身体一直肿胀。一定有一些自然进化的东西可以控制反应的严重程度。奥特森想,那个东西能提供驯服过敏的关键吗?
目前,令数百万人痛苦的是,还没有可靠的方法来平息它们。抗组胺药和减充血剂对某些人有效,但常常引起令人不快的副作用,如嗜睡。过敏针的有效率只有大约一半。它们的原理是通过定期注射微量致敏物质来诱导身体对过敏原产生耐受性。但实际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奥特森说:“在科学界,它们并不受高度重视。它们几乎没有科学依据,就像巫术一样。有时它们有效,有时无效,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当谈到调节对寄生虫的反应时,奥特森认为他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实上,在过去十年里,他投入了大量的实验室时间来拼凑这个过程。他解释说,事实证明,存在一种与IgE竞争的IgG抗体。这种G抗体在遇到固定在肥大细胞上的E抗体之前抓住蠕虫蛋白,从而阻止其触发炎症反应。
这种被称为IgG4的阻断抗体是IgG家族中最稀有的。通常,我们产生的大部分IgG抗体是那些常见的病毒和微生物杀手,官方名称为IgG1;IgG4仅占总量的1%到2%。但有趣的是,在寄生虫感染者中,阻断抗体跳升到总量的10%,增加了五到十倍。奥特森说:“我们研究的寄生虫感染者表现出巨大的G4反应。因此,即使他们产生大量IgE抗体来攻击寄生虫的蛋白质,许多攻击性抗体也被阻断抗体阻止,无法到达其靶标。”这种阻断导致了炎症反应的减弱,使人类和蠕虫能够共存。他总结道:“这是硬币的另一面——控制面。即使你有很强的IgE反应,如果你知道如何产生大量的G4,你就可以控制这种反应。”
这种阻断似乎是寄生虫感染的一个不寻常特征。它通常不会发生在过敏患者身上。但是,如果我们能以同样的方式驯服我们荒谬不恰当的过敏反应,那岂不是一件好事?奥特森确信,控制过敏症的挑战在于学习如何刺激阻断反应。这正是他现在敦促他的过敏症同事们去做的。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战胜过敏症的方法。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最好完全消除IgE反应,或以其他方式破坏过敏机制。但话又说回来,那些过敏症研究人员可能没有去过莫克岛,也不像奥特森那样对蠕虫充满热情。奥特森意识到他正在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如果你与其他过敏症专家交谈,你可能不会得出同样的方法。但是,”他向前倾身,用耳语说道,“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故事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