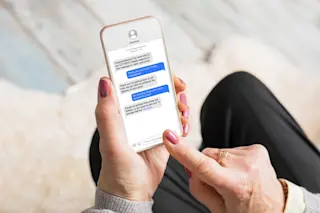这是一个永远无法科学提问的迷人问题:意识的本质是什么?即使是科学实验也无法证明意识的存在(请参阅我 2006 年 6 月的专栏,以了解原因)。幸运的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越来越接近这个不可能的话题。例如,我们可以问“意义是什么”,即使我们无法询问“意义的体验”。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索尔克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 V. S. Ramachandran 提出了一项研究计划,以非常具体的方式来探讨意义的问题。像许多最优秀的科学家一样,Rama(他的同事们都这样称呼他)正在将他的童年好奇心延伸到研究中。他 11 岁时,就对捕蝇草(一种食肉植物)的消化系统感到好奇。它的叶片中的消化酶是由蛋白质、糖类还是两者共同触发的?像糖精那样欺骗我们的味蕾一样,它是否也会欺骗捕蝇草?后来,Rama 转而研究视觉,并在 20 岁时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在《自然》杂志上。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与我的兴趣重叠的工作:使用镜子这种低技术虚拟现实来治疗幻肢痛和中风瘫痪。他的研究也促成了我们之间关于语言和意义的富有成效的持续对话。
在我 2006 年 5 月的专栏中,我描述了大脑皮层的一些区域是如何专门负责特定感官系统(如视觉)的,以及在这些区域之间存在着重叠区域,称为跨模态区域。Rama 一直对跨模态区域如何产生语言和意义的一个核心元素:隐喻感兴趣。
他最经典的例子就是“bouba/kiki”实验。Rama 向测试对象展示两个词,这两个词都可以发音,但在大多数语言中都没有意义:bouba 和 kiki。然后,他向对象展示两张图片,一张是尖锐的、刺猬状的形状,另一张是圆润的云状形状。让他们匹配词语和图像!当然,尖锐的形状与 kiki 相匹配,而云状形状与 bouba 相匹配。这种关联是跨文化的,似乎对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个普遍真理。
bouba/kiki 实验分离出了一种语言抽象形式。“Bouba 性”或“kiki 性”出现在两个原本完全不同的刺激之间:一个是视网膜上形成的图像,另一个是耳蜗中激活的声音。这种抽象似乎与隐喻的心理现象有关。例如,Rama 发现,在被称为颞顶叶联合皮层的跨模态大脑区域有病灶的患者,在 bouba/kiki 任务以及解释有非字面意义的谚语或故事方面都存在困难。
Rama 的实验表明,一些隐喻可以被理解为轻度的联觉。在更严重的联觉形式中,这是一种有趣的神经学异常,在这种异常中,一个人的感官系统是交叉的;颜色可能会被感知为声音。(有人可能会争辩说,莎士比亚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将联觉与意义联系起来:在《仲夏夜之梦》中,包底(Bottom)将他的梦描述为无法形容,因为“人的眼睛没有听过,人的耳朵没有见过……我的梦是什么样的。”)
Rama 实验中的图像和声音之间有什么联系?从数学角度来看,kiki 和尖锐的形状都有“尖锐”的成分,而 bouba 则不那么明显;发 kiki 音或画 kiki 图所需的舌头和手部动作中也存在类似的尖锐成分。
Rama 认为,跨模态抽象——即跨感觉建立一致联系的能力——可能最初是在低等灵长类动物中进化的,以便更好地抓住树枝。它是这样发生的:大脑的跨模态区域可能进化出了将视网膜上的倾斜图像(由观看倾斜树枝引起)与一系列“倾斜”的肌肉抽搐(引导动物以一定角度抓住树枝)联系起来。然后,这种重塑能力被用于人类擅长的其他类型的抽象,例如 bouba/kiki 隐喻。这在进化中是一个普遍现象:一个已有的结构,经过轻微修改,承担了相似但不同的功能。
Rama 也对其他类型的隐喻感到好奇,那些不属于 bouba/kiki 范畴的隐喻。在他目前最喜欢的例子中,莎士比亚让罗密欧将朱丽叶称为“太阳”。年轻、女性、注定要悲剧的浪漫女主角与天空中明亮的球体之间,没有明显的 bouba/kiki 式的动态联系,但这个隐喻对听到它的人来说是立即可以理解的。
几个月前,我们在一个我们都在发表演讲的会议上偶然相遇,我向 Rama 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建议,关于如何将 bouba/kiki 的想法扩展到朱丽叶和太阳。假设你只有 100 个词的词汇量。(如果你曾经去过一个你不会说当地语言的地区,你就会熟悉这种经历。)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有创意地使用你有限的词汇量来应付。现在,将这种条件推向极端。假设你只有四个名词:kiki、bouba、朱丽叶和太阳。当选择减少时,那些原本可能显得微不足道的联觉或其他共同点元素的 গুরুত্ব 会被放大。
朱丽叶不尖锐,所以 bouba 或太阳,两者都是圆形的,比 kiki 更合适。(如果朱丽叶有过尖锐的、愤怒的叫喊声,那么 kiki 会更有竞争力,但在这里她不是那种人。)还有其他各种微小的重叠,使得朱丽叶比 bouba 更像太阳。
如果有限的词汇量必须被扩展以覆盖大范围的领域,那么词语质量之间任何微小的差异几乎就意味着天壤之别。大脑是如此渴望关联,以至于它会放大任何微小的潜在联系,以获得一个可用的联系。(当然,这个隐喻在戏剧中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朱丽叶像太阳一样落下,但她死后,并不会像太阳一样回来。我们都只能希望她在这方面真的更像太阳。或者也许朱丽叶的原型总是像太阳一样回归——一个好的隐喻会渗透到一个不断增长的互动思想社区中。)
我绝不是莎士比亚的学者,但在我看来,这位伟大的作家在创造隐喻时,通常并没有追求他词汇量的极限。他的词汇量很大——近 30,000 个词,但他通常会选择常用的小词,尽管是用令人震惊的组合方式,来描述朱丽叶、哈姆雷特或其他重要事物。
同样,许多最富表现力的俚语来自于那些正规教育贫乏或不适用的人,他们创造性地使用他们所知道的词语。这在皮钦语、街头俚语等方面都是如此。最具启发性的词语通常是最常用的词语,并且以最多样化的方式使用。意第绪语:Nu? 西班牙语:Pues. . . .
太阳的隐喻之所以让我着迷,部分原因在于它涉及到信息科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冲突:意义是可以被紧凑而精确地描述的,还是只能从大量组件的统计关联中近似地出现?数学表达式紧凑而精确,大多数早期计算机科学家认为,至少语言的一部分也应该具有这些特性。在我 2006 年 8 月的专栏中,我描述了像自动语言翻译这样的任务,统计方法似乎比紧凑、精确的方法更有效。我还反对在语言演化初期存在一个小的、定义明确的词汇表的可能性,并倾向于一个从未精确定义的涌现词汇表。然而,至少还有一种我没有在 8 月份专栏中描述的可能性:词汇表可能是涌现的,但可能有一个外部因素最初阻碍了词汇表的增长,尽管涌现过程本身可能倾向于它。
bouba/kiki 动态以及大脑中的其他相似性检测过程,可以被设想为创造一系列无限隐喻的基础,这可以对应于一个无限的词汇量。但太阳的隐喻,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可能只出现在词汇量至少有些有限的情况下。想象一下,在发明语言的同时,你拥有无限的词汇容量。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为每一个需要表达的新事物创造一个任意的新词。一个压缩的词汇量可能会产生不那么任意、更具启发性的词语。
也许早期人类有限的大脑容量是词汇量大小受限的根源。无论原因是什么,有限的初始词汇量可能是产生富有表现力的语言的必要条件。当然,一旦语言建立起来,词汇量以后总是可以增长的。现代英语拥有庞大的词汇量。试试谷歌搜索“hystric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