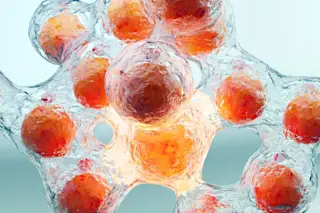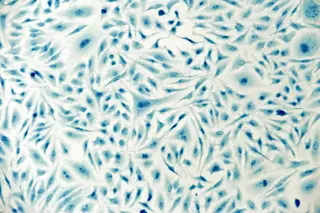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 现代进化遗传学起源于20世纪初的一系列智力辩论。其中大部分内容在Will Provines的《理论群体遗传学起源》中有概述,虽然弗朗西斯·高尔顿的传记也同样有用。简而言之,在此期间,查尔斯·达尔文的继承者们在遗传的本质上存在冲突(据我所知,达尔文在此问题上留下了含糊不清的说法)。一方面,你有一群围绕着格雷戈尔·孟德尔关于通过基因抽象来实现的离散和离散遗传思想的拥护者威廉·贝特森。另一方面,则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的追随者,由数学家卡尔·皮尔逊和生物学家沃尔特·韦尔登领导。这个“计量学派”关注连续特征和达尔文的渐进主义,可以说是数量遗传学的前身。他们信奉“高尔顿主义”观点存在一定的讽刺意味,因为高尔顿本人对离散遗传模型并非没有同情!

威廉·贝特森 最终科学和真理取得了胜利。在计量学派传统中接受训练的年轻学者不断地转向孟德尔阵营(例如,查尔斯·达文波特)。最终,现代统计学和进化生物学的创始人之一R. A. Fisher在他的开创性论文《基于孟德尔遗传假说的亲属相关性》中融合了这两种传统。孟德尔学说为何不损害经典达尔文理论的直觉很简单(诚然,一些最初的孟德尔学支持者似乎认为这是一种违反!)。许多对性状有中等或小影响的离散基因可以通过中心极限定理产生连续分布。事实上,经典的遗传学方法通常难以将具有超过半打显着基因座的性状视为除了数量和连续性之外的其他东西(考虑色素沉着,我们通过基因组学方法知道它在不同种群中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半打左右的连锁基因)。

致谢:Richard Wheeler 请注意,我没有提及DNA。这是因为在理解DNA是遗传的基质之前的40年,科学家们已经通过孟德尔过程很好地掌握了遗传的本质。基因本质上是一个抽象的单位,一个可以被操作的分析元素,使我们能够清晰地追踪和预测跨代的变异模式。碰巧的是,基因是通过DNA生物分子的序列在物质意义上实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现代遗传学的物质基础,所以它是一门比经济学更基础的科学(经济学仍然陷入其“计量时代!”)。“后基因组时代”是建立在对DNA序列和结构形式的遗传物质基础进行工业规模分析的基础上。但我们不应该将DNA(具体的碱基)与经典的孟德尔学混淆。对物质和具体的关注不仅限于遗传学。在21世纪中期,曾经流行过认知神经科学fMRI研究,这些研究被认为比经典的认知科学对“思维运作方式”的理解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随着fMRI“科学”由于严重的 th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而衰落,我们不得不重新依赖不那么迷人的心理学抽象,这些抽象可能不像物质理解那样容易被还原,但它们具有信息性的优点。这让我联想到最近一篇关于与教育相关的SNP在庞大队列中的论文,对126,559名个体进行全基因组关联研究,识别与教育成就相关的遗传变异。您还应该阅读随附的常见问题解答。底线是,作者们已经令人信服地确定了三个SNP,它们在他们庞大的数据集的教育成就变异中解释了0.02%。将所有具有某种关联的SNP汇集起来,它们解释了约2%的变异。这并不特别令人惊讶。几年前,这篇论文的作者之一写了大多数报告的与一般智力相关的基因关联可能都是假阳性。那些在人类遗传学领域记忆力更长的人,在我21世纪初就警告我这个问题。更有统计学头脑的朋友从2007年开始警告我。那时,我开始告诫那些认为基因组学将揭示正常智力变异的变异的人,因为看起来可能需要比我预期的更长的时间。正如上面论文所暗示的,先前的研究强烈暗示,智力的遗传结构是这样的:正常范围内的变异是由人群中无数的小效应等位基因控制的。否则,经典的遗传技术可能已经能够更确定地检测出基因座的数量。如果你读过人类群体遗传学,你会注意到,通过经典的杂交技术和系谱,遗传学家在60年前就已经大致收敛到解释欧洲和非洲色素沉着之间变异的连锁基因座的数量!一些我的朋友一直在争论这些小效应大小证实了智力变异主要是环境因素的观点。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我想将讨论范围限制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方面是,可以说在最特权的人群中,智力是最可遗传的。我所说的可遗传是指由基因控制的性状变异的组成部分。当你消除环境变异(即剥夺)时,你就剩下基因变异。在家庭内部,兄弟姐妹之间的智商差异很大。相关性约为0.5。不算差,但也不算很高。当然,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认为我现在要谈论双胞胎研究。根本不是!尽管科学记者似乎喜欢从事像Slate的Brian Palmer这样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但经典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基因组学所证实,但正是通过观察非近亲个体,才建立了对智力可遗传性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上面研究的主要作者之一也是之前链接的作者,这并非巧合。
承认评估性状变异的具体物质位点存在困难,即使能够有把握地推断出这种关联,也并不矛盾。
DNA出现之前就有遗传学。并且,即使没有特定的SNP,也存在可遗传性。此外,我想为“环境”变异成分增加一个注意事项。出于技术原因,这个环境成分实际上可能包括相对固定的生物变量。基因-基因相互作用或发育随机性可能值得考虑。尽管这些从亲代到子代的关联很难或不可能预测,但它们并不像从贫困儿童环境中去除铅那样简单。我个人怀疑,同卵兄弟姐妹之间智力的大幅差异告诉我们“环境”变异的难以控制和引导的性质。最后,我想指出,即使是小效应的基因座也并非微不足道。作者们在他们的FAQ中提到了这一点,但我想说得更清楚,小基因效应并不能排除药物开发
以胆固醇水平为例。已经对该性状进行了大规模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识别了大量的小效应基因座。其中一个基因座是HMGCR,它编码HMG-CoA还原酶,这是胆固醇合成中的一个重要分子。鉴定的等位基因将胆固醇水平提高了0.1个标准差,这意味着基因检测在预测胆固醇水平方面几乎没有能力。根据Newsweek文章的逻辑,任何以HMGCR为目标的药物都不会有成为畅销药的机会。任何医生都知道我的意思:目前世界上销量最好的药物之一是他汀类药物,它们抑制HMGCR(基因产物)的活性。当然,他汀类药物已经问世,所以这是一个有些经过挑选的例子,但我猜想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数据中还有数十个类似的例子等待被发现。找出哪些GWAS命中具有潜力成为药物靶点需要时间和努力,以及相当多的运气;在我看来,这是Decode(并非令人惊讶的教训)的主要教训——药物开发真的很难。
附录:我大多数有生物学本科学历、学过一些数量遗传学的朋友,似乎都猜测智商的遗传度为0.0到0.20。这太低了。但知道这一点重要吗?我认为,在评估潜在伴侣的前景时,准确的遗传图谱可能很有用……引文:Rietveld, Cornelius A., et al. "GWAS of 126,559 Individuals Identifies Genetic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Educational Attainment." Science (New York, NY)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