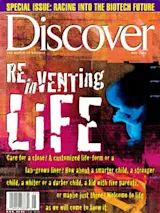妈妈,婴儿是从哪里来的?自从鹳鸟第一次送来婴儿,父母们就一直害怕这个问题。但今天的爸爸妈妈们需要解释的比他们自己的父母想象的要多得多。尽管关于“鸟和蜜蜂”的讨论从来都不容易,但其要素相当直接:烟花爆炸,火车穿过隧道,海浪拍打海岸,偶尔提到解剖学。曾几何时,生孩子就等同于做爱,冷冻卵子是用来做糕点面团的,电话响七声你应该挂断,而不是你子宫里能装下多少个胎儿。
然而,如今,生命的事实听起来很像科幻小说,因为20世纪末的人类正在努力应对非性交受孕的兴起。现在有十几种方法可以生孩子,其中绝大多数都绕过了过时的性交行为。过去三十年见证了生育药物、体外受精、捐赠卵子、捐赠精子、捐赠胚胎和代孕母亲等高科技干预的出现。还在研发中的有更先进的技术,例如细胞核移植、胚胎分割,甚至,如果至少有一个人愿意,还可以克隆成年人。
这些技术通常归于辅助生殖的范畴。所有目前使用的技术都是为育龄不孕夫妇首创并通常由他们使用的。但它们也被那些对生育有不那么传统观念的人所使用——单身人士、绝经后妇女和同性伴侣。在不久的将来,辅助生殖可能会成为任何想要怀孕且负担得起的人的标准程序。当然,其吸引力在于控制:控制为人父母的时间,控制胚胎质量,控制遗传疾病,控制性别等不那么有害但同样由基因决定的特征。
到目前为止,由于联邦政策和社会偏好,辅助生殖的实践基本上不受监管。一位专家甚至称之为医学的“狂野西部”。它也很昂贵、麻烦、低效,并伴随着伦理复杂性——但这些考虑都没有减缓其增长。自1978年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以来,美国生育诊所的数量已从不到30家增加到300多家。数十亿美元的生育产业已经创造了数万名婴儿。辅助生殖缓解了那些几十年前不得不放弃生孩子希望的男人和女人的痛苦。它也创造了一个世界,死人可以使陌生人怀孕,女人可以出租自己的子宫,一个孩子可以有五个父母——但最终仍可能成为孤儿。这个新世界将如何改变家庭的意义尚不清楚。但它已经改变了曾经被称为“生育奇迹”的事物。
去年11月,在爱荷华州,一对夫妇创造了历史,登上了全国电视,并成为《时代》和《新闻周刊》的封面,因为他们的七个孩子都活着出生了。当被问及如何应对突然增加的子女时,麦考伊夫妇告诉记者:“我们信赖上帝。”但为了第二次怀孕,博比·麦考伊信任的是Metrodin,一种刺激卵巢卵子成熟的生育药物。服用Metrodin的女性一个月可以产生几十个卵子,而不仅仅是一个。
Metrodin属于一系列用于增加卵子发育和释放或排卵的激素。生育药物有许多品牌名称,如Clomid、Pergonal、Humegon、Fertinex、Follistim,其中一些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排卵不规律的女性在生育药物提高成功率后,通常可以通过传统方法怀孕。
即便如此,服用生育药物也和服用阿司匹林不同。大多数药物需要每天注射,夫妇们会被训练自行操作。药物本身并不便宜——例如,一剂Fertinex大约60美元——而且大多数医生会通过超声波检查和血液检测监测卵子成熟的进展,这会增加总成本。最终,一个生育药物治疗周期可能花费超过1500美元。
而且存在风险。最常见的是多胎妊娠:同时受孕两个或(更多)胎儿,就像麦考伊夫妇那样。尽管爱荷华州七胞胎的到来伴随着庆祝的气氛,但这种怀孕实际上对准父母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困境。多胎妊娠会增加母亲并发症的几率,如高血压和糖尿病。它们对未出生胎儿的风险甚至更大。多胎妊娠中的胎儿比单胎胎儿更容易发生流产、出生缺陷、低出生体重和早产,以及早产可能导致的终身问题——包括脑瘫、失明、肾衰竭和智力迟钝。
有一些方法可以避免多胎妊娠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如果超声波扫描显示大量卵子即将释放,就禁欲。然而,统计数据表明,许多夫妇选择不使用这种选项。一般人群中多胎妊娠的发生率为1%到2%,而接受生育药物治疗的女性中,这一比率可能高达25%。
处理多胎妊娠风险的另一种方法是在胎儿出生前消除一些胎儿。不孕症专家称之为选择性减胎。该手术在怀孕第三个月之前进行,通过向选定的胎儿注射氯化钾来停止心跳。医生会将针头通过准妈妈的腹部或阴道插入,进行注射。
像大多数辅助生殖技术一样,选择性减胎在解决医学问题的同时,也引入了伦理问题。对于许多夫妇来说,决定是否减胎以及减胎多少是痛苦的。一些人,包括麦考伊夫妇,干脆拒绝这样做。另一些人则接受这种痛苦——以及讽刺——将销毁多余胎儿视为他们状况的一个不幸后果。然而,还有一些人对这项技术感到足够放心,将其用于实际而非医学原因。美国生殖医学学会执行董事本杰明·扬格说:“有些病人会非常努力地要求从三个胎儿减到两个。他们会说,‘医生,我应付不了三胞胎。’”
如果一对不孕夫妇选择进行更先进的辅助生殖程序,选择性减胎只是他们可能面临的几次考验之一。“我想我从未做过如此困难的事情,”一位波士顿妇女承认,她在两年不断升级的干预后怀孕。“你必须真的想要它。”
凯瑟琳·格雷文和她的丈夫在格雷文34岁时决定组建家庭。经过九个月的常规尝试后,他们去当地诊所进行了生育检查。不孕症有多种原因,包括女性荷尔蒙失衡、男性精子数量低,以及任何一方生殖道堵塞。但检查未能确定格雷文夫妇的具体原因,所以他们的医生建议保守治疗。在连续三个月里,格雷文口服生育药物Clomid,以刺激卵子产生,然后与她丈夫的精子进行人工授精。当这不起作用时,格雷文改用皮下注射的Fertinex。在两次Fertinex和人工授精也失败后,这对夫妇决定尝试体外受精。
体外受精(IVF)是辅助生殖技术的基石。该程序——将成熟卵子从卵巢中取出并与精子一起培养——大大改善了传统体内受精的随机性。它也带来了另一层复杂性和费用。除了促卵成熟激素,接受IVF的女性通常会服用一种多变药物混合物,旨在抑制然后触发成熟卵子的释放。取卵手术,通过将一根空心针穿过阴道壁进入附近的卵巢进行,被描述为一个小手术。(“第二天我感觉就像一台Roto-Rooter管道疏通机在我体内穿过一样,”格雷文说。)然后受精胚胎必须被转移回子宫。
当格雷文的试管受精尝试也失败后,她的医生推荐了一种更先进的技术:配子输卵管内移植(GIFT)。在这个过程中,卵子被取出,与精子混合,然后送回输卵管——卵子和精子通常在那里相遇——进行受精。GIFT需要一个更长时间、更复杂的手术,在患者腹部有三个切口,大约需要两天恢复。但其成功率比IVF高5%到10%。这项技术对格雷文奏效了:她将在7月分娩,届时37岁。
GIFT是IVF主题的几种变体之一,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当时不孕症专家寻求扩展他们在辅助生殖方面的技能(见第80页的侧栏)。然而,即使有了这些创新,辅助生殖的效率也令人警醒。格雷文的经历代表了许多不孕夫妇可能经历的事情,除了一个方面:格雷文怀孕了。IVF的成功率取决于患者的年龄,并因诊所和程序而异。但大致的数字——所谓的“抱回婴儿率”——是每五个IVF周期有一个活产。不孕症专家指出,这些程序的成功率每年都在提高,而且在任何给定的月份,一对生育夫妇通过传统方式受孕的机会也是五分之一。根据美国生殖医学学会的数据,如果所有不孕夫妇坚持足够长时间的辅助生殖治疗,超过一半的人可以怀孕。
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大约一半的人无论接受多少治疗,都永远无法拥有自己的孩子。而且,通过常规方式生孩子是免费的。如果一开始没有成功,你可以反复尝试,而无需办理二次抵押贷款。另一方面,一个IVF周期的费用在8000到10000美元之间。像GIFT这样的特殊选项可能费用更高。格雷文的大部分治疗费用无需自付,因为马萨诸塞州是十个强制保险覆盖不孕症治疗的州之一。她的怀孕费用本会远远超过25000美元。
值得吗?市场说是。尽管不孕不育率保持不变,但在过去二十年里,不孕不育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如今,美国约有600万夫妇存在生育问题;其中一半寻求医生帮助,约四分之一最终尝试辅助生殖。这些夫妇是将这些尝试视为祝福还是诅咒,取决于结果,“取决于结果”,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的全国不孕不育支持组织“Resolve”求助热线主任玛格丽特·霍利斯特说。“治疗压力大,费用高,而且需要投入大量时间。”
当然,这些也可以用来形容为人父母。然而,与不孕不育相关的压力可能特别有害。波士顿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不孕症行为医学项目主任爱丽丝·多马尔发现,尝试通过辅助生殖怀孕两年或更长时间的女性,其抑郁症发生率与癌症、心脏病和艾滋病患者一样高。她还发现,严重抑郁症患者在治疗抑郁症后,受孕率会提高。
多马尔利用她的研究结果来论证不孕症应被视为一种严重的医疗状况,并且需要对大脑和生殖机制之间的联系进行更多研究。问题是,多马尔的研究未能确定她的受试者的抑郁症是否由不孕症本身或不孕症治疗的苦难引起。不孕症患者在描述他们与辅助生殖的经历时,使用了“过山车般的旅程”、“上瘾”和“痴迷”等词语。生育药物因引起情绪波动以及痉挛、体重增加和腹胀而闻名。而追踪排卵的要求可以让人生活翻天覆地。在周期的某些阶段,患者可能每天访问她的试管婴儿诊所一次甚至两次,进行血液检查、超声波扫描和注射。“你的生活开始围绕着你周期的开始、中期和结束,”格雷文说。“监测你的身体成为一项全职工作。”
此外,通过辅助生殖追求生育,意味着要面对超出大多数人道德雷达范围的伦理决策。由于IVF技术常导致多胎妊娠,选择性减胎也成为一个问题。接受IVF的夫妇还必须决定一次受精和移植多少个卵子(这与多胎妊娠问题相关),是否要创建和冷冻胚胎以备将来使用,以及任何未使用的冷冻胚胎最终应如何处理。前配偶曾为冷冻胚胎争夺监护权,至少有一个案例中,经手的IVF诊所声称胚胎是其合法财产。从法律上讲,人类胚胎拥有其独特的灰色地带,介于人类生命和某种稀有财产形式之间。
辅助生殖也促使人们根据遗传特征对胚胎进行预筛选,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所有道德困境。筛选通过从一个八细胞胚胎中取出一个细胞,并分析细胞核中的染色体或DNA来完成。一些诊所已经提供对体外胚胎进行与囊性纤维化、血友病和肌肉萎缩症相关的基因筛选。夫妇可以决定他们创造的哪些胚胎符合他们的要求;被拒绝的胚胎可以丢弃或捐赠用于研究。
最后,辅助生殖为各种配子交换和代孕打开了大门,从最简单和最古老的方法——通过捐赠者的精子进行人工授精——到更复杂的方案,其中可能使用捐赠卵子、捐赠精子和捐赠胚胎的任何组合。除了生物代孕(创造了著名的“M婴儿”的方法)之外,妊娠代孕者将同意怀胎并生下一个与她们没有遗传关系的孩子。现在,一个人可以通过从捐赠者那里获取卵子和精子,并雇用一名代孕母亲来完成其余的工作(这已经做到了)来拥有一个孩子。一个女人可以仅仅出于美容或方便的原因使用代孕母亲(这也已经做到了)。死者的精子可以被提取并用于使其寡妇受孕(同样如此)。绝经多年的女性也可以生育(这也已经发生)。
去年十月,另一起非同寻常的诞生占据了新闻头条,一位卵巢功能失调的女性在亚特兰大生殖生物学协会的帮助下,分娩了两名健康的男婴。该协会利用冷冻两年多的捐赠卵子,成功地实现了这对双胞胎的受孕。由于人类卵子体积庞大且复杂,使其在冷冻过程中比精子更容易受损,因此卵子冷冻保存的方案一直难以完善。事实上,直到最近,大多数卵子冷冻尝试都失败了。这对双胞胎是美国首例通过此技术诞生的。
尽管生殖生物学协会的成就很快被爱荷华州七胞胎的到来所盖过,但卵子冷冻这项壮举具有更重要的影响。一旦广泛普及,冷冻保存将为女性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储存她们年轻的卵子以备将来使用。衰老卵子的缺陷被认为是导致老年女性生育力下降的原因;事实上,捐赠卵子技术已经证明,女性生殖系统的其他部分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通过确保女性终生拥有可用的配子,卵子冷冻可以帮助她们战胜生物钟。
当然,女性随后将出于自身便利而非治疗现有疾病而使用辅助生殖。在这方面,卵子冷冻呼应了辅助生殖的一个普遍主题。目前的技术是为了帮助有特定医疗问题的患者而开发的——例如,卵子冷冻将允许卵子可能被辐射破坏的癌症患者在治疗前保留一些配子。然而,不孕症研究的成果不可避免地扩展了所有男性和女性的生殖选择。而这些选择对个人或社会来说并非总是容易接受的。
一个显著的例子来自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生殖内分泌学家杰米·格里福的实验室。为了在另一项挑战生物钟的努力中,格里福正在将老年女性卵子的细胞核转移到已去除细胞核的年轻卵子中——即去核卵子。当这些杂交细胞被人工刺激分裂时,转移的细胞核没有显示出典型老年卵子的染色体异常。格里福的工作仍处于研究阶段,但他希望最终能使这些卵子受精并植入他的患者体内。
格里福并非在克隆人类,但他的实验借鉴了既有的哺乳动物克隆技术。绵羊6LL3,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多莉,就是通过将成年细胞的细胞核转移到去核卵子中而创造出来的。格里福强调他只关心卵细胞之间的转移,目的是治疗不孕症;他说他强烈反对人类克隆,而且无论如何,研究人员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弄清楚如何实现。但事实是,这是可能的,他说。“我只是想不出任何临床指征。”
如果格里福想不到,其他人会想到。物理学家出身的不孕症企业家理查德·西德,在一月份登上头条,当时他宣布正在寻求资金建立一个克隆成年人的实验室。
早在多莉诞生之初,国家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就建议禁止人类克隆。最近,克林顿总统重申了他对人类克隆研究实行五年暂停的呼吁。但美国生殖医学学会,一个发布辅助生殖技术使用伦理指南的组织,采取了中间立场。“我们不支持克隆现有或曾经存在的个体,”扬格说。“但这并非说克隆技术不好。例如,克隆的神经细胞培养物可以用于治疗脊髓损伤,”他说,“我们不希望看到研究被限制。”
该协会也表示赞成继续胚胎孪生研究——这是一种迄今为止只在动物身上进行过的程序,其中一个胚胎被分割以产生两个基因相同的个体。该协会的理由是,胚胎孪生技术可以为不孕夫妇提供两倍的胚胎用于植入。但是,如果例如,其中一个孪生胚胎被冷冻,直到其兄弟姐妹长到成年,那么克隆和孪生之间的区别就变得模糊了。
辅助生殖的批评者担心,今天的创新将成为明天的必然。一些不孕夫妇已经感到被选择的目录所困。威斯康星大学法学教授、国家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成员R. 阿尔塔·查罗说:“所有这些技术,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选择,使得人们很难说‘不,我们已经尝试够了’。选择并非坏事——但也不是全然的好事。”
而缺乏监管只会加剧辅助生殖周围的问题。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生物伦理学家亚瑟·卡普兰说:“这个领域急需监管、监督和控制。阻碍我们这样做的观念是个人应该拥有生育自由。”
关于堕胎的怨恨也阻碍了对辅助生殖技术的监管。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立法禁止联邦政府资助人类胚胎或胎儿组织研究,以回应担忧此类研究会鼓励胚胎和胎儿贩运。然而,这项禁令并未适用于私人资助的项目;因此,大多数辅助生殖研究都在联邦监管和监督范围之外进行。
包括格里福在内的辅助生殖专家表示,这样做也很好——监管者不会理解这项工作的技术和道德复杂性。但由于大部分实验都在私人诊所进行,患者——以及他们的孩子——可能成为小白鼠。即使夫妇不直接参与实验程序,他们也可能面临不舒服的选择,例如捐赠配子或胚胎的经济诱惑。
“人们常常感到被环境所迫——‘我们还能做什么?’”巴鲁克学院社会学教授芭芭拉·卡茨·罗斯曼说,“我不确定我们应该如何做出这些决定,但我很确定它们不应该由市场来决定。”
市场力量影响的不仅仅是不孕夫妇。尽管卵子比精子稀有且难以获得得多,但年轻女性捐赠者通常只获得微薄的补偿,以弥补她们的时间和精力。但2月份,《纽约时报》报道称,新泽西州利文斯顿的生育诊所圣巴纳巴斯医疗中心已开始向年轻女性提供5000美元捐赠卵子——据报道,这个价格是竞争对手的两倍。与器官买卖(非法)不同,有限地支付卵子是合法的。美国生殖医学学会的专业指南将其视为“身体产物”,而非“身体部位”。
许多观察家担心,受新科技不慎使用的最大影响的不是辅助生殖的参与者,而是他们的孩子。例如,随着辅助生殖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孩子面临早产的风险:自1971年以来,美国每年多胎出生数量增长了四倍多。科学家和伦理学家都曾发声反对帮助单身、绝经后母亲受孕,认为创造可能成为孤儿的孩子是道德上应受谴责的。一些人质疑代孕或配子捐赠等可能分散父母责任的安排的智慧。一些研究人员关注辅助生殖程序本身的安全性。一项近期——且有争议的——针对420名儿童的澳大利亚研究表明,通过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即将单个精子注射到孵化中的卵细胞中)辅助生殖的婴儿,心脏、生殖器和消化道等主要出生缺陷的风险是其他婴儿的两倍。
“我们对哺乳动物胚胎进行的任何体外操作都会给它带来压力,”20年前主持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的专家罗伯特·爱德华兹说。“但科学界负有巨大责任,要评估和消除新程序的任何不良后果,”他说。
其他评论员指出,辅助生殖中参与者和后代的权利仍未明确。关于通过捐精受孕的孩子是否有权知道其生父身份,各州的法律差异很大。“我们从未解决围绕人工授精的问题,”波士顿大学法律、医学和公共卫生教授乔治·安纳斯说,“我们只是假装解决了。然后我们将这些问题引入了新技术。”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快速发展,伦理和法律问题只会变得更加复杂,解决这些问题的任务将落在后代肩上。但这也许是恰当的,如果对帮助他们诞生的技术做出判断的是辅助生殖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