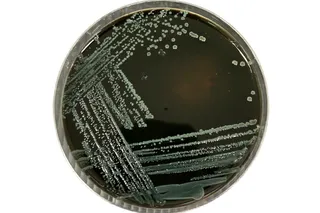我必须说实话。病人目光锁定在我的脸上,探究着,搜寻着诚实,紧跟着我的一举一动,又一次问道:“所以这是判死刑?”
我的办公室墙壁仿佛向我逼近。我的手心开始出汗,那些在我脑海中如此 the 秀的言辞,一旦到达唇边便夭折了。“是,”我只能挤出这个字。
他嘴唇因用力而颤抖。“那还有多久?”他问道。
在我开口之前,我仔细地衡量着我的想法。“因人而异,但三到五年是个合理的估计。”
我停顿了一下。杰瑞没有回应;也不需要回应。不想听起来过于陈词滥调,我没有再说别的,让这次短暂的交流就此结束。
医生在面对病人时的艰难时刻,没有可以参考的指南。对我这个神经科医生来说,没有任何谈话比在那个美好的夏日与杰瑞的谈话更令人痛苦。
这位 47 岁的病人说,他在一年前来看我之前就注意到肌肉抽搐。起初不频繁,但这些他称之为痉挛的症状,现在变得持续不断,并且在他的手臂和腿部最为明显。他没有抽筋,觉得肌肉体积没有变化,并且认为自己的力量是正常的。
尽管杰瑞仍然活跃于业余地质学研究,但疲劳正在一点点吞噬他对生活的激情。像系衬衫纽扣或端咖啡杯这样简单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困难。杰瑞说他的腿不再正常地移动,这使得短暂的行走变得疲惫,有时甚至令人沮丧。
除此之外,杰瑞的健康状况良好。他没有服用任何药物,他的家人也没有神经系统疾病史。他病史中唯一其他相关的记录是,他说话带有一种略带鼻音的腔调,他将其归因于季节性过敏。
带着一种恐惧感,我开始了杰瑞的检查。通过详细询问病史,大多数医生在检查开始前就知道会遇到什么,而在检查杰瑞时,我的脑海中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大多数都不好,有些更糟,而且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都与神经肌肉有关。
杰瑞的记忆力、视力、听力、吞咽和感觉都正常。他的说话不含糊,但异常地带有鼻音——我却知道这并非过敏所致。我注意到他的舌头、肩膀、手臂和大腿几乎持续地抽搐。他的力量很好,但他的手和脚的一些肌肉萎缩了,或者说比同龄同体型的人预期的要小。杰瑞检查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他的步态。他走路时,腿部以一种僵硬、机械的方式移动。他看起来就像在走高跷。
作为一名专家,我经常被要求提供第二意见,而这正是杰瑞来找我的原因。他已经被“打探”、“摸索”过,并且不经意间得到一个无法逃脱的诊断。现在他希望我确认。杰瑞的医生告诉他,他患有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或称卢伽雷氏病。我告诉他,我认为他们的诊断是正确的。
控制自主运动的信号起源于大脑运动皮层的神经元。它们向下延伸到脊髓的神经元,然后传递到个体肌肉。在 ALS 中,大脑和脊髓的运动神经元退化,最终停止向肌肉发送信号,这导致肌肉萎缩和抽搐。ALS 只影响运动神经元,因此患者保留由其他神经元控制的感觉。他们仍然有言语(尽管可能含糊不清或带鼻音)和记忆,以及嗅觉、触觉、味觉、听觉和视觉。随着疾病的进展,自主运动能力会丧失;最终,膈肌受影响,无法自主呼吸。大多数患者在出现第一个症状后三到五年内死亡。
为什么运动神经元在 ALS 中死亡尚不清楚。一种主要的可能性集中在大脑化学物质谷氨酸上。几项研究表明,ALS 患者的血清和脑脊液中谷氨酸过量,而长时间暴露于谷氨酸对运动神经元有毒性。第二种理论认为,自由基(可能损害细胞的代谢副产物)的失控形成会损害运动神经元。最后,几条研究线索表明,一种侵袭性的自身免疫反应可能是罪魁祸首。最终,原因可能是这三种理论的结合,或者完全是意想不到的。
这种疾病,因 1941 年夺走了伟大洋基队球员的生命而被称为卢伽雷氏病,最常见于 40 岁以后。在美国,约有 30,000 人患有 ALS,每年新诊断出约 5,000 例。早期症状包括肌肉僵硬、虚弱和抽筋,言语含糊不清或带鼻音,以及咀嚼或吞咽困难。患者常常会注意到跑步或走路时的笨拙,以及系衬衫纽扣或转动钥匙时的困难。随着虚弱的加剧,肌肉萎缩和抽搐变得更加明显,最终说话、吞咽、呼吸和行走会受到严重影响。
诊断需要临床经验——识别上运动神经元和下运动神经元的体征和症状——以及实验室检查和大脑及脊髓的神经影像学检查。这些检查结果通常是正常的,有助于排除其他疾病,如肌病(肌肉纤维疾病)或脊髓病(脊髓疾病)、多发性硬化症和脊髓灰质炎后遗症。在某些情况下,传染病如莱姆病可能模仿 ALS 的症状。通常会进行肌电图检查,这项技术可以记录肌肉的电活动,某些肌电图结果可以支持 ALS 的诊断。
ALS 没有治愈方法。主要治疗药物是利鲁唑,它被认为可以通过减少谷氨酸的释放并减轻对运动神经元的损害来发挥作用。在临床研究中,利鲁唑将患者的生存期延长了几个月,并延长了患者需要呼吸器的等待时间。除了利鲁唑,还有治疗疲劳、肌肉痉挛、疼痛、失眠、抑郁和唾液过多的药物。医生、物理和言语治疗师、社会工作者,以及居家护理和临终关怀护士,还有帮助家庭成员应对的咨询师,通常都会参与其中。
在预约快结束时,我向杰瑞解释了我所知道的关于 ALS 的情况。然后,我觉得让他主导接下来的谈话很重要。无论沉默多么令人不适,我都压制住了继续说话的冲动。
几分钟后,杰瑞就实验性治疗、替代疗法和临终关怀问题问了我几个深思熟虑的问题。他告诉我,他还没有决定如何进行,但还是拿了利鲁唑的处方。“宁可小心谨慎,”他说。
在与病人谈论死亡和临终问题时,没有手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培训。医生只能通过经验和他们与生俱来的医疗天赋来培养必要的技能。大多数医生只需要偶尔与病人及其家属讨论这些问题。然而,神经科医生必须经常这样做——在办公室、急诊室或重症监护室,在那里脑死亡是一个过于常见的话题。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在谈论死亡和临终时,病人及其家属会以尊严的态度对待。但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情绪。有些病人及其亲属会感到震惊、愤怒和狂怒。就像人们各不相同一样,他们对绝症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很难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如果我知道,那就无所谓了:根据我的经验,传递坏消息永远不会变得容易。每一次,我所感受到的悲伤都变得更难以承受。
John R. Pettinato 是一名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的神经科医生和骨科医生。Vital Signs 中描述的案例是真实故事,但作者为保护患者隐私,已更改了部分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