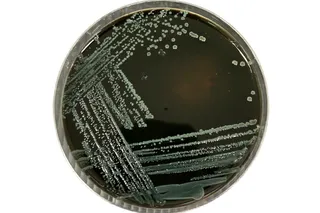在电影《美丽心灵》的结尾,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数学家约翰·纳什决定不再服用药物,也不再住院,尽管他仍然经历着无休止的妄想。“如果我能想通这一点,”他向他饱经磨难的妻子解释说,“我就可以做得更好。”她握住他的手,放在她的头上。“也许分辨梦境与现实的部分,也许不在这里,”她说。她将他的手向下移到她的心脏。“也许在这里。”
这是一个古老的比喻,但却是一个错误的。几十年后,当电视观众在经典电影频道看到《美丽心灵》时,爱存在于心脏而非大脑的观念,将像放血疗法一样荒谬。这是因为爱的生理现实与肝脏无关,也与心脏无关。像所有情感一样,爱无疑源于大脑,正如辉煌的数学定理一样。我们感受到爱的激情,因为我们的大脑包含特定的神经化学系统,这些系统在我们体内产生这些感受。我们不是在心与脑之间挣扎,而是在大脑的不同部分之间挣扎,这些部分专门负责理性思维的基石,如长期规划,而另一些部分则赋予我们的生活情感色彩。
研究大脑的科学家传统上花费更多时间探索负面情绪反应的神经通路:在我们当前的心智地图上,恐惧区域被清晰地描绘出来。而爱与依恋的王国则不然,直到最近,它一直是一片广袤的未知之地。但是,一幅新的爱情画卷已经开始浮现,其核心是一种迷人的激素——催产素,它很可能步血清素的后尘,后者在十几年前百忧解问世时进入大众意识。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大脑生物化学能够理解难以捉摸的爱恋的时代。
你泰山,我珍妮 1998年3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教授雪莉·泰勒在学校的韦斯特伍德校区听了一场客座讲座。主题是压力与“战或逃”本能,这是一个她颇为了解的领域,因为她研究人类应激反应已有20年。在讲座中,演讲者讲述了一个故事,关于他在压力情境下观察到的实验室老鼠的攻击性水平。在反复遭受电击后,这些老鼠开始互相撕咬,直至死亡。
“那在我脑中像灯泡一样亮了起来,因为这与我们通常在人类研究中看到的完全不符,”泰勒回忆道,她坐在她的校园办公室里,窗外松枝后是洛杉矶的城市景观。“我回到我的实验室小组,我说,‘你们如何看待动物研究和我们人类所见之间的这些差异?’其中一个人说,‘你知道,动物研究都是基于雄性。它们几乎不包括雌性,因为雌性周期变化太快。’然后另一个人说,‘你知道,我认为人类文献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开始查阅文献,看看女性对应激的反应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体现,结果是非常糟糕。1995年之前,女性只占参与者的17%。几乎没有研究有足够的女性参与者进行比较研究。”
性别不平等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几十年来,关于应激反应的科学文献围绕着一条基本的因果链:引入一个应激源——比如一只扑来的捕食者,或者一个竞争对手偷走你的食物供应——身体就会启动现在著名的“战斗或逃跑”反应。理论认为,面对压力时,我们的身体会本能地做好反击或逃跑的准备。“战斗或逃跑”符合达尔文时代“自然界弱肉强食”的刻板印象,但它没有给人类对创伤事件同样普遍的反应——向亲人寻求帮助——留下多少空间。父母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时,如果意味着保护孩子或伴侣,他们往往会让自己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这种无私的行为对任何感受过父母之爱或浪漫之爱的人来说都非常合理,但在“战斗或逃跑”的范式下,这种行为似乎是异常的。
泰勒怀疑“战或逃”反应只是故事的一半,而性别差异可能有助于揭示另一半。“我对我的团队说,‘好的,我们从头开始。女性在做什么?“战或逃”是女性对应激反应的合理描述吗?’几秒钟之内,我们所有人都立即回答:不。因为女性对应激的反应与男性的不同之处在于,女性的反应必须包含对后代的保护,至少在有后代的一段时间内是如此。我们的想法是,如果你是单独个体,战斗行为很有效,但如果你试图保护幼崽,战斗就行不通。逃跑也是一样——只有鹿等有蹄类动物的幼崽在出生后不久就能逃跑。”在听完那次客座讲座两年后,泰勒形成了一项新理论,以一篇发表在《心理学评论》上的文章形式呈现,题为《女性的应激行为反应》。她承认,“战或逃”是应对压力的一种方式,但还有另一种选择:关爱与结盟。你可以通过与威胁进行字面上的战斗来对抗威胁,或者你可以依靠你的朋友和家人寻求支持。
泰勒认为,“抚育”本能更常见于女性。“最近对28项不同研究进行了一项元分析,其中26项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寻求社会支持。除了分娩,人类中没有像这样的性别差异。对于大多数性别差异——男性在空间上略有优势,女性在语言上占优势——当你实际观察曲线时,存在巨大的重叠。”但当面对压力时寻求社会联系时,这种对比是显而易见的。
泰勒和她的团队甚至对“抚育”本能背后的大脑化学机制有了一个可靠的猜测。研究人员早已发现,在涉及强烈情感依恋的一些关键生活经历中,如出生、母乳喂养和性高潮,催产素肽会被释放。近年来,催产素水平升高也与压力经历有关。虽然催产素存在于男性和女性的大脑中,但证据表明雌激素会增强这种肽的作用,使其在男性体内由于睾酮水平而效力较低。如果存在一种生物学上的“抚育”本能,催产素可能发挥了作用。
泰勒的“关爱与结盟”理论在2002年她的著作《关爱本能》出版后,作为媒体流行语风靡一时,但其核心概念远不止一句口号。大脑中专门用于亲密关系和社会联系的回路可能与我们的恐惧机制一样复杂,这一观点已经酝酿了近十年。尽管一群充满攻击性的实验室老鼠可能为泰勒带来了她的“尤里卡时刻”,但对依恋的大脑科学的探索始于一个更不寻常的实验对象。
补充肾上腺素,或用催产素冷静下来 大约20年前,神经内分泌学家苏·卡特开始研究草原田鼠的大脑,以了解这种原产于美国中西部平原的小型啮齿动物为何是自然界中最浪漫的物种之一。交配后,大多数田鼠会终生保持一夫一妻制,像啮齿动物版的幸福家庭一样共同抚养幼崽。这至少可以说是自然界中一种不寻常的做法:不到5%的哺乳动物表现出一夫一妻制、双亲抚育的行为。
“那时我对催产素产生了兴趣,因为我知道催产素在性行为中释放,”卡特说。“已经有研究表明催产素促进绵羊的亲子关系。”当卡特将催产素注射到田鼠大脑中时,它们比平时更快地形成了联系。她和她的同事还从反向角度探索了催产素的作用,通过注射阻断催产素受体的化学物质,切断了这种激素的供应。田鼠的生活方式开始看起来不像《留给海狸吧》,而更像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不加选择地交配,没有任何持久的依恋。“催产素在结合中作用的最有力证据是,当你阻断催产素受体时,动物就不会形成配偶关系,”卡特说。
几年后,卡特的前同事,现任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的汤姆·因塞尔,开始了一项比较研究,分析草原田鼠和它们不那么一夫一妻制的近亲——山地田鼠的大脑。因塞尔发现了这两个物种之间一个显著的差异:在忠诚的田鼠中,催产素受体与多巴胺受体在大脑的一个叫做伏隔核的区域重叠;而在非一夫一妻制的田鼠中,催产素受体位于其他地方。伏隔核通常被认为是大脑重要的快乐中枢之一。多巴胺协调许多寻求和食欲行为。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田鼠中,催产素受体牢牢地植入大脑的奖赏回路中。这种结构表明,与催产素释放相关的行为会在草原田鼠的大脑中产生愉悦感,但对山地田鼠相对没有影响。如果催产素促使动物与伴侣保持依恋,那么草原田鼠如此忠诚也就不足为奇了。它们的大脑被设计成使形成依恋成为一种愉悦。
研究人员首次瞥见了使配偶结合变得可取的潜在回路。将田鼠研究推断到人类大脑化学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田鼠能给我们一个关于那个古老问题——为什么傻瓜会坠入爱河——的答案吗?
根据大多数说法,探索人类大脑中爱的神经化学基础已被证明是一项棘手的任务。当我问卡特设计人类实验的难度时,她笑了。“嗯,你想参加这项研究吗?我是说,这可是强大的东西。它对人类行为至关重要。假设你同意参与一项爱情研究,然后我为你随机选择一个伴侣?他们在电视上这么做,但在大学里你不能这么做。”
尽管存在固有的困难,许多近期研究揭示了人类爱情的大脑化学机制。与一夫一妻制的草原田鼠一样,人类的催产素受体位于大脑中几个富含多巴胺的区域,这表明催产素嵌入我们的奖赏回路中。一项研究比较了人们观看亲人照片和非浪漫朋友照片时的大脑活动。皮层活动模式根据受试者接触的面部类型而显著不同。对处理浪漫凝视的大脑进行的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与新妈妈倾听婴儿哭声时的大脑活动惊人地相似。它们也类似于吸食可卡因后的人的大脑图像。
面部识别研究尤其令人感兴趣,因为许多动物研究已经令人信服地将催产素与社交记忆的形成联系起来。一种假设是,在性高潮或分娩等关键配偶结合事件中释放的催产素有助于将伴侣或新生儿的形象牢固地刻印在脑海中。母乳喂养孩子的母亲经常描述婴儿在哺乳时凝视她们的强烈记忆。这些记忆的生动性及其与温暖感觉的关联,很可能就是催产素的印记。
催产素也被广泛认为与人类对应激的反应有关。“由于我个人抚养孩子的经历,我对母乳喂养作为一种保护机制产生了兴趣,”卡特说。“我们能够比较压力对泌乳期和非泌乳期女性的影响。对于泌乳期女性,我们知道她们有更多的催产素,我们也知道她们能更好地应对压力。”许多研究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催产素是科学家所说的身体应激轴系统的下调剂,该系统会产生当你得知升职未通过时所经历的那种沮丧、肠胃紧绷的感觉。受催产素影响的人比其他人有更小、更短暂的应激反应;坏消息似乎更容易从他们身上滑过。
应激反应与社会依恋之间的联系是泰勒“抚育本能”理论的核心。你可以通过消灭敌人来摆脱压力,也可以通过向亲人寻求帮助来减轻压力。就大脑化学而言,你可以通过补充肾上腺素来战斗或逃跑,或者你可以通过催产素来冷静下来,进行抚育和结盟。
爱情魔药9号不存在 尽管催产素的范围和效力构成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但泰勒警告说,它对人类情感的影响远非简单:“很多人说,‘催产素是拥抱激素’,或者‘催产素是爱情激素’。催产素比这更难以捉摸,它与心理状态没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试图将这些分子映射到特定状态是非常危险的。”
“例如,”泰勒向前倾身强调说,“与丈夫同住但发现丈夫不支持的年长女性,其催产素水平长期较高。现在尚不清楚因果关系的方向。但我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当社会支持需求未得到满足时,催产素水平会升高,作为寻求社会接触的信号。一旦找到,催产素可能会恢复到正常水平。所以催产素不是‘感觉良好’的激素。有时,它可能是‘感觉糟糕’的激素,促使你采取措施让自己感觉更好。”
一些科学家认为,催产素与身体的天然阿片类物质协同作用,催产素触发对社会依恋的驱动力,而阿片类物质则提供与亲人在一起时的温暖、模糊的感觉。“催产素的故事如火如荼,它无疑是一个大热门,”俄亥俄州鲍灵格林州立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雅克·潘克塞普说,他的实验室从1970年代开始研究阿片类物质和社会依恋。“但不幸的是,催产素的人们忘记了早期的阿片类物质故事。”
潘克塞普认为,催产素的作用之一是降低在药物成瘾中扮演毁灭性角色的耐受效应。正如吸毒者对海洛因产生耐受性,导致他们服用越来越大的剂量一样,大脑对天然阿片类物质也会产生相同的耐受性。在动物实验中,催产素注射显著降低了对阿片类物质的耐受性。换句话说,催产素可能不会创造爱和依恋的强烈快感,但它确实能让这种快感持续更长时间。
所有这些都表明,“爱上瘾”这个词可能不仅仅是诗意的表达。海洛因等毒品之所以造成伤害,是因为它们直接作用于调节爱情纽带的大脑化学物质。当人们对毒品上瘾时,亲密朋友最常见的反应之一就是对吸毒者背弃亲情友谊的能力感到困惑。不亲自体验成瘾的巨大力量,我们觉得有人为了针尖的刺激而牺牲孩子的爱是多么可怕。但是那根针里装的正是帮助让孩子的爱变得有吸引力的毒品。我们凭直觉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为了孩子牺牲生命。当吸毒者做出类似的牺牲时,这似乎是彻头彻尾的反人类。然而,从神经化学角度来看,这些牺牲都摆在同一个祭坛上。
阿片类物质和催产素之间的联系强调了泰勒关于“爱情药”还原论的观点。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充满了爱情魔药的故事,但这个故事远比那复杂得多。存在一个生物学基础的大脑系统,它创造并维持我们称之为“爱”的感觉,但其原因不能简化为单个分子。催产素和阿片类物质之间存在不可否认的相互作用,草原田鼠的大脑解剖结构表明多巴胺和催产素之间存在强烈的联系。更重要的是,雌激素会增强催产素的作用,而睾酮等雄激素会减弱催产素的作用,这可能有助于解释男性和女性应激反应之间的差异。爱可能不像民间智慧所说的那样存在于心脏中,但它也不存在于单个分子中。当我们感受到浪漫爱情或亲子依恋的萌动时,我们感知到的是大脑化学物质复杂的相互作用,触发大脑特定区域的活动。催产素对这种相互作用至关重要,但它并非全部。
田鼠为什么会坠入爱河? 人类大脑的复杂性——以及对人类进行实验的伦理问题——可能意味着对依恋的科学理解不会进展迅速。当我问泰勒她最希望在这个领域看到什么突破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希望有一个人类等同于草原田鼠的模型,”她若有所思地说,“草原田鼠模型是一个非常棒的模型。”
虽然我们对人类神经化学的了解是有限的,但这种化学物质在其他哺乳动物中重复出现的程度表明,爱是我们进化遗产的一部分,就像心跳调节或立体视觉一样。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物种,进化出不同的交配和育儿习惯——像大多数爬行动物一样,出生后就抛弃孩子,随意更换伴侣——那么我们的大脑可能无法感受爱。
爬行动物缺乏我们的大脑新皮层,即语言和高级学习的所在地,并且拥有一个非常原始的边缘系统,即大脑中在调节情绪反应中起关键作用的部分。爬行动物的大脑只产生非常初步版本的催产素分子。如果进化的某种意外导致爬行动物发展出新皮层,同时保持它们不存在的育儿习惯,它们最终可能会写出关于其他根深蒂固的生化冲动(比如体温调节)的强有力诗歌,但在爬行动物经典中不会有爱情十四行诗。
爱的生物学能力是大脑为我们做好准备的方式之一,以应对那些出生时幼小无助、需要照料才能有一丝生存希望的后代。这种照料以社会纽带的形式出现——在父母与孩子之间,在父母之间,以及在帮助抚养孩子的 extended social family 成员之间。维持这些纽带牢固的粘合剂是我们的大脑在进入爱的关系时为我们调配的快乐、奖励和满足感。
想到这种粘合剂的核心成分为人类和草原田鼠所共有,可能会令人感到不安。因为爱是人类许多最高创造性成就的源泉,我们喜欢认为这种情感本身同样独特。但是大脑化学的共同性——以及行为的共同性——表明,至少有一部分爱的陶醉感是被其他哺乳动物所体验的。“我认为理智的人必须对非常相似的基本情感存在的可能性敞开心扉,”潘克塞普说。“其他哺乳动物不能像我们一样用情感创作电影、艺术或其他伟大的事物。但否认基础元素的连续性对我们来说是愚蠢的。”
当被问及草原田鼠的爱与人类体验的主观体验可能有什么不同时,潘克塞普无言以对。“我认为这个问题无法回答,”他说,然后开始组织答案。“我们对草原田鼠依恋和爱的化学机制的了解远多于对人类化学机制的了解。我的意思是,动物研究在底层细节方面产生了如此丰富的成果。我们对自己物种的了解还不够多。但我们从人类和动物基因组项目中了解到的关于神经化学和神经解剖学保守性的所有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当我们研究这些小动物时,我们也在了解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