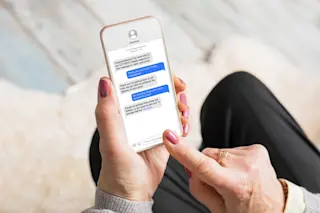珍妮弗·H是一位专业音乐家,23岁时因性亲密问题寻求帮助。在治疗期间,她还开始探索自幼困扰她日常的莫名的恐慌感。她说,渐渐地,她追溯了恐惧感的根源,回想起了离家后一直压抑的记忆。她记得父亲从她4岁时就开始猥亵她,然后强奸她,直到17岁她搬出去为止。她回忆说,父亲曾掐住她的喉咙,威胁说如果她告诉任何人就杀了她。随着这些记忆的浮现,她的恐慌发作和其他症状消退了。但是当她质问她的父亲——一位在著名东北大学工作的机械工程师时,他断然否认虐待过她。
其他家庭成员记得詹妮弗的父亲抓过她的胸部。詹妮弗自己也有一个从未忘记的记忆:父亲盯着她的胸部,说些粗俗的性评论。詹妮弗担心她的父亲会虐待其他孩子,除非他承认自己的问题,于是她求助于法院,希望通过诉讼促使父亲接受治疗。提起刑事指控的诉讼时效已过,但在1988年,詹妮弗对她的父亲提起了人身伤害诉讼。除了她自己的证词,法院还听取了她的母亲(当时已离婚)的证词,她作证说曾看到詹妮弗的父亲躺在詹妮弗14岁的妹妹身上;她还说他在保姆十几岁时曾猥亵过她。詹妮弗的父亲的妹妹回忆说他曾对年轻女孩进行性挑逗。1993年,马萨诸塞州的一个陪审团判决他向詹妮弗支付50万美元的损害赔偿。(民事陪审团不能作为判决的一部分命令人们接受治疗。)尽管詹妮弗的父亲承认猥亵了保姆,但他至今仍坚称他从未虐待过他的女儿。
珍妮弗·H的案例是最近几起围绕“恢复记忆”——即在一段时间的压抑后重现的性虐待记忆——展开激烈争议的核心案例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小时候曾遭受猥亵的成年人才开始向法院提出诉求,公开与施虐者对峙,希望迫使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但随着案件数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家长、研究人员和学者开始公开谈论虚假指控的危险。他们特别质疑:创伤性童年记忆是否可能被压抑然后恢复?他们还认为,有些人可能在治疗师或自助书籍的煽动下,编造了从未发生过的事件记忆。到目前为止,辩论双方都依赖心理学而非生物学的见解来论证记忆如何运作。
生物学能否就记忆是否以及如何被压抑和恢复提供任何线索?也许可以——但要充分理解这场辩论,我们首先需要将其置于其社会学背景中。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儿童性虐待基本上被忽视;他们的故事受到怀疑和淡化,或者他们被指责鼓励了猥亵行为。但过去15年左右的研究表明,儿童猥亵远非罕见。根据受访者和虐待定义的差异,研究发现8%到38%的女性表示她们在儿童时期曾受虐待,而男性的数据范围从3%到16%。(38%的数据来自1978年对旧金山930名女性进行的一项随机调查,该调查将虐待定义为18岁前与亲属发生的任何不想要的性活动;14岁以下儿童被非亲属猥亵、强奸或试图强奸;以及14至17岁儿童被非亲属试图或完成的强行强奸——这些描述与刑法中儿童猥亵的定义一致。)
许多在儿童时期曾受虐的成年人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但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家朱迪思·赫尔曼及其他人的研究也表明,暂时压抑这些记忆可能并非罕见。1987年,赫尔曼发现,在53名参加乱伦幸存者团体的女性中,近三分之二的人报告在虐待发生后的某个时间点出现部分或完全的记忆缺失。这些发现后来得到了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家约翰·布里埃领导的一项针对男性和女性的更大规模调查的响应。虐待发生得越早,越是暴力或持续,受害者长期 блоки记忆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发现与旧金山加州大学精神病学家莉诺尔·特尔的临床研究相吻合,她发现经历重复创伤的儿童比经历一次性创伤事件的儿童更容易压抑记忆。
新罕布什尔大学社会学家琳达·迈耶·威廉姆斯最近开展了一项最系统的记忆压抑追踪工作。威廉姆斯采访了129名女性,她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年幼时曾因性虐待接受治疗。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对医疗记录中记载的猥亵行为没有记忆,或者选择不报告。由于这些女性中超过一半讨论了其他性虐待事件,因此选择性失忆是她们反应(或缺乏反应)的更可能解释,而不是不愿意讨论性。
大多数临床心理学家认为,儿童可以学会阻止记忆作为一种生存机制:如果身体上无法逃脱折磨者,那么心理上的逃脱可能变得至关重要。当儿童无法避免虐待并知道虐待会重复发生时,一些人会通过心不在焉——在虐待发生时精神上与虐待分离——或者事后压抑记忆来应对。
但是,根据这一学派的观点,压抑在成年生活中可能不再有益。离开了创伤环境,成年人可能会发现他们的记忆重新浮现,可能是碎片状的逐渐浮现,也可能是突然生动的闪回。正如詹妮弗·H的案例一样,这些记忆可能在治疗期间重现,但这绝非总是如此。弗兰克·菲茨帕特里克38岁,已婚,在罗德岛州担任保险理算员,工作稳定,他自发地回忆起26年前被詹姆斯·波特神父猥亵的经历。自1990年被菲茨帕特里克质问以来,这位罗马天主教神父已经承认猥亵了数十名男孩和女孩。当新闻曝光后,68名男女表示他们也曾被波特神父侵犯。至少有六人直到新闻报道触发了他们童年记忆的回归后才回忆起虐待。
但是,被指控虐待的人通常不会坦白——而且他们的指控者的故事也不容易得到证实。这就使得记忆成为许多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基础,并使得确定人们记忆的准确性至关重要。由于儿童猥亵如此令人憎恶,仅仅是怀疑的污点就可能毁掉人生。被指控者面临失去家庭、事业和声誉的风险;如果提起刑事指控,他们将面临高昂的法律费用和潜在的牢狱之灾。根据“虚假记忆综合症基金会”的数据,目前有超过9500个美国家庭声称他们的成年子女用从未发生过的虐待行为玷污了他们。(该基金会由帕梅拉和彼得·弗雷德于1992年成立,此前他们的女儿詹妮弗,现在是俄勒冈大学心理学教授,指控她的父亲虐待她——这一指控他们极力否认。)这些家庭中的许多人将他们的孩子的“虚假记忆”归咎于狂热的治疗师和流行的自助书籍。
一些研究人员——其中包括华盛顿大学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图斯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家理查德·奥夫谢——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对被压抑记忆的可信度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关于儿童虐待的宣传营造了一种氛围,让人很容易相信许多人不明症状的痛苦是隐藏虐待造成的。
洛夫特斯和奥夫舍认为,有些治疗师有意或无意地将想法植入易受影响的病人心中。他们指出,虚构的记忆可以通过催眠——甚至无需催眠——植入。洛夫特斯引用了一项研究,其中五个人被一位年长的亲戚告知了一个虚假的故事,关于他们小时候如何在商场或公寓大楼里迷路。当后来被要求回忆更多细节时,他们讲述了虚构事件的详细记忆。植入一个像被家人反复强奸那样创伤的事件是否也同样容易?承认虚假记忆可能确实存在强大的负面激励。尽管如此,曝光的案例仍然如此之少,这仍然令人惊讶。
作为记忆可塑性的进一步证据,洛夫特斯和奥夫谢引用了轰动一时的保罗·英格拉姆案。这位华盛顿州副警长被他的两个女儿指控作为撒旦教派成员性虐待她们。作为一名基要派基督徒,英格拉姆否认了这一指控。然而,在监狱里,他被警方和一名牧师反复审问涉嫌事件,并被一位心理学家要求将它们形象化——直到他最终想出了关于这些事件的淫秽记忆。奥夫谢最初是由检方而非辩方聘请来采访英格拉姆的。为了测试英格拉姆的易受暗示性,奥夫谢询问他一个完全虚构的场景:英格拉姆强迫他的儿子和女儿发生性关系。起初英格拉姆什么也回忆不起来。然后奥夫谢鼓励英格拉姆想象那个场景,并像英格拉姆以前做的那样“祈祷那个画面”。英格拉姆随后对虚构的场景产生了详细的记忆,从而使他之前的所有供词都受到质疑。
英格拉姆案表明,某些条件可能会促成完全虚假记忆的产生:制度化或宗教压力。在十名“翻供者”的案例中,一名女性在一家私立医院的隔离病房中获得了她的虐待记忆。另一名则在一个基督教组织运营的项目中住院。另外两名翻供者指控他们的治疗师使用了强效精神药物,这些药物,与催眠一样,可以增加对暗示的易感性。虚假记忆的发生和一些人被不公正地指控是不可否认的,但奥夫谢和其他怀疑论者抓住这些案例来质疑所有被压抑的记忆。在1993年发表于《社会》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奥夫谢总结道:“只有治疗前的个人历史叙述才能被视为具有普通错误成分的正常记忆。”在他看来,记忆压抑只不过是“未经证实的猜测”。
那么,生物学能为这场艰难的辩论做出什么贡献呢?在过去的20年里,神经科学家在理解记忆运作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科学能否解释性创伤的延迟回忆呢?严格的答案是否定的。目前,对于记忆被压抑或恢复时人类大脑中可能发生什么,还没有一个适当的理解。然而,生物学可以提供关于记忆如何储存、储存如何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是否与压抑和记忆后期恢复兼容的见解。
解释记忆如何形成的细胞机制是什么?据我们所知,将我们的经历储存为记忆涉及改变大脑中神经细胞之间连接(称为突触)的强度。在初始阶段,持续几分钟,通常称为短期记忆,这种变化是暂时的;它不会改变连接的结构。然而,一小时或更长时间后,解剖学上的变化开始将记忆转化为更持久的形式。这个巩固期涉及神经细胞之间新连接的生长,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现有连接的回缩。
我们还知道,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都至少包含两种不同的形式: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内隐记忆处理我们对运动或知觉技能的无意识知识,即“知道如何做”。外显记忆处理我们对事实、人物和地点的知识,即“知道什么”。储存这两种形式涉及大脑中截然不同的系统。外显记忆由颞叶(我们耳朵后面发现的脑叶)的内部部分和下方的海马体区域处理。相比之下,内隐记忆涉及大脑中独特的运动或感觉通路,自主神经系统(调节呼吸和心率等非自主活动),以及两个额外的大脑结构,杏仁核和小脑。
关于颞叶和海马体在外显记忆中发挥作用的最初证据,来自20世纪50年代对癫痫患者的研究。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的神经心理学家布伦达·米尔纳描述了现在著名的H.M.病例,一位27岁的流水线工人,患有无法控制的颞叶癫痫。为了缓解他的癫痫发作,一位外科医生切除了他颞叶的一部分,包括海马体。这项手术使H.M.留下了毁灭性的记忆缺陷:他再也无法形成新的长期记忆。然而,H.M.仍然拥有他以前获得的长期记忆。他清楚地记得手术前发生的事情,比如他的工作和童年经历。从H.M.和像他这样的患者的研究中,很明显海马体只是长期记忆的临时储存库。海马体将新学习的信息处理几周到几个月,然后将信息传输到大脑皮层进行更永久的存储。因此,尽管H.M.仍然拥有完全完好的短期记忆,但他无法将他所学到的知识转化为长期记忆。他每次见到米尔纳都能正常交谈,但他每次见面都记不住她。
起初,人们认为这种毁灭性的缺陷适用于所有形式的新学习。但米尔纳和其他人很快有了一个奇妙的发现,彻底改变了对记忆的思考。颞叶受损的患者可以完成某些涉及知觉和运动技能的内隐学习任务——而且他们能很好地保持这些任务的记忆。例如,H.M.可以学习新的运动技能,如镜像绘画(看着镜子中的手而不是纸张来绘画)。通常,外显和内隐记忆系统之间存在交叉对话,因此当你学习或体验新事物时,两个系统都会发挥作用。事实上,某些类型的外显记忆可以通过不断重复转化为内隐记忆。学习打网球反手最初需要有意识的思考,但通过练习,打出好的底线球几乎会变成条件反射。你不会有意识地回忆该怎么做——你只是知道打反手是什么感觉。
这种交叉对话在情绪激动的经历(如性虐待)的记忆中尤为明显,其中与事件相关的情绪以及对事件的有意识回忆存储在不同的系统中。我们对“情绪记忆”的大部分了解来自纽约大学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克斯和耶鲁大学迈克尔·戴维斯所做的工作。这些研究表明,高度情绪化的记忆的有意识成分最初存储在海马体中。但无意识的内隐成分可能通过杏仁核存储,杏仁核将大脑的感觉和运动区域与自主神经系统连接起来。在非常紧张事件的记忆中,内隐记忆的作用可能特别强大。
当然,像所有记忆一样,高度情绪化的记忆需要一段时间的巩固才能成为长期记忆。但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米歇拉·加拉格尔以及其他研究这一过程的人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长期记忆的强度可能会受到所记忆事件发生的背景影响。有些因素会增强记忆的巩固、储存和回忆;另一些则会抑制它们。
通过对大鼠的研究,加拉格尔发现,当去甲肾上腺素——一种与警觉和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在杏仁核中释放时,恐惧经历的内隐记忆会得到强化。相反,内源性阿片类物质(一种天然的鸦片样物质)的释放会削弱记忆储存。其他研究人员此后发现,恐惧的外显方面也可以类似地调节。这一发现提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可能性。如果某个事件令人如此痛苦以至于大脑制造阿片类物质来麻痹疼痛,那么这些阿片类物质可能会干扰记忆储存过程。有趣的是,加拉格尔发现,在巩固期使用一种名为纳洛酮的药物来阻断内源性阿片类物质,确实能增强大鼠的记忆回忆。此外,一些研究表明,通过注射肾上腺素等兴奋剂可以增强弱储存的记忆。
这些研究为我们思考创伤记忆在人类中如何被抑制提供了生物学背景,但它们的提取又是如何呢?我们只能推测这可能如何运作。
假设记忆在显性系统中储存得很弱,因为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干扰了它的巩固——弱到个体对最初的痛苦事件没有意识记忆。然而,同一个事件也可能通过隐性系统以特有的身体感觉或姿态被捕获。也许后来隐性系统会提供线索——比如身体感觉——帮助激发对微弱显性记忆的召回。
事实上,那些声称童年曾受虐待的人,常常描述他们的记忆最初是以身体感觉的形式回归:珍妮弗·H在做缓解颈部紧张的运动时,回忆起她的父亲扼杀了她。莉诺尔·特尔说,有时受害者会表现出反映创伤事件的行为线索。特尔引用了艾琳·富兰克林的案例,她说她看到她的父亲强奸了她最好的朋友,并用石头砸碎了那个女孩的头。富兰克林的父亲也虐待富兰克林,当时她8岁。从8岁到14岁,富兰克林拔掉头皮特定部位的头发,直到流血,再现了她看到朋友受到的伤口。富兰克林压抑了这段记忆,直到她20多岁时,它的重新浮现导致了她父亲的定罪。
事实上,一些虐待幸存者将他们恢复的记忆描述为与D其他记忆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他们感觉自己实际上正在重新经历事件,包括所有的质感、气味和身体感受。这与退伍军人经历的闪回的强度相似。正如我们所见,加拉格尔发现通过刺激杏仁核中的去甲肾上腺素可以强化内隐记忆。耶鲁大学的研究表明,因压力而释放的去甲肾上腺素有助于越南退伍军人强大的闪回。也许性虐待幸存者通常无法接触到的记忆在他们的去甲肾上腺素系统被激活时才得以检索。
所有这些都表明,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和去甲肾上腺素在杏仁核和海马体中的作用可以开始为考察记忆如何被压抑和随后检索提供一个生物学框架。很快就可能直接检验这些想法。动物研究已经表明,长期记忆的特征,无论是内隐的还是外显的,都是解剖学变化——大脑中神经细胞之间连接的生长或收缩。脑部成像技术(如磁共振成像)的改进最终可能使我们能够以安全、非侵入性的方式检查人脑中的微小结构。我们那时可能能够看到性虐待是否导致杏仁核的物理变化,以反映一个人对事件的记忆——以及这些变化是否可以被去甲肾上腺素和阿片类系统调节。
事实上,现有的成像技术——PET扫描——已经让我们得以一窥为什么虚假记忆对于经历它们的人来说似乎完全真实。哈佛大学的史蒂芬·科斯林发现,大脑中参与感知图像并将其存储为记忆的区域,也参与想象该图像。例如,当你思考你昨天遇到的人的脸时,内侧颞叶区域——也就是最初用来感知那张脸的区域——会变得活跃。因此,想象的事件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感知到的事件,因为两者都使用相同的大脑结构。事实上,在许多方面,记忆就像感知。两者都是大脑中重构的事件,是创造性的阐述,涉及围绕一些坚实的视觉地标填充细节。正如感知的微小细节容易出现错觉一样,记忆的细节也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
因此,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有理由相信压抑记忆辩论的双方都可能有效。动物研究表明记忆储存可以被调节和抑制,一旦被抑制,记忆仍然可以恢复。同时,我们也知道记忆可能不可靠,并且我们对幻想可能被误认为是现实有所了解。那么,目前如何评估任何个别案例的数据呢?答案很明确:理想情况下,人们希望看到独立的证据来证实所谓的受害者的报告——例如,来自家庭成员、日记、照片、医疗和警方记录。但实际上,考虑到儿童虐待的私密性以及对儿童的威胁以防止他们告诉他人,独立的证据往往不可获得。(在缺乏独立佐证的情况下,特别引人注目的行为线索,例如艾琳·富兰克林所表现出的,有时可能有助于支持一个案例。)
所以争论还在继续。但目前这场辩论的论调令人不安的是,一些媒体和学术评论家急于利用怀疑的楔子公开诋毁延迟记忆的存在。批评者的问题是否反映了真正探求真相、捍卫无辜被冤枉者的努力?或者我们有时是否正在目睹一场对将儿童虐待从家庭隐秘中公之于众的斗争的反弹?在去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赫尔曼指出:“直到最近,儿童性虐待还是一项完美的犯罪。施虐者几乎可以保证永远不会被抓住或成功起诉。现在,女性——和男性——已经开始利用法庭首次追究他们的责任,我们看到施虐者正在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