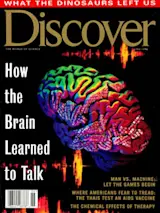早上 7 点,我抵达医院。黎明柔和的蓝色被急诊室全天候闪烁的荧光灯光所吞没。夜班主治医生 Reuben 睡眼惺忪地笑了笑。
“怎么样?”我问道。
“哦,一如往常。没有什么需要交代。”
轮到我感激了。但现在又有一个紧急情况:咖啡。我正要回到医生办公室,外面传来一阵微弱的呜咽声。救护车正在倒车。我猛灌了一口咖啡,走了出去。救护车停靠门嘶嘶地打开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别管我!哎哟……哦。该死的!别管我!”
“是出血,”我想,尽管药物过量或许是更可能的选择。我当时在一个为东北部一个小城市服务的急诊室工作。随着大西洋鱼类储量的枯竭,这座城市的经济崩溃了,毒品滥用和精神疾病普遍存在。但在医学上,最大的错误是在判定病人“疯了”之前先判定他们“生病了”。没有什么能比大脑突然出血更快地让人产生幻觉了。
四名壮实的急救人员按住了那个女孩。护士长 Ann 和我一起冲向担架。最近的急救员给我们做了介绍。
“弗吉尼亚·卡尔森,22 岁,凌晨 4 点出现剧烈头痛。呕吐了两次。然后,她父母说,她就这样了。已经感冒几天了。”
“不!走开!”女孩吼道。“哎哟……哎哟。我恨死你们了!”
急救人员紧紧抓住她,以便我们能用软约束带绑住她的手腕和脚踝。脑出血仍然有可能,但她父母描述的流感样症状表明了另一种可能:脑膜炎,即包裹大脑和脊髓的膜发炎,通常由细菌感染引起。当 Ann、另外两名护士、四名急救员和我们 250 磅重的护士助理 Bob 将弗吉尼亚制服并绑好时,我找到了她父母。
卡尔森夫人令人惊讶地平静,考虑到她的女儿正被急诊室的医护人员控制着。卡尔森先生,一个瘦削、沉默寡言的男人,模仿他妻子的反应。
“医生,您认为她得了什么病?”卡尔森夫人问道。
“我不能确定,但我需要非常快速地问一些私人问题。”
“请说。”
“您女儿用过什么药或者喝酒吗?”
“不,从来没有,”她坚定地回答。“我知道她偶尔会抽大麻,但她是个可爱、负责、优秀的孩子。”
“药物?即使是非处方药?”
没有。
“她最近没有压力过大,她从来没有吃过药或试图伤害自己?”
没有。
“也没有青霉素过敏?她以前用过吗?”
“没有过敏,是的,她用过。”
就在这时,Ann 喊道:“直肠体温 101 华氏度(约 38.3 摄氏度)。”
“马上回来,”我说。担架旁的医护人员少了一些。在谵妄中,弗吉尼亚奋力挣扎着,想要逃脱她想象中束缚住她手脚的恶魔。
Ann 走了过来。
“你在想我和你想的一样吗?”她问道。
“脑膜炎——尽管仍然有出血的小概率,即使发烧,”我回答。“但她现在最需要的是青霉素——大量、快速地注射。四百万单位。四小时后重复。”
单剂 120 万单位的青霉素可以治愈链球菌性咽炎。弗吉尼亚每天需要 20 倍的剂量,直到感染清除。
“青霉素之后呢?”
“先做 CT 扫描,然后腰椎穿刺。”
“镇静?”
“大量。她必须静止不动做这两项检查。我们不能只是把她按住。”
在先治疗后诊断的过程中,我违背了医学教条,但脑膜炎需要一种“先开枪后问问题”的方法。
脑膜是保护大脑和脊髓的包裹层。脑膜有三层,从前脑延伸到脊髓,这就是为什么不存在纯粹的脊髓脑膜炎。最内层膜——网状的软脑膜——像保鲜膜一样紧贴大脑和脊髓表面。最外层膜是致密的硬脑膜。介于两者之间的是蛛网膜,一层宽松的膜,包裹着脑脊液,即 CSF。这个充满液体的腔室保护脆弱的大脑免受损伤性冲击,而脑膜炎致病细菌恰恰就在这温暖、富含葡萄糖和蛋白质的 CSF 中滋生。
对于急诊医生来说,很容易将脑膜炎误诊为药物引起的痴呆。幸运的是,通过进行腰椎穿刺可以确诊脑膜炎,即通过插入下背部的长针抽取一部分 CSF,然后进行细菌和对抗感染的白细胞检查。但在进行腰椎穿刺之前,医生必须排除大脑肿瘤或血管破裂的可能性。这两种情况都会引起痴呆——以及颅内危险的高压。当颅内压力急剧增加时,从脊髓腔抽出 CSF 会迫使大脑穿过枕骨大孔,即大脑与脊髓连接的颅骨开口。柔软的胶状脑组织会压碎在坚硬的骨头上。幸运的是,CT 扫描可以检测到肿瘤或脑出血,从而避免此类灾难。但 CT 扫描需要时间。而脑膜炎不会等待。
如果一个病人正在与脑膜炎这样的危及生命的感染作斗争,应该立即给予抗生素。不幸的是,医生们常常不愿在没有实验室结果证实感染的情况下使用如此强力的抗生素。因此,一些医生会等待细胞计数结果出来后再开始使用挽救生命的抗生素。此外,医生希望做出准确的诊断,如果他们在进行腰椎穿刺之前给予抗生素,实验室培养结果就会呈阴性。
解决办法是及时给予抗生素,然后使用检测细菌抗体的测试,而不是直接检测细菌本身。对于像弗吉尼亚这样的健康年轻女性,我知道只有两种主要的可能性,而这两种细菌,肺炎链球菌和脑膜炎球菌,都对青霉素敏感。
药物通过静脉滴入弗吉尼亚的输液管。弗吉尼亚入院已经过去了 50 分钟,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把她固定住并准备好接受治疗。
我祈祷延迟不会产生影响。
Ann 把弗吉尼亚的父母带了过来。卡尔森夫人开始抚摸她女儿的前额。
“医生,您看到她胸前那点淡淡的皮疹了吗?”她问道。“昨天她洗热水澡缓解肌肉酸痛时说,‘妈妈,你觉得这些红点是什么?’”
那一刻,我所有的警钟都响了。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我们还没有脱光弗吉尼亚的衣服并进行皮肤检查。Ann 拉开了被单。弗吉尼亚的胸部和腹部布满了小红点。比脑膜炎更致命的是脑膜炎球菌败血症,一种脑膜炎球菌通过血液传播的疾病。脑膜炎球菌败血症是传播速度最快的传染病杀手之一,并且以其独特的皮疹而闻名。它比最新的电视特效恐怖病毒还要快,可以在症状出现几个小时内夺走患者的生命。我突然非常、非常希望那 50 分钟不要浪费。
脑膜炎球菌,学名是脑膜炎奈瑟氏菌,并非一种罕见的进口微生物,能够出乎意料地袭击免疫系统。相反,这些细菌非常普遍,以至于我们许多人鼻腔和其他粘膜中都携带它们。幸运的是,抗体像巨柱仙人掌一样守卫在我们的粘膜上,通常能捕捉住任何入侵者。
但在极少数情况下,一种有毒株的脑膜炎奈瑟氏菌会设法压倒哨兵抗体,穿透我们呼吸道中的粘膜细胞。它们通过一种诡诈的生化机制,伪装成熟悉的细胞内物质,欺骗细胞将它们吞入膜状囊泡,并将它们运送到粘膜屏障下方的毛细血管。一旦进入血液,它们就会通过显示与红细胞相同的分子装饰来欺骗免疫系统。这样伪装后,它们就会穿过通常保护大脑免受感染的血脑屏障,并在没有防御的 CSF 中肆虐。其结果就是脑膜炎。在美国每年估计发生的 20,000 例细菌性脑膜炎病例中,约有 2,500 例是脑膜炎球菌感染。
在脑膜炎球菌败血症中,脑膜炎奈瑟氏菌在血液中大量繁殖,导致如此严重的感染,以至于免疫反应可能失控。在正常的免疫反应中,血管壁会变得更具渗透性,以便免疫细胞进入感染组织。但在严重的感染中,血管渗漏如此严重,以至于血压骤降。血液渗入皮肤和内脏器官,导致大面积出血。
当有严重的内出血时,皮肤上有时会出现斑驳的紫红色皮疹。幸运的是,弗吉尼亚的皮疹看起来不像那样。但卡尔森夫妇需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她得了脑膜炎,”我告诉他们。“也有可能感染已经通过她的血液传播了。”
“她会死吗?”卡尔森夫人问道,声音没有丝毫颤抖。
“是的。危险期将是接下来的 24 小时。她的血压现在稳定。如果今晚能保持这个水平,我们就进步很大了。”
“如果她活下来,她会有问题吗?脑损伤?”卡尔森夫人直视着我的眼睛。她想要真相。
“有这个可能,”我犹豫地回答。“是的。”
幸运的是,弗吉尼亚的 CT 扫描结果为阴性。大脑没有肿瘤或出血。在 Bob 的身体压住弗吉尼亚,Ann 将她抱成 C 形以暴露脊椎骨之间的间隙后,我进行了腰椎穿刺。我将针头插入两个脊椎骨之间,抽取了脑脊液。如我所料,它浑浊,但我检测到的压力增加了我的担忧。在正常患者中,脊髓腔内的压力不会迫使 CSF 在腰椎穿刺测压计上超过 180 毫米。在弗吉尼亚的情况下,压力超过了 550 毫米——仪器所能测量的最高值。
这种天文数字般的压力意味着弗吉尼亚正在与一场巨大的脑部感染作斗争。当身体对抗感染时,免疫细胞会聚集在感染部位,导致肿胀。弗吉尼亚的大脑肿胀得如此厉害,以至于需要神经外科医生来处理,而我们医院没有。
实验室打来电话。弗吉尼亚感染了脑膜炎球菌。与肺炎球菌不同,肺炎球菌往往只引起零星的脑膜炎病例,而有毒株的脑膜炎球菌可能在原本健康的年轻人中引起脑膜炎爆发。细菌通过密切接触或喷嚏、咳嗽传播;疫情往往在学校或军营等密切接触环境中出现。出于未知原因,有些人会遭受侵袭性感染,而另一些人则保持健康的携带者状态。
谁与弗吉尼亚有过密切接触?我列出了所有可能性:她的家人、将她制服的急救人员、急诊室工作人员,以及两天前在她家过夜的朋友。他们都需要接受为期两天的利福平治疗,这种药物可以杀死鼻腔和咽喉中的脑膜炎球菌,消除任何患病风险。然后是偶发接触者。由于他们的接触有限,他们不需要——但可以理解的是,他们会要求——接受抗生素治疗。
我们安排了弗吉尼亚转往附近医院。在她离开时,她已经昏迷——我希望这是我们给她镇静剂的效果。Ann 带了一袋青霉素在途中给她注射。
“弗吉尼亚的血压没有变化,”我告诉正准备陪同女儿的卡尔森夫妇。这是个好消息。弗吉尼亚来的时候,血压正常。如果保持稳定,感染可能没有通过她的血液传播。
第二天早上,Ann 带着一丝无奈的表情迎接我。
“他们刚把弗吉尼亚的弟弟送进急诊室。头痛和发冷。”
“哦,不,”我想。“我们给他用了利福平,对吧?”
“当然了,”Ann 回答。
“呼。这镇子疯了吗?”
“你觉得呢?”
“弗吉尼亚怎么样了?”
“她仍然没有反应。那家医院的医生听起来不太乐观。”
我心沉了下去。五十分钟。我们怎么会花了这么长时间?
不过,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那天下午,弗吉尼亚弟弟的诊断出来了:他的腰椎穿刺结果为阴性。只是流感。
两天后,情况似乎有所好转。
“弗吉尼亚今天早上醒了,”Ann 告诉我。“她会活下来。但脑损伤后遗症呢?脑损伤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显现。”
四周后,我打电话给弗吉尼亚的母亲。
“哦,弗吉尼亚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了,而且情况不错,戴杰医生。最糟糕的是头痛——这让她以为脑膜炎又回来了。这让她很害怕。”
我知道弗吉尼亚可能已经脱离危险了。她没有表现出任何脑损伤的迹象,细菌再次感染的可能性也很小。但我也知道弗吉尼亚的感受。脑膜炎是一个可怕的敌人,无论医生行动多快,它都可能更快。弗吉尼亚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