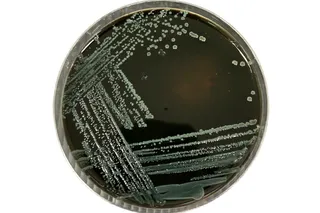几天前我评论了“回溯家庭”,嗯,泰晤士报(伦敦)有两篇文章,在我看来,这降低了它是骗局的可能性。显然,有一个高度近亲繁殖的家庭居住在土耳其,其中有几个孩子四肢着地行走并表现出其他形式的损伤。尽管如此,这里发生的具体细节对我来说很成问题。一如既往,报纸往往会把许多问题搞得一团糟。考虑这句话:“所有五个孩子都因 17p 基因突变而脑损伤,该基因位于第 17 条染色体上,该突变发生是因为父母是近亲:哈蒂斯的母亲的母亲是雷西特父亲的姐妹(这使他们有十六分之一的亲缘关系)。”这可能是语法错误,但突变并不是因为近亲关系而发生的。也就是说,高度近亲繁殖不会自发地增加突变率,相反,近亲婚姻往往会增加有害突变被暴露出来的机会。原理很简单。考虑一个有时会提出的说法,即每个人都有 3 个致死隐性基因。重点是,如果等位基因,即基因变异,携带两份(人类是二倍体,我们有两份所有基因),那么个体将是纯合的,就会产生负面的表型后果并降低适应度。例如,囊性纤维化是一种致死性隐性遗传病,如果是一种长效的(如今服用药物,CF 患者可以活到 30 多岁)。20 个西欧人中就有 1 个携带 CF 突变。在这些人中,几乎所有人都是杂合子,也就是说,他们携带一份“好副本”和一份“坏副本”。这些人不会表现出任何负面的表型结果,因为基因的良好副本足以正常运作。问题发生在携带该基因的两个个体结合时,子女有 25% 的几率会同时接收到两个坏副本,从而暴露出负面的表型后果。如果人群中有 20 个人中有 1 个是杂合子,那么携带者配对的随机交配几率为 1/400,任何后代表现出 CF 的几率为 1/4。因此,考虑一种情况,其中一个父母是 CF 携带者。该个体与纯合“野生型”个体(无坏副本)的子女有 1/2 的几率成为携带者。现在,想象一下这些子女互相交配。每个子女成为 CF 携带者的几率为 1/2,所以有 1/4 的几率两个携带者会配对,后代表现出负面表型后果的几率为 1/4。将独立概率相乘意味着,如果一个携带者的子女乱伦交配,孙辈表现出 CF 的期望值为 1/8。与那些子女不乱伦交配的人相比,每个子女成为携带者的几率为 1/2,而他们成为另一个携带者的几率为 1/20,所以双携带者配对的几率为 1/40。1/4 的子女将表现出表型,所以这个个体孙辈患 CF 的几率为 1/160。换句话说,**对于一个杂合个体而言,近亲交配与非近亲交配导致 CF 孙辈的概率差异是 20 倍**。这是一个极端情况,但多代温和的乱伦可能会有问题,换句话说,我怀疑相关系数是否仅仅是 1/16。同样,不幸的是,返祖现象的说法被强调了。这是好写法,但我们应该对此持怀疑态度。这是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很可能的。似乎 17p 突变是**功能丧失**,具有广泛的多效性影响。我怀疑祖先基因从无效功能转变为新功能。正如卡尔·齐默尔(Carl Zimmer)指出的那样,双足行走是一种复杂而特殊的特征,它导致了我们形态和生理的许多其他方面的改造。尽管它可能不是以经典的渐进方式出现的,但它不太可能是由单一的积极突变引起的,然后修饰基因在几百代中进化。所以,如果导致这种非双足行走的基因在序列水平上与我们古代非人祖先的特征性质不同,我们究竟能从这个家庭中学到关于双足进化什么呢?我不知道。最后,问题在于,这个家庭中携带 17p 突变的一个孩子似乎并没有表现出他同胞的异常特征。文章中引述的首席科学家认为,这是**自然与后天**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在给定初始基因型的情况下,特定的环境背景增加了这种表型表达的可能性。在技术文献中,这可能被称为不完全外显率。但是,我想聚焦在结论上,质疑 Humphrey 对此想了多深,或者如果《泰晤士报》将他脱离语境,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它。
Humphrey 教授说,多种因素的结合——遗传缺陷、庞大的家庭、有限的父母关注、同胞模仿、骨骼异常、外部世界的干预缺失——导致了这种非凡的结果。“如果其中每一项因素发生的几率只有千分之一,那么这些因素加起来,在同一个家庭中发生的几率将是十亿分之一。我们从未见过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我们可能再也不会看到了。”
在第一段中列举了大量的变量,而在第二段中,Humphrey 似乎在暗示这些变量是独立的,每个后代都是一个独立的试验,可以单独看待。我看不到这是如何运作的,似乎上述许多变量应该彼此之间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和相互作用。我在上面已经展示了遗传缺陷在同一个家庭中表现出来的几率如何大大增加。这个家庭也可能为其后代提供类似的环境输入,即使存在差异。我可能很困惑,因为我看不到 Humphrey 在第二段关于概率的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最后,后天与自然共同作用可能是正确的,但对于不完全外显率,另一种解释是,性状通常是多基因的,其复杂性是我们不理解的,因为存在一个上位性、基因间相互作用的参数。换句话说,“正常”的儿子可能携带另一个基因座上的基因,该基因掩盖了非双足表型。**简而言之,我确信这不是骗局,而且可能在医学上很有趣。但我也对这个说法是否能告诉我们在广泛的进化遗传学和古人类学尺度上有什么东西持怀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