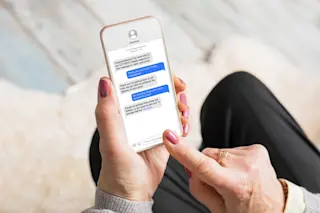罗伯特·普罗文想让我看看他的“挠痒痒艾摩”娃娃。实际上,他想让我拿着它。对于普罗文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不寻常的要求。作为马里兰大学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教授,他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广泛的智力探索,从年轻黑猩猩的喘息嬉戏到美国情景喜剧的历史——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科学地理解人类最不科学的习俗:笑声。这个艾摩娃娃恰好融合了他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挠痒痒和传染性笑声。“你玩过这种东西吗?”普罗文说着,从一个小帆布手提袋里拿出娃娃。他举起它,一两秒钟后,娃娃开始尖叫着大笑。这个场景无疑有些滑稽:一个身材魁梧、留着胡子、五十多岁的人抱着一个红色的布偶。普罗文把艾摩递给我,以展示娃娃的震动效果。“它引出了两个有趣的问题,”当艾摩在我怀里时,他解释道。“你有一个畅销玩具,它就是一个被美化了的‘笑盒’。当它摇晃时,你会得到反馈,就像你在挠痒痒一样。”普罗文与笑声的关系让我想起了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所说的“疏离效应”的戏剧技巧。在布莱希特的愿景中,激进戏剧旨在让我们疏离那些过于熟悉的社会结构,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审视这些结构。在他对笑声的研究中,普罗文一直在做着同样富有启发性的事情,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最熟悉的情感状态之一的奇特之处。想想那个“挠痒痒艾摩”娃娃: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挠痒痒会引起笑声,并且一个人的笑声会轻易地“感染”听力范围内的其他人。即使是孩子也知道这些。(挠痒痒和传染性笑声是童年的两个显著特征。)但是当你从远处思考它们时,它们是奇怪的习俗。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自然选择会在我们体内植入“战或逃”反应,或者赋予我们性冲动。但是,在他人面前发笑或被羽毛挠肚子时发笑的倾向——这有什么进化优势呢?然而,快速浏览一下尼尔森收视率或征友广告就会告诉你,笑声是我们最令人满意和最受追捧的状态之一。有趣的是,普罗文越接近理解我们为什么发笑,他就越远离幽默。要欣赏笑声的根源,你必须停止思考笑话。
捧腹大笑的解剖
笑可能感觉很好,但从生理上讲,它最初是一种身体压力源,与恐惧引起的战或逃反应非常相似。当大脑更高级的区域检测到挠痒痒的感觉或理解一个笑话时,脑干和边缘系统会协调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的突然激增,提高心率、血压和新陈代谢,同时启动一种接近过度换气的呼吸反应。好处随后而来。一些研究表明,笑声的后遗症会增强免疫活性,但支持数据稀少。神经胚胎学家罗伯特·普罗文说,真正的回报可能更多地与笑声有助于强化的社会纽带有关:“我们知道社会支持在从健康老龄化到心血管疾病的一切方面都发挥着作用。因此,至少在这方面,好心情等于好健康。”——乔斯林·塞利姆 对幽默本质的学术研究有着悠久而半辉煌的历史,从弗洛伊德的《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这可能是关于幽默的最不好笑的书)到去年宣布确定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的英国研究小组。尽管研究人员表示他们为了这一发现对大量国际受众进行了抽样调查,但获胜的笑话围绕着新泽西居民:两个新泽西猎人在树林里,其中一个倒在了地上。他似乎没有呼吸;他的眼睛翻白了。另一个人掏出手机,拨打紧急服务电话。他气喘吁吁地对接线员说:“我朋友死了!我能做什么?”接线员说:“别急。我能帮忙。首先,我们得确定他死了。”一片寂静,然后传来一声枪响。那个人的声音回到电话里。他说:“好的,现在怎么办?”这个笑话说明,对幽默潜在结构的大多数评估都倾向于“受控不协调”的概念:你期望X,但你得到Y。要让笑话奏效,它必须在两个层面都可理解。在狩猎笑话中,对911接线员的指示有两种合理的解释方式——要么猎人检查他朋友的脉搏,要么他开枪射杀他。上下文让你期望他会检查他朋友的脉搏,因此,当他选择更不可能的路径时,幽默( admittedly dark)就出现了。当然,这种不协调是有限制的:如果猎人选择做一些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解开鞋带或爬树——那么这个笑话就不会好笑。近年来,一些研究在受试者因好笑话而发笑时观察了大脑活动——试图定位神经学的“笑穴”。有证据表明,额叶与“理解”笑话有关,而与运动控制相关的大脑区域则执行笑的身体反应。1999年的一项研究分析了右额叶受损的患者,右额叶是大脑的一个整合区域,情感、逻辑和感知数据在此汇聚。与对照组受试者相比,脑损伤患者在选择一系列笑话的正确结局方面困难得多,他们通常选择荒谬、闹剧式的结局,而不是传统的结局。幽默通常以粗俗、最低公分母的形式出现,但真正理解笑话需要我们更高的大脑功能。当普罗文开始研究笑声时,他想象他会按照这些幽默研究的思路来解决问题:研究笑声意味着让人们听笑话和其他妙语,并观察发生了什么。他首先简单地观察日常对话,计算人们在听人说话时发笑的次数。但他很快意识到他对笑声运作方式的假设存在根本性缺陷。“我开始录下所有这些对话,”普罗文说,“我得到的数字——我看到它们时都不相信。说话者比听众笑得更多。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我都会想,‘好吧,我必须回去重新开始,因为这不可能对。’”结果发现,说话者比听众发笑的可能性高46%——而且他们发笑的内容,通常情况下,根本不好笑。普罗文和他的大学生团队记录了在日常对话中引发笑声的“妙语”。他们发现,只有大约15%的句子是传统意义上的幽默。在他的书《笑声:一项科学调查》中,普罗文列出了一些引起笑声的引语:我晚点见你们。/把那些香烟收起来。/我希望我们都做得好。/见到你也很高兴。/我们能搞定这个。/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应该那样做,但我太懒了。/我努力过正常生活。/我想我完了。/我早告诉过你!迄今为止,关于笑声的少数研究都假设笑声和幽默是密不可分的,但普罗文的早期研究表明,这种联系只是偶尔的。“笑声有一个我们太容易忽视的阴暗面,”他说。“科伦拜恩事件中的孩子们在学校里射杀同学时还在笑。”随着他的研究进展,普罗文开始怀疑笑声实际上是关于其他事情——不是幽默或玩笑或不协调,而是我们的社交互动。他在一项已经进行的研究中找到了支持这一假设的证据,该研究分析了人们在社交和独处环境中的笑声模式。“当你和别人在一起时,你发笑的可能性是独自一人时的30倍——如果你不计算电视上的笑声轨道等模拟社交环境的话,”普罗文说。“事实上,当你独自一人时,你大声自言自语的可能性比大声发笑的可能性大得多。大得多。”想想你很少会对着书中有趣的段落大声发笑,但遇到一位老熟人时你却会很快发出友善的笑声。笑不是对幽默的本能身体反应,就像因疼痛而颤抖或因寒冷而发抖一样。它是一种本能的社会联系形式,而幽默就是为了利用这种联系而设计的。
普罗文位于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的实验室,看起来像一个音响维修店的后屋——长桌上堆满了旧设备,到处都是管子和电线。墙上挂满了色彩鲜艳的缠结神经元图片,其中大部分是普罗文画的。(加上一些荧光字体,它们可能被认为是菲尔莫尔剧院“死之舞”演出的宣传海报。)普罗文的老导师,神经胚胎学家维克托·汉堡格,从一张挂在破旧的Silicon Graphics工作站上方的照片中俯视着,面露担忧和困惑:“我把你训练成一个科学家,而你却在这里玩娃娃!”普罗文工作中更具技术性的部分——探索笑声的神经肌肉控制及其与人类和黑猩猩呼吸系统的关系——借鉴了他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接受汉堡格和诺贝尔奖得主丽塔·列维-蒙塔尔奇尼指导的训练。但要最直接地理解他对笑声进化的见解,是观看他非正式田野调查的视频片段,其中普罗文和一名摄像师在巴尔的摩内港漫游,要求人们对着镜头笑。整体效果就像当地新闻的彩色专题报道,但当普罗文和我一起在他的实验室里看这些录像带时,我发现自己以全新的眼光审视着这些发笑者。屏幕上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一个模式。普罗文让某人笑,他们会推辞,困惑地看着一秒钟,然后说“我不能就这样笑起来。”然后他们转向他们的朋友或家人,笑声就从他们口中喷薄而出,仿佛呼吸一样自然。即使受试者改变,模式也保持不变:一群高中生在实地考察,一对已婚夫妇,一对大学新生。有一次,普罗文——穿着格子衬衫和卡其裤,看起来有点像喜剧演员罗伯特·克莱因——拦住了两名开着装满垃圾袋的高尔夫球车的废物处理工人。当他们未能按时发出哄笑时,普罗文问他们为什么不能笑出来。“因为你不好笑,”其中一人说。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哈哈大笑。“看,你们俩刚刚互相逗笑了,”普罗文说。“是啊,我们是同事嘛,”其中一人回答道。当普罗文播放这些录像时,这种对笑声模式的执着关注对我产生了奇怪的影响。当我们看到那群高中生时,我完全听不到他们说的话,只听到每隔10秒左右爆发出的有节奏的笑声。从声音上讲,笑声压过了说话声;你几乎听不到歇斯底里下的对话。如果你是一个第一次遇到人类的外星人,你一定会认为笑声是主要的交流方式,口语只是穿插其间的想法。在一次特别响亮的爆发之后,普罗文转向我,说:“现在,你认为他们每个人都在有意识地决定笑吗?”他轻蔑地摇了摇头。“当然不是。事实上,我们常常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笑。我们大大高估了我们对笑声的意识控制。”我们对笑声的自愿控制的局限性在对中枢性面瘫(一种令人不安的疾病)中风患者的研究中得到了最清晰的揭示,这种疾病根据神经损伤的位置,使他们无法自愿移动脸部的左侧或右侧。当这些个体被要求按指令微笑或大笑时,他们会发出不对称的笑容:嘴巴的一侧向上弯曲,另一侧保持僵硬。但当他们被告知一个笑话或被挠痒痒时,传统的微笑和笑声会使他们的整个脸部都生动起来。有证据表明,笑声本身的物理机制是在脑干中产生的,脑干是神经系统最古老的区域,也负责呼吸等基本功能。患有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渐冻症)的患者,这种疾病攻击脑干,经常会出现无法控制的自发性大笑,而没有感到愉悦。(他们也经常经历类似的哭泣经历。)脑干有时被称为爬行动物大脑,因为其基本结构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爬行动物祖先,它主要致力于我们最原始的本能,远离我们理解幽默的复杂、高级大脑技能。然而,不知何故,在这个大脑的原始区域,我们找到了笑的冲动。我们习惯于将普遍但无意识的本能视为基本的适应,例如惊跳反射或新生儿的吮吸。为什么我们会有对笑声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的无意识倾向呢?当我在屏幕上观看它们时,普罗文的青少年让我想起了卡尔·萨根的一段老段子,他首先描述了“一种灵长类动物”,它们喜欢成群结队地聚集,每群50或60个个体,挤在一个黑暗的洞穴里,同步过度换气,直到几乎晕过去。这种行为被描述得如此奇特和有些愚蠢,就像鲑鱼拼命逆流而上直至死亡,或者蝴蝶旅行数千英里每年聚会一次。当然,这个笑话是,这种灵长类动物是智人,而这种群体过度换气是我们喜欢在喜剧俱乐部或剧院,或者与电视笑声轨道的虚拟人群一起大笑的嗜好。我正在思考萨根的引语时,电视扬声器里又传来一阵笑声,我不自觉地发现自己和屏幕上的孩子们一起笑了起来。我情不自禁——他们的笑声很有感染力。
在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的实验室里,笑声专家罗伯特·普罗文(左)研究大卫·斯帕达奇诺和朱莉·怀特对“挠痒痒艾摩”娃娃的反应。普罗文说:“艾摩身上有很多科学。”格雷格·米勒摄
我们可能是地球上唯一以如此大规模群体一起发笑的物种,但我们对笑声的渴望并非独一无二。不出所料,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也是热衷于发笑的,尽管它们的发声器官差异导致笑声听起来更像是喘息。“黑猩猩的笑声是快速而呼吸急促的,而我们的笑声则伴随着声门塞音,”传奇黑猩猩研究员罗杰·福茨说。“此外,黑猩猩的笑声发生在吸气和呼气时,而我们的笑声主要发生在呼气时。但除了这些细微的差异,在我看来,黑猩猩的笑声在大多数方面都与我们相似。”黑猩猩当然不会表演脱口秀,但它们与人类有一个与笑声相关的共同痴迷,普罗文认为这正是笑声根源的核心:黑猩猩喜欢挠痒痒。回到他的实验室,普罗文给我看了两只名叫乔什和莉齐的年轻黑猩猩与人类看护者玩耍的视频片段。这是一场全面的挠痒痒盛宴,当它们的肚子被挠时,黑猩猩们歇斯底里地喘着气。“你听到的是黑猩猩的笑声,”普罗文说。它足够接近人类的笑声,以至于我也忍不住跟着笑起来。父母们会证明,挠痒痒通常是他们与孩子进行的第一种复杂玩耍方式,也是最可靠的笑声诱导剂之一。据福茨说,他曾帮助教导世界最著名的黑猩猩之一沃肖手语,这种行为在黑猩猩中同样普遍,甚至可能更长寿。“挠痒痒……对黑猩猩来说似乎非常重要,因为它贯穿它们的一生,”他说。“即使37岁的沃肖仍然喜欢被她的成年家庭成员挠痒痒和挠痒痒。”在被教过手语的年轻黑猩猩中,挠痒痒是一个常见的话题。像笑声一样,挠痒痒几乎按定义就是一种社交活动。与幽默的不协调理论一样,挠痒痒依赖于一定的惊喜元素,这就是为什么不可能自己挠痒痒的原因。可预测的触摸不会引起笑声和扭动,而是不可预测的触摸才能奏效。许多与挠痒痒相关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挠痒痒利用了感觉运动系统对自身与他人之间差异的感知:如果系统命令你的手移向你的肚子,当肚子上的神经末梢报告被抚摸时,它不会感到惊讶。但如果触摸是由另一个感觉运动系统产生的,那么抚摸肚子就会带来惊喜。挠痒痒愉快的笑声是大脑对这种触摸的反应。在人类和黑猩猩社会中,这种触摸通常首先出现在亲子互动中,并在建立这些最初的纽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罗杰·福茨说:“(挠痒痒和笑声)如此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在维持家庭和社区内的友好情感纽带方面发挥作用。”几年前,贾里德·戴蒙德写了一本标题 provocative 的短书《性为什么有趣?》这些最近的研究为挠痒痒为什么有趣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进化的答案:它鼓励我们与他人友好相处。幼童对挠痒痒这种嬉闹玩耍的接受度很高,即使是假装挠痒痒也常常会让他们捧腹大笑。(福茨报告说,挠痒痒的威胁对他的黑猩猩也有类似的效果。)在他的书中,普罗文认为“假装挠痒痒”可以被认为是“最初的笑话”,是第一个旨在利用挠痒痒-笑声回路的刻意行为。我们的喜剧俱乐部和情景喜剧是那些最初童年玩耍交流的文化增强版本。与吮吸和微笑本能一样,挠痒痒的笑声作为一种巩固亲子关系的方式而进化,为成年人的社交生活延续奠定了基础。我们曾经因为父母或兄弟姐妹的惊喜触摸而发笑,现在我们因为妙语的意外转折而发笑。鲍灵格林州立大学教授亚克·潘克塞普认为,大脑中存在一个专门的“玩耍”回路,与研究更广泛的恐惧和爱回路相当。潘克塞普研究了嬉闹玩耍在巩固幼年大鼠社会联系中的作用。玩耍本能不易被抑制。被剥夺这种玩耍机会的大鼠——这种玩耍具有独特的动作编排和吱吱作响的声音,这可能是大鼠的笑声——一旦有机会,仍然会立即参与玩耍行为。潘克塞普将其比作鸟类的飞行本能。“可能所有最强烈的积极情绪——一旦你的肚子饱了,没有生理需求——就是年轻人之间充满活力的社交互动,”潘克塞普说。“人类大部分的笑声似乎发生在幼儿时期——嬉闹玩耍、追逐,所有他们喜欢的事情。”玩耍是年轻哺乳动物会做的事情,在人类和黑猩猩中,笑声是大脑表达玩耍愉悦的方式。“既然笑声似乎是仪式化的喘息,那么你发笑时基本上就是在复制嬉闹玩耍的声音,”普罗文说。“而且你知道,这就是我认为它起源的地方。挠痒痒是我们灵长类动物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触摸和被触摸是作为哺乳动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他的实验室里,普罗文背对着导师维克托·汉堡格严肃的面孔,记录下自己的笑声。他使用声学分析仪来分离构成普通和“禁忌”笑声变体的模式。 格雷格·米勒摄
关于笑声的神经学基础,我们还有很多未知。我们尚不清楚为什么笑会带来如此美妙的感觉;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刺激伏隔核(大脑的快乐中心之一)会引发笑声。潘克塞普进行的研究表明,阿片受体拮抗剂会显著降低大鼠玩耍的欲望,这意味着大脑的内啡肽系统可能与笑声带来的愉悦有关。一些轶事和临床证据表明,笑通过抑制应激激素和提高免疫系统抗体来使你更健康。如果你认为笑是一种与识别幽默基本同义的行为,那么“笑让你更健康”的说法似乎很奇怪。为什么自然选择会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对笑话做出反应呢?普罗文的方法有助于解开这个谜团。我们的身体不是对俏皮话和妙语做出反应,它们是对社会联系做出反应。在这方面,笑提醒我们,我们的情感生活既是外向的,也是内向的。我们倾向于将情感视为私事,是浸润我们主观世界的感觉。但情感也是社会行为,笑声或许更是如此。我们有如此多精心编排的姿势和面部表情——其中许多似乎是我们物种与生俱来的——来表达我们的情感,这并非偶然。我们的情感系统旨在分享我们的感受,而不仅仅是将其内在地呈现——达尔文在一个多世纪前在他的著作《人与动物的情绪表达》中首次提出了这一见解。“面部和身体的表情动作,无论其起源如何,本身对我们的幸福都非常重要。它们是母婴之间最早的交流方式;她微笑表示赞同,从而鼓励孩子走上正确的道路……通过外在迹象自由表达情感会增强情感。”即使我们尚未了解笑声带来愉悦的神经学基础,我们也应该寻求传染性笑声带来的联系,这是有道理的。毕竟,我们是社会性动物。如果这种笑声常常涉及一些相当幼稚的行为,那就随它去吧。“我的意思是,这就是我们不像蜥蜴的原因,”普罗文把“挠痒痒艾摩”娃娃放在膝上说。“蜥蜴不玩耍,它们不像我们这样社会化。当你开始看到玩耍时,你开始看到哺乳动物。所以当我们聚在一起玩得开心、大笑时,我们正在回归我们的根源。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讽刺的:生活中最能给我们带来愉悦的一些事情,实际上是最古老的。”
要了解更多关于罗伯特·普罗文的信息,请参阅他的著作《笑声:一项科学调查》(纽约:企鹅图书,2000年),或访问他的网页:www.umbc.edu/tmp/provine。
要了解亚克·潘克塞普关于快乐和笑声的神经化学和神经解剖学研究,请访问他的网页:caspar.bgsu.edu/~neuro/Faculty/Faculty_JPanksepp.htm。
再次阅读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并在赫特福德大学理查德·怀斯曼的LaughLab网站上笑笑那些落选者。不要错过不同国家最受欢迎的笑话排名:www.laughlab.co.uk。
要了解更多关于罗杰·福茨的工作,请访问黑猩猩与人类交流研究所的主页:www.cwu.edu/~cwuchci/mai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