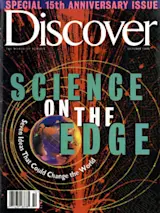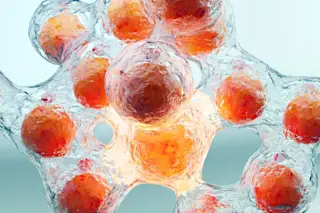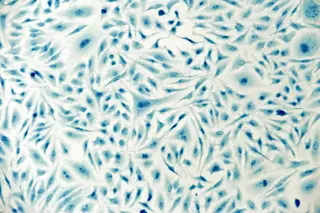保罗·埃瓦尔德从一开始就知道扎伊尔的埃博拉病毒爆发会逐渐平息。5月26日,在连续八天只报告了六个新病例之后,这种平息正式成为现实。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不再需要每天更新埃博拉数据(尽管零星病例一直报告到6月20日)。
这种病毒已经将扎伊尔的班顿杜省置于其致命的控制之下数周,感染了约300人,其中80%的人死亡。大多数感染者来自基奎特镇。
这一切都正如埃瓦尔德所预测的那样。他回忆说,当埃博拉疫情爆发时,我像以前一样说过,这些事情会突然出现,会蔓延,你会经历一次严重的疫情,大约100到200人在医院,也许疫情会蔓延到另一个孤立的社区,但随后它会自行消退。
埃瓦尔德不是预言家。他是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的进化生物学家,也许是世界上关于传染病以及引起这些疾病的生物如何进化的主要专家。他也是一些人吹捧的下一个伟大医学革命的推动者: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应用于理解人类疾病。
达尔文的观点可以阐明埃博拉病毒一旦进入人群后如何在人际间传播。(在人类疫情之间,病毒存在于一些未知的生活宿主中。)埃瓦尔德解释说,病原体只有在其后代能够轻易地从一个宿主传播到另一个宿主的情况下才能在人群中存活。一种方法是花费很长时间才能使宿主丧失能力,给他足够的时间接触其他潜在受害者。然而,埃博拉病毒通常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迅速致死。另一种方法是在人体外长时间存活,以便病原体可以等待新的宿主找到它。但迄今为止遇到的埃博拉病毒株几乎立即被阳光摧毁,即使没有阳光照射,它们在人体外也往往会在一天之内失去传染性。“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你可以将95%不构成主要威胁的致病生物与5%构成威胁的区分开来,”埃瓦尔德说,“埃博拉病毒真的不属于那5%。”
达尔文医学方法的最早建议出现在1980年,当时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进化生物学家乔治·威廉姆斯读到了一篇文章,埃瓦尔德在文章中讨论了如何运用达尔文理论来阐明传染病某些症状的起源——例如发烧、低铁含量、腹泻。埃瓦尔德的方法引起了威廉姆斯的共鸣。23年前,他曾写过一篇论文,提出了衰老(senescence)的进化框架。“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并没有担心衰老的实际方面,即医学方面,”威廉姆斯指出,“那时我还很年轻。”然而,现在,他开始重视起来。
当威廉姆斯发现埃瓦尔德的作品时,兰道夫·内塞正在发现威廉姆斯的作品。内塞是一名精神病学家,也是密歇根大学进化与人类行为项目创始人之一,他正在探索自己对衰老过程的兴趣,他和威廉姆斯很快就走到了一起。“他一直想找一位医生一起研究医学问题,”内塞说,“而我一直想找一位进化生物学家,所以我们俩是非常自然的结合。”他们的合作导致了1991年的一篇文章,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这篇文章标志着该领域的真正诞生。
内塞和威廉姆斯将达尔文医学定义为寻找疾病易感性的进化解释。正如埃瓦尔德所指出的,它可以是一种解读身体防御机制的方式,例如,试图弄清楚我们感冒时为什么会感到疼痛或流鼻涕的原因,并确定我们应该或不应该对这些防御机制做些什么。例如,像阿尔伯克基洛夫莱斯研究所的生理学家马修·克鲁格这样的达尔文研究人员现在认为,体温适度升高不仅仅是疾病的症状;它是一种进化适应,身体通过使自己不适合入侵微生物来对抗感染。那么,似乎如果降低发烧,可能会延长感染。然而,没有人准备说我们是否应该扔掉我们的阿司匹林瓶。“我很想看到十几个关于在有人患流感时降低体温是否明智的恰当研究,”内塞说,“这从未做过,令人震惊的是它从未做过。”
腹泻是疾病的另一个常见症状,有时是病原体为了自身利益操纵你身体的结果,但它也可能是你身体的一种防御机制。例如,霍乱细菌一旦侵入人体,就会通过产生毒素使肠道细胞渗漏,从而诱发腹泻。由此产生的腹泻既可以清除肠道中竞争的益生菌,也可以将霍乱细菌带到外界,以便它们能够找到另一个不幸的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对于霍乱来说,停止腹泻似乎只会带来好处。
但由志贺氏杆菌入侵引起的腹泻(导致各种形式的痢疾)似乎更多是肠道防御而非细菌攻击。感染会导致肠道周围肌肉更频繁地收缩,显然是为了尽快排出细菌。十多年前进行的研究表明,使用洛哌丁胺等药物来减少肠道收缩并减少腹泻排泄实际上会延长感染。另一方面,非处方药如Pepto Bismol中的成分不影响肠道收缩的频率,可用于止住腹泻流而不会延长感染。
西雅图生物学家玛吉·普罗费特指出,月经是另一个更应被视为进化防御的症状。正如普罗费特所指出的,身体进行如此耗费体力的活动,如脱落子宫内膜和排出血液,一定有充分的理由。她声称,这个理由是为了清除子宫内可能随精液中的精子而来的任何微生物。如果卵子受精,感染可能值得冒险。但是,如果卵子没有受精,普罗费特说,身体会通过排出可能已被感染的子宫细胞来保护自己。同样,普罗费特推测,怀孕期间的晨吐会导致母亲避免食用可能含有对发育中的胎儿有害化学物质的食物。如果她是正确的,用药物阻止这种恶心可能会导致更高的流产率或更多的出生缺陷。
达尔文医学不仅仅是关于治疗哪些症状和忽略哪些症状。它是一种理解微生物的方式——因为它们的进化速度比我们快得多,除非我们能找到如何利用它们的进化力量为我们自己谋利的方法,否则它们可能总是胜过我们。它也是一种认识到在人群中持续存在的致病基因,从长远来看,通常是被选择而非被淘汰的方式。
镰状细胞性贫血是进化如何权衡成本和收益的经典案例。多年前,研究人员发现,携带一个镰状细胞基因副本的人比不携带该基因副本的人更能抵抗引起疟疾的原生动物。携带两个基因副本的人可能会死亡,但在疟疾肆虐的地区,如热带非洲,他们的数量将通过具有抗病能力的亲属留下的后代得到弥补。
囊性纤维化也可能通过这种遗传逻辑持续存在。动物研究表明,携带一个囊性纤维化基因副本的个体可能对霍乱杆菌的影响更具抵抗力。与疟疾和镰状细胞性贫血的情况一样,霍乱的患病率远高于囊性纤维化;由于携带单个、赋予抵抗力的基因副本的人数远多于携带致病双重剂量的患者,因此该基因可以稳定地代代相传。
“凭借我们进行基因操作的能力,人们会忍不住去寻找那些导致衰老的基因,并将其剔除,”内塞说,“如果我们对一个基因的所有功能都了如指掌,那没问题。但进化论的方法告诫我们不要操之过急,并要预期每个基因都可能既有好处也有代价,甚至可能有一些完全不相关的好处。”
达尔文医学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石器时代设计的身体在新时代遇到的问题。正如西蒙弗雷泽大学的进化心理学家查尔斯·克劳福德所说:“几千年前,我常常去追逐剑齿虎。我得到了很多锻炼等等。现在我坐在电脑前,只玩鼠标,没有锻炼。所以我以各种未知的方式改变了我的身体生物化学,这可能会以各种方式影响我,但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
埃默里大学的放射科医生博伊德·伊顿及其同事认为,这种生化变化是当今乳腺癌流行的幕后推手。虽然不可能研究石器时代人的生化,但仍然存在一些狩猎采集群体——例如非洲的桑族人——他们可以作为令人钦佩的替代者。伊顿指出,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也意味着月经开始较晚、第一个孩子出生较早、孩子数量更多、母乳喂养数年而非数月,以及更年期提前的生活方式。总的来说,他说,如今的美国女性经历的月经周期可能比我们一万年前的祖先多3.5倍。在每个周期中,女性体内都会充满雌激素,而乳腺癌,正如研究发现的,与雌激素密切相关。乳房接触雌激素的频率越高,肿瘤生长的机会就越大。
根据您选择的数据,今天的女性患乳腺癌的可能性是我们的祖先的10到100倍。伊顿提出的解决方案相当激进,但他希望人们至少能考虑它们;其中包括用荷尔蒙延迟青春期,以及使用荷尔蒙制造假妊娠,这能让女性在年轻时获得怀孕的生化优势,而无需生育孩子。
总的来说,达尔文医学告诉我们,组成我们身体的器官和系统并非源于追求完美,而是数百万年进化妥协的结果,旨在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繁殖效益。我们直立行走,但脊柱是在我们四肢爬行时进化的;双腿平衡解放了双手,但我们可能也总是会受到一些背痛的困扰。
“真正不同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一直用进化论来解释事物为何起作用,为何是正常的,”内塞解释道。“这种转变——我不知道它是简单还是深刻——在于我们试图理解异常,理解疾病的脆弱性。我们试图理解为什么自然选择没有让身体变得更好,为什么自然选择让身体留下了脆弱性。对于每一种疾病,都有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对于极少数疾病,答案仍然非常不明确。”
这些答案尚不明确的一个原因是,很少有医生或医学研究人员从达尔文的视角进行过认真的调查。在许多情况下,这是因为进化理论难以检验。无法观察人类进化的进程——它充其量是在数十万年的时间尺度上运作的。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进化生物学家詹姆斯·布尔说:“达尔文医学主要是一种猜测游戏,猜测我们认为进化在过去是如何作用于人类的,它把我们设计成了什么样子。几乎不可能检验我们进化是为了应对这种或那种环境的观点。你可以做出有根据的猜测,但没有人会出去做一个实验来证明,是的,事实上人类在这种环境条件下会以这种方式进化。”
然而,有些人说这些实验可以、应该、也将会进行。康奈尔大学的感觉生理学家霍华德·霍兰正在进行这样一项进化实验,希望能干预影响四分之一美国人的近视。近视被认为是试图将图像聚焦在视网膜上的精细反馈回路的结果。容错空间不大:如果你的眼球长度偏离十分之一毫米,你的视力就会模糊。研究表明,当眼睛感知到图像模糊时,它会通过改变其长度来补偿。
霍兰指出,这个循环显然有遗传成分,但驱动它的是环境。在石器时代,当我们在田野里追逐野牛时,我们看到的图像通常是清晰的。但随着现代文明的到来,大量近距离工作也随之而来。当你的眼睛聚焦在附近物体上时,晶状体必须弯曲,由于弯曲晶状体是很费力的工作,你会尽可能少地弯曲。这就是为什么,无论你是否意识到,近距离物体往往会有点模糊。“模糊图像?”眼睛说,“是时候生长了。”它生长得越多,那些野牛就越模糊。近视似乎是工业社会的疾病。
为了预防这种疾病,霍兰建议回到石器时代——或者至少让人们的眼睛相信他们身处石器时代。他说,如果你给视力正常的人戴上眼镜,让他们以为自己正在看远处的物体,而实际上他们正在看近处的物体,那么从一开始就可以避免整个反馈循环。军事院校招收视力20/20(即正常视力)的年轻人,他们要经历四年的大学生活,并接受飞行或执行某些困难视觉任务的训练。但是,霍兰指出,由于他们读了大量的书,出来后却近视了,不再符合从事他们被聘用的工作。“我认为这些人非常希望在学习过程中不近视。”他希望在一年内给他们戴上眼镜。
对于那些对困扰我们的细菌如何进行其肮脏工作的研究人员来说,进化的缓慢速度要小得多。细菌数量如此之多(一个人携带的病原体可能比地球上的人口还多),进化速度如此之快(一个细菌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以繁殖一百万次),以至于我们无法想象在人类身上进行的实验,可以在微生物身上短短几周内完成。埃瓦尔德说,我们甚至可以利用进化理论来驯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他指出,艾滋病毒变异速度如此之快,我们肯定会发现大量既温和又严重的突变株。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哪种变异株会胜出?他说,就像埃博拉病毒一样,这都取决于病毒如何有效地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
“如果与新伴侣发生性传播的潜力很大,那么繁殖迅速的病毒就会传播,”埃瓦尔德说。“由于它们在对宿主健康至关重要的细胞类型——辅助性T细胞中繁殖,那么这种细胞类型就会被大量破坏,宿主很可能会因此遭受痛苦。另一方面,如果你降低传播率——通过禁欲、一夫一妻制、使用避孕套——那么更严重的毒株很可能在有机会传播很远之前就死亡了。”埃瓦尔德说,真正的问题是,通过降低病毒传播给新伴侣的速度,你能把这种病毒变得多温和,以及这种变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发生?他指出,塞内加尔已经存在毒性如此之低的艾滋病毒毒株,以至于大多数感染者都会死于老年。“我们没有所有的答案。但我认为我们将与这种病毒长期共存,如果必须与它共存,那就让我们与一种真正温和的病毒共存,而不是一种严重的病毒。”
尽管避孕套和一夫一妻制并非特别激进的治疗方法,但它们不仅能抵御病毒,还能驯服病毒,这却是一个激进的观点——一些研究人员对此持怀疑态度。“如果它变得过于剧毒,它最终会通过过快杀死宿主来切断自身的传播,”詹姆斯·布尔指出,“但推测认为,人们主要在感染后一到五个月内传播艾滋病毒,那时他们血液中的病毒水平很高。因此,对于艾滋病毒,主要的传播期发生在感染后的几个月内,然而毒性——由此导致的死亡——却发生在几年后。主要的传播阶段与毒性是脱钩的。所以除非每个人都始终采取保护措施,否则我们无法阻止大多数传播实例;毕竟,大多数人在传播病毒时甚至不知道自己已被感染。”
但埃瓦尔德认为这些保护措施值得一试。毕竟,他说,病原体驯化在过去也曾发生过。我们在美国遇到的痢疾形式相当温和,因为我们纯净的水源切断了细菌毒性菌株的主要传播途径。卫生条件的改善不仅减少了病例数量,还筛选出了较温和的志贺氏菌,这些菌株让受害者身体状况良好,能够正常活动。白喉是另一个例子。当白喉疫苗被发明时,它只针对最严重的白喉毒素形式,尽管这是出于经济而非进化的原因。然而,多年来,这种选择淘汰了最毒性的白喉菌株,筛选出了那些导致很少或没有症状的菌株。今天,这些较弱的菌株就像另一层疫苗一样,保护我们免受新的、毒性菌株的侵害。
埃瓦尔德说:“你对这些生物所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对狼所做的一样。狼对我们来说很危险,我们驯化它们成为狗,然后它们帮助我们,警告我们提防那些准备伤害我们孩子的狼。通过这样做,我们基本上将一个有害的生物变成了一个有益的生物。我们对白喉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我们拿了一个正在造成伤害的生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把它驯化成一个保护我们免受有害生物侵害的生物。”
创建一个新的科学学科并使其获得认可本身就是一个进化过程。尽管威廉姆斯和内塞表示有数百名研究人员(无论他们是否知晓)正在这个新建立的框架内工作,但他们意识到这个领域仍处于起步阶段。达尔文医学成为家喻户晓的词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内塞讲述了《著名医学杂志》的一位编辑被问及该领域时回答:“达尔文医学?我没听说过,所以它不可能很重要。”
但达尔文医学的批评者并不否认该领域的合法性;他们主要指出它缺乏明确的答案,缺乏清晰的临床指南。“我认为这个想法最终会成为医学的基础科学,”内塞回答说,“例如,人们在1900年的时候,当生物化学家们正在研究克雷布斯循环时,他们说了些什么?人们会说,‘那么生物化学与医学到底有什么关系?在了解克雷布斯循环之前,你现在能治愈什么病?’生物化学家们只能说,‘嗯,天哪,我们不确定,但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正在回答重要的科学问题,最终这会很有用。’我认为这里也完全适用同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