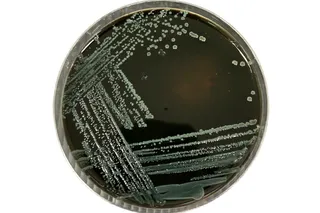罗伯特·梅爵士播下了混沌理论的种子,他通过数学模型研究生态系统和传染病的成果,已经转化为全球性的保护工作和对艾滋病的认识。作为英国前首席科学顾问,以及在疯牛病时期的国家最高科学权威,他制定了一套科学建议的决策和向公众发布的规程。2000年,他被任命为皇家学会会长,这是科学界最受尊敬的职位之一,在那里他继续与政府密切合作,制定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科学问题政策。
政府应该怎么做才能帮助科学?
M:科学传授给下一代的方式需要改进。我们需要增加基础科学的支出,以创造新知识,并确保资金得到最大化利用,包括直接的科研经费和基础设施的间接成本,如建筑和设备。在英国,我们希望更多地抓住那种能够最终将想法推向市场的创业精神,就像美国做得那样好。
为什么美国的体系运作得更好?
M:我认为这是拥抱风险的文化。这是一种愿意冒险、放弃工作,将实验室里的成果推向市场的意愿。在英国,人们的本能是想保住自己的工作,以便有后路,然后兼职尝试将其推向市场。这种情况正在缓慢改变。
这是否基于人们所处的经济环境?
M:这更多的是关于意愿。你想想看,在英国和欧洲,大多数大学教育基本上是免费的,人们毕业时并没有觉得自己对任何人或任何事负有义务。在美国,人们,尤其是在私立大学,常常要支付巨额费用,毕业时感到债务缠身,并认为这并未涵盖真正的成本和效益。
有没有一种成功的模式来做好科学研究?
M:我不相信任何关于科学如何进行的哲学。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几乎是存在主义式的提问过程。有不同的风格。有些人会非常有用,也过得非常快乐,他们花一生的时间深入到一个狭窄的领域,对某个问题了解得越来越多。另一些人,你可以说,注意力不太集中,他们乐于跳来跳去,更关注某个事物的早期阶段:它的基本是什么,然后将进一步的阐述留给不同类型的人。这种性格类型不一定适合一个需要十年时间来解决一个问题的大型团队。两者都需要。而我属于注意力不集中的那一类。
您如何看待“忧思科学家联盟”对布什总统的批评?
M:我会谨慎措辞。该联盟有许多非常成功和杰出的成员。布什政府被认为是为了符合其他方面的意识形态结论而挑选和选择科学建议,就像在法庭上提出一个案子,而不是客观地解决不确定性。而且,它被认为疏远了那些不认同意识形态议程的声音。因此,您看到的是一场相当独特的抗议,这在欧洲并不常见。英国科学界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忧思科学家联盟”的说法具有说服力。
为什么欧洲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
M:嗯,在英国,我们有一个程序,部分是在疯牛病之后建立的。它基于一种理解,即需要一个不随政府更迭而改变的科学管理机构,而且是在最高层。我们设立了一个科学技术办公室,由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担任常务秘书长。并且有科学建议和政策制定的指导方针。因此,有一套明确的规程来处理口蹄疫或干细胞研究等热门话题。
那些规程是什么?
M:它们规定您应该广泛征求意见,刻意寻求不同意见,并应明确说明已知和不确定的内容,然后公开发表。如果可以把一群人关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出来说“这就是结论”,那么决策过程会容易得多。但科学并非如此非黑即白——一天我们不确定,第二天我们就确定了。它是一个意见的图景,在实验的指导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占主导地位的意见集群,最终你会看到一个大的高峰,人们会同意平方反比定律来解释行星的运动。长远来看,你想要公众的信任,而通过公开辩论来建立信任。
为什么欧洲人对转基因食品如此不满?
M:疯牛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做出了过于确定的声明:疯牛病不会影响人类。事实上,当时应该说的是:“这非常不太可能,因为它有点像绵羊的痒病,而绵羊的痒病似乎不会造成任何伤害,所以可能没问题,但我们不知道,你们必须自己决定。”因此,在经历过这样的食品恐慌之后,一些游说团体说我们需要担心转基因食品;政府却说一切都很好。辩论被光谱两端的喧闹声音所主导,但公众却被排除在讨论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出现有益的产品时——比如无过敏原的坚果,或者一种让你变得苗条又聪明的“黄金苹果”——人们才会参与到辩论中来。
政府如何监管像干细胞研究这样的争议性科学?
M:在英国,我们花了三年时间就干细胞问题进行辩论,这是建立在早期辩论,如体外受精的基础上的。如果你做公众民意调查,会发现人们以二比一甚至更高的比例支持我们现有的更宽松的立法,这在议会中得到了体现。对话询问我们将打开哪些门,又想关闭哪些门。而一个能够响应这种对话的政治进程是政府最重要的部分。创造新知识,然后将新知识传播给人们,只有当整个社会都满意于知识的应用时,才会有成效。
哪些国家在科学方面做得更好?
M:如果你只看单凭数量谁是世界领导者,美国当然是领导者,无论你是计算论文、引用次数,还是任何东西。但这混淆了规模与质量。我的意思是,毕竟,美国在奥运会上获得的奖牌最多。但按人口比例计算,每位公民的奖牌数,美国甚至不在前20名之列。在科学领域,如果你按人口或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引用次数,瑞士是第一名。但美国非常强大。如果你看看世界上引用率最高的1%的论文,那么美国按人口比例计算,略低于英国,但远高于欧盟。有趣的是,欧盟的进步非常显著,如果以此为基础进行预测,再过几十年,谁能说得准呢?印度和中国也正在展现出巨大且快速的增长。
除了钱之外,要做到科学研究的生产力还需要什么?
M:总的来说,在花费的钱与表现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而且这种相关性往往是表现最好的国家,实际上是确保年轻人能够自由追求自己的议程并表达创造力,而那些让年轻人在培训或层级森严的学徒制和对长辈的尊重中停留太久的体系,则无法获得同等的价值。如果你看看欧洲的三大科学支出国——法国、德国和英国——它们都有出色的人才,但德国和法国的许多最佳科学研究是在专门的研究所进行的,而不是在充满无畏的年轻人的大学或类似环境中进行的。这也许就是英国生产力更高的原因。
那么,无畏是好事吗?
M:科学是关于提问的。科学常常被视为琐碎的、有确定答案的事实,无论是在选择题考试还是在《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中。但科学的激动人心之处在于前沿领域,那里往往存在着真正的不确定性——例如,干细胞。科学既关乎提出问题,也关乎给出答案,而我们在许多科学教学方式中未能捕捉到这种兴奋和活力。那些快乐地质疑所被告知的内容,而不怎么尊重,那些有点不知道该想什么的人,才是重要的。即使在繁荣的民主制度下,你也未必能充分发挥这种潜力,而如果你没有鼓励普遍言论自由的制度,就极其难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