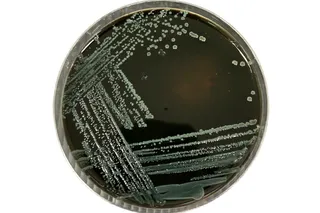去年,我开始在阿米什地区中心的一家医院工作。我的第一个阿米什病人是一位看起来很苍老的妇女,但她的病历显示她只有49岁。她朴素的蓝色棉质衬衫用直针整齐地扣在前面。只有阿米什男人才允许使用纽扣;如果一个女人穿带纽扣的衣服,她就被认为是虚荣的。
“你生了多少个孩子?”我出于简单的好奇心问她。
“十三个,”她说。
阿米什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截然不同,令人着迷。我花了几个月时间了解它,但就医疗保健而言,这两个世界有很多共同之处。像其他人一样,阿米什人会在孩子喉咙痛和耳痛时带他们来看病。他们的孩子接种了疫苗;年老的阿米什人戴助听器,欢迎安装心脏起搏器。他们甚至乘坐汽车——他们只是不能拥有汽车或驾驶汽车。许多阿米什人,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不再务农。在我工作的镇上,几百人在当地一家奶酪工厂工作。阿米什人不允许吸烟或饮酒,但我看到一些阿米什男人吸烟和饮酒,有时过量。一些女人也吸烟,但只在男人不在家的时候在后门廊上吸。
一天晚上,我拿起了一位22岁妇女的病历,据分诊护士说,她的主要抱怨是“产后三周”。我心想,这不算什么抱怨。我收起病历和听诊器,走向4B病房,那里恰好是为精神病人保留的。在门口,我发现一个女人抱着一个用蓝色毯子包裹着的小婴儿,婴儿睡着了。
“你的小家伙怎么样?”我问。
“哦,”女人说,“他不是我的。”她指了指小床。“那是她的孩子。我是她姐姐。”
小床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低着头,肩膀耷拉着。
“有什么问题?”我把问题转向她姐姐,因为病人看起来非常困扰。
“她想杀死她的孩子,”她平淡地说。
我肯定站在那里呆了一会儿,张着嘴,因为她急忙向我保证:“不,真的。她说她也想自杀。”
产后抑郁症。我的第一个想法是,阿米什人中不会有这种病。我从未见过多动的阿米什儿童,也没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没有“边缘型病人”。我见过几例普通的轻度抑郁症——似乎大多是由婆婆引起的。否则,阿米什人似乎没有困扰我其他病人的情绪和思维障碍。
“她真的很糟糕,”姐姐说。“她不吃东西。她根本不睡觉,她告诉我她无法停止想孩子。她害怕自己会伤害孩子。”
我向病人做了自我介绍。“今天有什么问题?”我问。
她耸了耸肩,甚至没有抬起头。
我跪下来,想看清她头巾下面的脸。“你能跟我说说话吗?”
她耸了耸肩,说:“我一直在想坏念头。”
“什么样的坏念头?”
“关于我孩子的坏念头。”
“多久了?”
她想了一分钟。“这个星期。”停顿了一下,她说,“有个小声音告诉我杀死我的孩子。它是个邪恶的婴儿。”她抬头看着天花板,歪着头,仿佛在听什么人说话。“不,不,”她轻声说。
这不是产后抑郁症。这是产后精神病。这位女士需要住院。
“你要把我关起来,不是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她说。
“我们需要保证你的安全,”我说。“我不确定你现在独自一人是否安全。”
“我想上帝需要惩罚我有了坏念头。”
“我不认为事情是这样的。我认为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帮助你感觉好起来。”
“没有什么能帮助我,”她说。
我离开房间后,那种阴郁感是如此强烈,我似乎一直带着它。我坐下来,看着她的病历,喃喃自语:“产后三周……”
我知道生完孩子后可能会感到不快乐。产后抑郁通常出现在最初几周,当新生命颠覆了一个女人的世界时。这些“忧郁”不一定等同于坏情绪,更多的是一种不稳定的情绪。女性可能在一分钟内确信“一切都不对劲”和“我是一个坏妈妈”,然后突然感觉一切都好。这些情绪为何发生仍是未知数。性激素和调节压力的激素失调被怀疑是原因,但尚未有证据表明存在联系。
大约五分之一的女性经历更严重的产后抑郁症,这往往比产后忧郁症来得晚,通常在产后六到八个月。产后女性的抑郁症发病率与一般人群的抑郁症发病率大致相同,这表明生孩子可能不是一个因素。治疗方法与常规抑郁症大致相同——咨询和抗抑郁药——尽管如果母亲正在哺乳,药物会有问题。
产后精神病则罕见得多,每1000名女性中有一两例。它在分娩后几天到几周内出现,通常与其他精神疾病相关。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其他案例涉及一名产后五天的女性。当我采访她时,她比这位女性更激动,更狂躁。她丧失了理智能力。然而,她没有精神病史,婚姻幸福,是一名牙科保健员。“躁郁症,”主治医生告诉我,“毫无疑问。”有终身精神障碍史的母亲,如躁狂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最有可能经历产后精神病。安德里亚·耶茨(Andrea Yates)的悲剧案例就是一个例子,她淹死了她的五个孩子。她告诉调查人员,她认为拯救孩子免受永恒诅咒的唯一方法就是杀死他们。她认为撒旦住在她体内,如果德克萨斯州处决她,邪恶就会从世界上消除。这种强大的妄想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很常见。
治疗病人的第一步是让她住院,并将孩子安置在安全的环境中。下一步是治疗症状,这可能需要抗精神病药物和镇静剂。
我转身望向那个女孩所在的房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会在我的阿米什病人身上看到各种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重度抑郁症、自杀冲动、酗酒、痴呆症。我感到幻灭。我曾想当然地认为阿米什人生活在一个彼此紧密相连、充满精神生活的世界里。我曾想相信他们的世界没有精神疾病。
我看到她姐姐站在病人旁边,一只手臂抱着婴儿,另一只手臂环绕着她姐姐的肩膀。门口站着一个害羞的年轻人,可能是丈夫,还有一个年长的男人,也许是父亲或牧师。病人现在正在哭泣,肩膀颤抖。他们都低着头。我回望他们,第一次明白,当遇到厄运、困境和可怕疾病时,阿米什人也和我们其他人一样,无法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