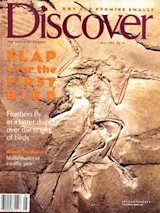他看起来病得很重。非常重。
住院医生焦急的语气,即使在繁忙的急诊室的嘈杂声中,也像一声喊叫一样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迅速写完了手头的病历,并让自己有空。
怎么回事?我问她。
一名二十岁的中国男性昨晚来就诊,抱怨头痛和发烧。夜班团队认为可能是脑膜炎,所以做了腰椎穿刺。但实验室刚刚打来电话,说脑脊液是清澈的,所以不是脑膜炎。现在他的体温又升到了103度。
在芭芭拉(住院医生)找到我之前,她已经和急诊室里碰巧在场的一位神经科医生谈过了这个病例。快速看了一眼我们病人的房间,就足以在他老鹰一样的脸上刻下了忧虑的皱纹。
我找不到任何异常,他说,在给我们的病人做了一次快速的神经系统检查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脑肿瘤、中风、脓肿或其他明显的头痛源。不幸的是,他不会说英语,所以很难了解情况。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头痛得厉害。他建议做CT扫描可能不是个坏主意。
当我们围在病人房间外时,一位护士递来了他第二次血常规报告。我们都目瞪口呆。六个小时前,他血液中红细胞的比例是36%——虽然低,但还不危险。现在是30%。就在我们眼皮底下,他几乎损失了近一夸脱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而且没有人知道原因。
我转向芭芭拉。这孩子是哪里人?
据我们所知,来自中国南方,她回答道。昨晚医院里没有会说粤语的翻译。夜班的两位医生检查了他,据他们所知,他来美国三四个月了。显然,他已经头痛很久了。
仿佛从某种记忆宝箱深处被释放出来,各种热带疾病蜂拥而至,各种由原生动物、线虫、真菌、病毒和细菌引起的疾病。但没有明显的原因可以解释这位年轻人的症状。
好了,在我们做任何其他事情之前,让我看看,我说,更多是为了履行我作为芭芭拉上级的职责,而不是出于任何希望——作为第五位医生,能嗅出任何遗漏的线索。
在神经科医生说了句“祝你好运”之后,我们一起走进了检查室。我向年轻的病人露出了我最友好的微笑,但他只能捂着头,这种姿势无论用什么语言都表达着痛苦。我摸了摸他的额头。他发烧了。他的床单都湿透了。但其他的检查我一无所获。一切都很正常:脖子灵活,肺部清晰,心脏规律,腹部柔软,皮肤无瑕。检查完后,芭芭拉和我快速回顾了我们所知道的。答案是,引用达希尔·哈米特的话来说:一无所获,一无所知。
只剩下一件事可做了。我仰起头大喊:这里有会说粤语的吗?两位护士转过身,指向了朱迪思。
朱迪思是急诊室里最好的护士之一——对防止年轻住院医生犯错和约束年长的主治医生至关重要。我走到她面前,双手合十,做出恳求的姿势。
在芭芭拉和我陪同下,朱迪思走近年轻病人的床边。我告诉她我们所知道的他不多的病史,然后让她从头开始讲:他来美国多久了?什么时候开始生病的?从他接下来的连珠炮似的粤语交流中,我意识到她正在不经我的提示,就已经在回答我接下来要问的几个问题了。
在我们等待朱迪思翻译的时候,我瞥了一眼病人透明的塑料尿壶。尿壶几乎满了,尿液呈棕色,深桃花心木色。突然,仿佛我的大脑被踢对了地方,齿轮终于卡住了。
你听说过“黑水热”这个词吗?我问芭芭拉。
嗯,没有,她回答道,然后给了我一个期待的眼神。
我指了指尿壶。
过去,人们称恶性疟疾——最严重的疾病形式——为黑水热,因为它会严重破坏红细胞,导致患者的尿液变黑。不过,我的猜测似乎牵强。许多其他疾病也会引起尿液颜色变深,而且疟疾在该国已不再是地方性疾病。在美国,几乎所有的病例——1990年约有1100例——都发生在旅行者或新移民身上。大多数美国医生甚至从未见过一例。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家伙去过哪里。
朱迪思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他只来美国三周,而不是三个月。他从下飞机起就发烧头痛。去了唐人街的三个医生,给了他药,但都没用。
他从哪里飞来的?我问。
泰国,朱迪思说。
那么他最初是从哪里出发的?
中国南方。
但是,我依稀记得,泰国和中国没有共同边界。他是怎么去泰国的?
他从中国出发,穿越缅甸,回答道。徒步。一路上的。旅程大约需要两周。
现在他的症状开始变得有意义了。缅甸东部是疟疾的温床,尤其是恶性疟疾,它对氯喹——治疗该疾病的标准药物——具有抗药性。疟疾的潜伏期是两周。如果他在缅甸丛林中被携带疟疾的蚊子叮咬,直到他抵达美国,发烧和头痛才会开始。
然而,要确诊,必须将血液涂片放在显微镜下检查疟疾寄生虫。吸血蚊子只是将疟疾从一个人类宿主传播到另一个宿主;疾病的真正原因是几种微小的寄生虫,它们会攻击人体血液中的红细胞。检查将告诉我们这位年轻人患的是哪种疟疾——当然,前提是我们确实在处理疟疾。我们立刻送了一管血到实验室,但准备载玻片需要30分钟。我们并不是有时间坐着等着;急诊室里还有很多其他患有不那么奇异但同样紧急疾病的病人。
疟疾在美国现在很罕见,但它曾经是致命的。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它才逐渐在美国南部失去控制。几个世纪以来,它曾导致帝国覆灭,军队减员,并使大片土地人烟稀少,尤其是在赤道国家。事实上,它袭击的威力已刻在我们的基因中。镰状细胞贫血症是非裔美国人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它源于携氧并使血红细胞呈红色的血红蛋白基因突变。在现代医疗出现之前,从父母双方各继承一对镰状细胞基因,会注定一个人痛苦地早逝。但只继承一个镰状细胞基因,却能提供一项关键优势:对疟疾的抵抗力更强。换句话说,一种潜在的致命基因之所以繁盛,是因为它为某些人提供了对抗疟疾的保护。不幸的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无疟疾国家中的个体来说,这种突变基因不再有益处,只有成本。
然而,在热带地区,疟疾仍然是一种瘟疫。1991年,约有1.5亿人感染疟疾,近200万人——主要是儿童——死亡。疟疾不仅抵制了现代医学所能施加的一切,甚至还在重新获得失地。20世纪50年代,人们发起了全球性的运动来根除这种疾病及其讨厌的蚊媒。DDT成为了新的奇迹杀虫剂,氯喹成为了新的抗疟疾“魔弹”。然而,35年后,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唯一改变的是,从秘鲁到尼日利亚再到越南,蚊子已经对DDT产生了抗药性,恶性疟疾也对氯喹产生了抗药性。与此同时,即使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免疫学实验室也未能开发出一种有效的疫苗。
作为对现代科技的最后一次嘲弄,对抗疟疾的最终药物仍然是奎宁,正如300年前那样。而古老的预防方法,如使用蚊帐和排干蚊子繁殖的死水池,又重新占据了中心舞台。看来,我们古老的敌人正在向我们发出一个非常现代的警告,关于大自然报复性打击的能力。
然而在这里,我不会让这种可怕的疾病占上风。但在我们治疗病人之前,我们仍然需要证实我的诊断猜测。最后,我们接到了实验室的电话。芭芭拉抓起电话。她只用了几秒钟就传达了消息。
是疟疾!她喊道。而且看起来是恶性疟。
我拦住了另一位值班的住院医生。
来吧,你不会每天都看到这样的载玻片。
我们三个人冲出急诊室,坐电梯到实验室。技术员已经准备好了载玻片。她调整了显微镜。
看,就在视野中间,你可以看到“印戒”。
我的眼睛适应了显微镜,我聚焦在几片淡粉色的血细胞上。其中一个血细胞中间有一个蓝色的圆形带,上面有一个微小的红宝石:单细胞原生动物,名为恶性疟原虫。然而,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这种美丽的杀手所造成的破坏。我也了解到,这也是恶性疟的另一个伎俩。它不仅仅是通过破坏红细胞来施暴。它还会使红细胞膜变得粘稠,导致它们在肝脏、肾脏和大脑等重要器官中聚集,阻碍血液流动。结果通常是永久性器官损伤,或者在脑型疟疾的情况下,死亡。
住院医生轮流通过显微镜观察。当他们只在教科书中见过的图像聚焦时,房间里充满了惊叹声。我们得到了诊断。现在只需要服用适量的奎宁,再加上增强的四环素,这位年轻的访客就能康复了。
离开实验室的路上,我们看起来像一支在达阵区击掌庆祝的队伍。看着那些快乐的脸庞,我意识到我的脸上也一样。我当时想,我们医生真是一群奇怪的人——庆祝显微镜载玻片上微小的污点,并在面对致命病原体时,都发出同样的惊叹的单音节词: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