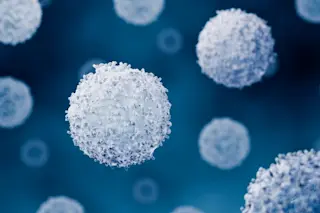编者按:我们网站上最受欢迎的文章之一是由佐治亚理工学院研究员 John Edgar Browning 撰写的,讲述他与 真实吸血鬼社群 的工作,该文发表于 2015 年 3 月。在文中,Browning 讨论了什么是真实的吸血鬼,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研究人员希望从中了解什么。在此,他将详细阐述寻找和研究这个神秘群体人的困难,以及他在过程中学到的经验。
随着克里斯托弗·赖斯的关于新的《夜访吸血鬼》电视改编版的诱人 推文,以及达克·斯托克和 J.D. 巴克将于十月由 Putnam 出版的《德古拉》前传 Dracul 的消息,吸血鬼的话题再次在文学和超自然爱好者的心中萦绕。然而,当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时,会发生什么呢?
对于真实的吸血鬼(或者说,人类吸血鬼),这就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以下内容并非其故事的全部。甚至连一小部分都算不上。但我希望,这足以提供一些见解,并激发好奇心。也许,还能促使我们中的一些人进行自我反思。
撇开吸血鬼小说不谈,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人,他们会饮用 血液——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的——或者从他人那里汲取他们称之为 精神能量。这是一种出于需求而非享乐的行为,通常会极其小心地保护捐献者的安全和舒适。据他们说,这种需求源于他们身体无法自然产生足够的能量。恰如其分的是,他们采用“吸血鬼”这个词来形容自己不寻常的偏好,这种偏好据称在青春期过后开始显现。
吸血鬼采访者
我知道这些,因为在我的研究生研究期间,我曾多次与真实的吸血鬼 面对面 交谈,就像《吸血鬼访谈》中的克里斯蒂安·斯莱特扮演的角色一样。这远没有听起来那么光鲜,也远没有那么容易。真实的吸血鬼并不特别想被找到,而且,如果以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评论区作为衡量标准,我们又能责怪他们吗?
这一切都始于大约九年前,就在我从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一个英语博士项目转到纽约州西部的一个美国研究项目之前不久。当时正值我们一些吸血鬼学者称之为“吸血鬼复兴”的鼎盛时期,在 2009 年 10 月 26 日,我在我的田野调查日志中写下了一段话,至今仍让我回味,既因为它预示着未来,或许也因为它那份天真。
“巴吞鲁日——10 月 17 日,当我参加完在新奥尔良韦克德(Wicked New Orleans [位于新奥尔良的 Decatur St.])的活动后,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店主非常乐意在各方面满足我,并主动提供了信息。在与他交谈的最初五分钟里,他指着店的另一端的一位 40-50 岁的女士,她正在看衣服。“我认为她是个吸血鬼,”他说,“而且我相信她儿子和她在一起。”这时我感到有点尴尬,因为我知道他期望我马上过去和她对质。我没有为我的‘第一次’会这样发生做准备。尽管如此,我还是走过去打断了她,礼貌而简单地说:“打扰一下。”她脸上带着完全的惊讶、恼怒和好奇,转过头看着我的眼睛,什么也没说。于是,我继续介绍自己和我在店里的原因。然后我终于问她,我必须承认这非常尴尬:“你认识(吸血鬼)吗?”我尴尬地笑了笑,她也回以一笑,露出两颗明显的牙齿被磨尖成了门牙。她的回答是:“是的,我可能认识几个。”我赶紧问了她几个问题,想和她聊聊,但直到今天,我都记不清是关于什么的了。然后我给了她我的联系方式,并礼貌地问我是否可以以后再和她聊。虽然我没有问她的联系方式——因为我觉得这太冒昧了——但我确实问了她的名字。令我完全惊讶的是,她只是简单地说:“詹妮弗(Jennifer)。”
“我再也没有见过‘詹妮弗’,也没有收到过她的消息。”
詹妮弗是我的第一个吸血鬼。当时,我确信她将是我的最后一个。
我真是大错特错。
在我写下上述段落几天后,又一次类似的经历促使我再次在笔记中记录,这次我的文字几乎掩饰不住我的兴奋。
“夜晚,沿着 Bonnet Carré Spillway,一条狭窄的 10 号州际公路,濒临庞恰特雷恩湖的西岸,远远望去,可以看到 Shell Norco 精炼厂那哥特式的宏伟钢架和蒸汽喷流,这座建筑在黑暗的广阔空间中,只有零星的几点橙色灯光,显露出它孤寂的身影。他们的——钢、气和微弱的橙色灯光——在我离开新奥尔良和法国区时,在午夜刚过后的几个小时里,已经成为我熟悉的景象,这是我两个月来几乎每周都会重复的仪式。感觉几乎总是一样的:在尖叫喧闹的波本街之后,这条高速公路上的寂静震耳欲聋;我的衣服散发着酒、香烟和美食的气味;我周围的一切都陷入了死寂。但这个十月下旬的夜晚与众不同。今晚,在搜寻了数月之后,我遇到了并与五位居住在新奥尔良的吸血鬼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们是我作为一个外行所处的社群的成员。
这次命运的相遇发生在 Ye Olde Original Dungeon(简称“The Dungeon”),一个位于法国区 Toulouse Street 的夜总会。当我坐在吧台边喝着威士忌酸酒,匆匆写下田野笔记时,那里的调酒师(我已经和他谈过我正在进行的研究)在我耳边大喊,因为上面播放着一首 KoЯn 的歌曲,她在我身后斜眼看着刚进门的一群人,让我去和“那些人”谈谈。我站起来感谢她,赶紧喝完我的酒壮胆,然后带着我的皮质邮差包走到两个穿着一身黑、靠墙站着的年轻人面前。其中一位年轻人,留着长长的黑色马尾辫,看起来三十多岁;另一位,留着短而尖的脏金发,看起来二十出头。在我向后者介绍自己并(大声)解释我试图评估新奥尔良有多少人,以及他们最显著的特征和行为是他们如何自我认同为吸血鬼之后,我简单地问道:“你认识(吸血鬼)吗?”他带着嘲讽的笑容回答:“你在开玩笑吗?”令我惊讶(也松了口气)的是,这对獠牙从这个年轻人英俊的笑容后面显露出来。”
到十二月初,我将 遇到 新奥尔良的近二十多位吸血鬼,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从詹妮弗开始,都教会了我关于“藏身于显眼之处”的宝贵一课。
融入
事实上,我发现人类吸血鬼并非仅仅生活在我们中间——他们就是我们,几乎在每一个细节上。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店员,我们的调酒师,我们的古董商,我们的 IT 人员,我们的朋友,甚至对一些人来说,我们的家人和爱人。我们中的一些人每天都和吸血鬼一起工作,或者在街上与他们擦肩而过而毫不知情。但是,要理解真实的吸血鬼,他们的想法和行为,我们必须理解我们自己对他们的反应。
那个九年前十月的夜晚,在“The Dungeon”昏暗的走廊和哥特式的氛围中,为吸血鬼们提供了相对的安全,但门外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看到这些以及其他真实的吸血鬼被外界贬低,被称为怪胎或精神病人。一位吸血鬼甚至向我透露,她担心如果她疏远的丈夫得知她的“怪癖”,她可能会失去女儿的抚养权。尽管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责任,但那天晚上在“The Dungeon”时,我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我开始研究时,期望看到一群疯子和梦想家,莱斯特的模仿者和吸血鬼小说迷——但我发现的只是普通人,头脑清醒的人,他们大多避免了我们与吸血鬼相关的刻板印象(除了他们偶尔会佩戴的顶级的假吸血鬼牙套)。是我这个傻瓜,而不是他们。
吸取的教训
因此,我改变了方向,并相应地调整了我的预期目标,在此过程中,我更加意识到自己在我跟踪的这些人中的位置。当我这样做时,发生了一些相当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与研究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从我研究的辅助特征发展为更核心的部分。在新奥尔良吸血鬼长老们的月度小组会议上,我开始从我们所处的空间的边缘逐渐靠近内部圈子,起初是他们允许,然后是我自己。实际上,他们后来告诉我,我变得越来越像他们群体中的一员,我也开始有这种感觉。事实上,他们的信任成为我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没有我努力培养的密切关系,我根本无法收集到数据。然而,这种关系来之不易,因为这个社群最近刚刚因主流新闻媒体的信任破裂而受到冲击。
在 2000 年代后期《暮光之城》的狂潮之后,ABC 新闻的 20/20 特别报道了新奥尔良的吸血鬼社群,于 2009 年 11 月 27 日播出,就在《新月》打破纪录的开幕周末的几天后。对当地和更广泛的吸血鬼社群来说,这篇报道并没有准确地描绘他们的生活。它也没有反映出 ABC 引导新奥尔良吸血鬼社群相信会播出的节目内容,该节目本应包括安全进食和伤口护理的演示,以及提及他们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的当地慈善工作。因此,我的“使命”的很大一部分,正如我后来在接受 BBC 和 《华盛顿邮报》 采访时解释的,就变成了仅仅为了纠正这种不公正,通过我自己的记录,来展示 20/20 广播所遗漏的行为和实践。
真正的吸血鬼
通过在五年时间里在新奥尔良和纽约州布法罗收集到的数据,我希望为参与者提供具有地域特色的行为和社会文化见解,最终弄清楚一个地点的吸血鬼与另一个地点的吸血鬼有何不同。我认为地理能够提供关于真实吸血鬼身份复杂性最有价值的信息。最终,不同地点真实吸血鬼的生活成为了我研究的重点。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关于真实吸血鬼的研究著作一直在稳步增长,尤其是在过去 9 年(Joseph Laycock、DJ Williams 和 Mark Benecke 的著作是突出例子),但还没有一项研究试图在地方层面探索这种身份,以确定地理和地方文化是否发挥了作用。我的发现最终表明,新奥尔良的吸血鬼自我认同与真实吸血鬼在布法罗的身份塑造形成了鲜明对比。特别是,当地的文化规范似乎很重要——在布法罗的街道上戴着吸血鬼牙套走出去不像在新奥尔良那么容易。更令人震惊的是新奥尔良地方社群的突出性,许多吸血鬼组织成了“家族”,拥有长老和成员的等级制度。相比之下,布法罗这个似乎没有像法国区那样集中(或聚焦)社区的城市,似乎更倾向于独立和个性。
当我努力真正理解(而不是进一步耸人听闻)这个神秘的社群时,我发现真实吸血鬼身份最终实现的,是一种自我赋权。我称之为“反抗文化”,它在世界各地其他边缘化社群中都有体现。真实吸血鬼身份是那些可能不适合正常社会框框的人们构建身份并面对一个常常排斥而非接纳的世界的方式。虽然我的研究努力揭示了压迫性制度内如何发展出叛逆社群,但也唤醒了它最熟悉的对手——那些将自己经验之外的事物边缘化的人。对外界来说,真实吸血鬼饮用人类血液或能量并非他们最严重的罪行,而是他们作为一种骄傲、活生生的对正常的批判。
在好莱坞光鲜的世界里,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我们害怕黑暗的地方;我们害怕未知。但对于这些真实的吸血鬼来说,在阴影中、在匿名中存在着安全。也许他们所谓的阴森本性,仅仅是我们自身黑暗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