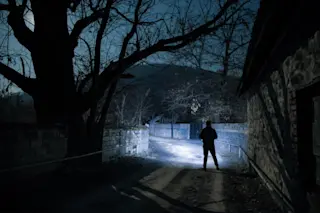我们一群人,有些是科学家,但大部分不是,刚刚在纽约科学院共进晚餐。我们吃得很好——烤三文鱼配芦笋,一份绿叶沙拉,杯装绿茶冰淇淋,还有酒和咖啡供想喝的人享用——然后坐下来听今晚的讲座。演讲者是来自耶鲁大学的琳达·巴托舒克,一位人类味觉专家。她递给我们每人一小包东西,看起来像圣餐薄饼。那是一小片滤纸,浸满了被称为丙基硫氧嘧啶的化合物,在味觉界被称为PROP。我们被指示把纸片放进嘴里。当我的唾液浸湿它时,一股令人不快的苦味随之而来。我的邻居也做了一个表示“呸”的表情。然后巴托舒克要求举手。我们中有多少人尝到了味道?多少人没有尝到?当然,巴托舒克知道结果:通常,四分之一的听众什么也尝不到。这个例行演示总是能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当两个问题都有人举手时,人们的下巴都惊得松弛下来。为什么同一种东西对有些人来说是无味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如此令人不快的苦涩?如果我们相信感官能反映真实世界,那么这个答案似乎令人不安:我们可能认为今晚都吃了同样的晚餐——但我们并不都生活在同一个味觉世界里。
事实上,研究人员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怀疑这一点,当时一位化学家正在制作一批名为苯硫脲(PTC)的化合物,一团晶体飞散到空气中。一位实验室同事,一定吞食了一些空气中的晶体,注意到它们有多苦。那位惊讶的化学家,他自己什么也尝不到,成为了第一个描述对这种苦味化合物“味觉失明”的人。当然,对PTC或其化学近亲PROP的味觉失明可能只是一种科学奇闻——所谓的“无味者”确实对其他类型的苦味有反应。但事实证明,无味者对所有类型苦味的反应强度都低于有味者,而人们尝到PROP的程度可以作为他们总体味觉能力的一个普遍指标。
从家族研究来看,无法尝到PROP是遗传性的,很可能是由于隐性基因。这与巴托舒克发现的“存在一部分对苦味超敏感的PROP尝味者”非常吻合。她称他们为“超尝味者”。观察这三组人,你会看到隐性基因所预期的模式。大约25%的PROP测试者尝不到味道,这与两个隐性基因一致;50%是尝味者,这与一个隐性基因和一个显性基因一致;而25%是超尝味者,这与两个显性基因副本(分别来自父母)一致。这种分布略有性别差异。女性中超尝味者多于男性,这可能是因为苦味在自然界中代表着危险,而进化曾偏爱拥有更优越的毒素检测系统的母亲。
巴托舒克说,令人着迷的是,舌头的解剖结构揭示了这些群体之间的差异。尝味者比非尝味者拥有更多的味蕾,而超尝味者拥有最多。因为味蕾周围环绕着不仅感知味觉,还感知疼痛和触觉的神经末梢,所以超尝味者拥有更丰富的感官味觉体验,这也许并不奇怪。苦味更苦,咸味更咸,酸味更锐利,有些甜味更甜。脂肪感觉更油腻,牙龈更厚,酒精和辣椒燃烧感更强烈。巴托舒克本人也是一名非PROP尝味者,她说,非尝味者的口腔内部“与超尝味者相比,是一个非常小的世界”。但由于超尝味者的感官领域如此强烈,他们可能会避免强烈的味道——尤其是像葡萄柚、咖啡、啤酒或西兰花这样的苦味——因此实际上缩小了他们的饮食范围。
我对她的发现很感兴趣,说服巴托舒克让我参观她的实验室,进行为期两天的味觉沉浸式体验。其中一个实验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名外科医生通过耳朵注射麻醉剂,以麻痹一条通往舌头的颅神经。(“你确定要这么做吗?”一位朋友问道,想象着我脸上某种不对称的瘫痪。)巴托舒克说:“如果你够幸运,可能会产生‘味觉幻象’,”一种没有明显原因出现的味道。我突然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有一种金属味悄悄袭来,仿佛铁以某种方式渗入了我的口腔。这是一个让我直面我的幻象的机会。
琳达·巴托舒克的实验室位于耶鲁大学医学院综合大楼一栋红砖建筑的二楼。它与其他任何设备齐全的实验室没什么两样,除了那些食物器具——糖豆罐、硬糖、一瓶又一瓶的塔巴斯科辣椒酱、墨西哥辣椒酱和其他辣酱。然后还有放大的舌头照片。这些被拍摄的舌头非常独特,有些图案稀疏,有些则布满了小突起。
巴托舒克是一位和蔼可亲、外向大方,六十出头的女士。她喜欢开怀大笑。然而,今天早上,她全身心投入工作。经过几分钟的随意交谈后,她像关灯一样,瞬间集中了注意力。研究味觉是一项棘手、耗时的工作。而且,要引导志愿者完成一系列测试——而不是像对老鼠舌头放置电极或在培养皿中操作细胞那样——并没有让这项任务变得更容易。尽管她不是医生,巴托舒克也调查由医生转诊给她的患者的严重味觉问题。
首先,巴托舒克进行了一次检查——对我舌头进行了一项空间测试——通过一次只在一个区域涂抹味道。她用棉签作为刷子,蘸取不同浓度的氯化钠溶液,将盐溶液涂抹在我的舌头上,并要求我以0到100的等级评价其强度。然后她涂抹蔗糖以测试我的甜味感,柠檬酸以测试酸味,奎宁以测试苦味。她瞄准的是舌头前部、两侧和后部的小突起,称为乳头。前部的乳头被称为“菌状乳头”,因为它们看起来像蘑菇。据说像叶子的“叶状乳头”则出现在靠近后部两侧的一系列红色褶皱中。在很靠后的位置,几乎在某些人的喉咙深处,是“轮廓乳头”,它们像被护城河环绕的圆形塔楼一样,呈倒V形分布在舌头表面。
我们把乳头上的隆起称为味蕾,但它们更像是标记味蕾位置的X:我们的味蕾,大部分都嵌套在这些隆起中,而且太微小了,肉眼无法看到。特殊的受体细胞从这些微小器官中伸出,捕捉落在口腔中的甜、咸、酸、苦分子。当美味分子刺激受体时,它们反过来刺激舌头内部的神经末梢,信息沿着神经反弹到大脑。
“所以这本质上是针对你口腔中神经的神经学测试,”巴托舒克解释道,“我正在将溶液涂抹在舌头我知道哪些神经支配该组织的地方,我想让你评估你感知到的东西。”
她所指的神经是两条主要的味觉颅神经,它们从大脑延伸到舌头的前部和后部。当她将甜味涂抹到菌状乳头时,她知道她正在刺激前部的味觉神经:鼓索神经。当她将甜味涂抹到轮廓乳头时,她正在测试舌头后部的味觉神经:舌咽神经。此外,通过涂抹纯酒精或辣椒素(辣椒中的灼热化学物质),她可以测试触觉神经,即三叉神经,它向乳头发送细小的、对疼痛敏感的纤维。这就像她在检查一个保险丝盒,系统地检查我味觉系统的开关和线路。
当巴托舒克继续在我的舌头上点缀各种味道时,我突然明白了那些教科书上舌头味觉分区图的不准确性——那些图显示甜味集中在舌尖,咸味和酸味在两侧,苦味在舌根。我们显然在舌头各处都能尝到它们。“舌头味觉分区图是错误的,”巴托舒克直截了当地说。
巴托舒克说,从我对味觉,尤其是苦味的评价来看,我是一个相对“强反应者”。“你肯定不会有非尝味者的舌头。问题只在于你有多少菌状乳头。”一个典型的非尝味者的舌头只有很少的菌状乳头,一个超尝味者的舌头则有很多,而一个中度尝味者的舌头介于两者之间。
为了让乳头更清晰可见,巴托舒克用植物染料把我的舌头表面染成了恐怖的蓝色(它把保持粉红色的菌状乳头与其他蓝色的舌组织区分开来)。然后,由于舌头肌肉容易抽动,我被要求把舌头夹在两块透明的小塑料板之间。一台摄像机对准了这套装置,突然,我的舌头放大10倍的图像跃上了视频屏幕。
“你的舌头上有一块区域缺少菌状乳头,”巴托舒克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表明三叉神经可能受损。最可能的原因是轻微的牙科损伤。你有没有打过麻药正好击中神经的情况?”
我不记得了。
她在显示器上数着菌状乳头。“很难确定你是中等尝味者中的高敏感者,还是超尝味者中的低敏感者。你处于临界线上,是那种我们需要基因测试的人,这正是当前非常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你看到这里,看这些菌状乳头的密度,”她指着我舌头右前方的一个区域,那里的菌状乳头比其他地方紧密得多。“那里很高,更符合超尝味者舌头的特征。”
然后她指向屏幕上散布的点。“在我的舌头上——我是一个非PROP尝味者——菌状乳头会像波尔卡圆点一样,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但请注意这边,”她指着我舌头左半边的一片空白区域。“我们看不到很多。这边应该有更多的菌状乳头。”
接着,巴托舒克思索着我没有菌状乳头的那一块。“你的三叉神经显然出了问题,”她说。在人类中,菌状乳头的维持并非由前方的味觉神经负责,而是由三叉神经负责。“这是牙医在进行大量钻牙工作时试图麻痹的神经。而且用麻醉剂注射时很容易不小心刺穿它,”她补充道,“这可能发生在你小时候,很久以前。”
通往口腔的神经容易受到多种损伤:牙科手术、耳部手术、头部撞击、挥鞭性损伤、常见病毒感染等。出于解剖学原因,支配舌头前部的味觉神经——鼓索神经,承受了病毒感染的主要冲击。当神经在大脑和舌头之间穿行时,它正好从鼓膜(tympanic membrane)下方经过。因此,在耳部感染或影响耳部的上呼吸道感染期间,病毒有时会侵入这条味觉神经,使其暂时——甚至永久——失效。
幸运的是,我们的味觉系统具有补偿机制。通常,舌头上的神经会相互抑制。例如,舌头前部的味觉神经会抑制舌头后部的味觉神经,反之亦然。如果前部的神经受伤,那么对后部神经信号的抑制就会解除,从而弥补不足。
“所以当前方的味觉减弱时,后方的味觉会增强,”巴托舒克说。她补充说,我们维持味觉的系统运转得如此良好,以至于“许多有局部味觉丧失的人,在我们测试他们之前,都没有意识到。”但有时会有代价。一条神经的丧失可能导致被解除抑制的神经出现夸张的反应,甚至唤起似乎没有真实世界原因的感官体验。
巴托舒克说,这些“味觉幻觉”是“在没有刺激的情况下产生的感官”。它们出现在所有四种经典味觉中,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也出现在我们解释为金属味的酸涩矿物味中。最常见的“解除抑制”幻觉出现在舌头后部,当前方的味觉神经受到某种损伤时。我的金属味访客倾向于在我感冒或流感鼻塞时出现,这可能是因为入侵的病毒进入了鼓索神经。
通过精心瞄准的麻醉剂注射来模拟鼓索神经损伤,可以实验性地诱发这种幻觉。巴托舒克回忆说,这项技术是偶然发现的。她和耶鲁大学医学院的耳鼻喉外科医生约翰·奎顿一起从一个讲座出来。“约翰提到一个病人,他的鼓索神经因为耳膜注射而麻醉了。我说,‘你能做到吗?’”从味觉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种注射比传统的舌神经阻滞或牙科注射有了巨大的改进。与阻滞不同,耳膜注射不会麻痹触觉。而且它只麻痹一条味觉神经——支配舌头前部的那条,并且只在注射侧。一项合作由此诞生。
奎顿的手法稳健而灵巧,举止沉着冷静。他的专长是手术切除听神经瘤,这是一种在大脑旁边生长的肿瘤,最终会累及味觉神经。第二天早上,当他给我注射右耳时,我感觉很放心。针头刺入耳道内的皮肤,靠近神经从耳膜下方经过的地方,然后注射的利多卡因冲刷着神经。经过短暂的恢复期后,巴托舒克用盐溶液测试我舌尖的右侧。我能感觉到棉签在舌头上轻微的摩擦感,以及水分带来的些许凉意,但没有味道——一点也没有。神经完全麻痹了,所以巴托舒克开始忙着进行她的测试。“喝点水,”她指示道,“如果你会出现幻象,这通常会诱发它。”没过多久。
我的幻象逐渐浮现,仿佛需要时间来整合所有部分。它先是作为酸味出现在我口腔左侧的后部,然后特征性的金属音符慢慢充盈。考虑到这种含铁的味道通常会破坏食物和饮料,我感到奇怪的愉悦。当然,在识别熟悉的事物中,在理解带来的掌控感中,都有一种愉悦。但这种愉悦也来自于纯粹的惊奇。
“注意到金属味是与麻醉侧对侧(相反)的吗?”巴托舒克说,“这非常重要,因为它必然是大脑在起作用。舌头的左右两半神经支配是分开的。来自两半的信号第一次相互作用是在大脑中。所以当我们在一侧做某事而另一侧受到影响时,我们得出结论它发生在大脑中。”
我的幻象时隐时现,最终随着麻醉药效的消失而彻底消退。与此同时,巴托舒克还有别的招数。她向我展示了大脑如何利用触觉来“定位”口中的味觉。她用刷子在我舌尖周围涂抹盐,从我右侧没有味觉的一边移到我左侧有味觉的一边。果然,直到盐碰到左侧,我才尝到味道。但当她反向操作,从左到右涂抹盐时,发生了一些反直觉的事情。我在左侧真实尝到的盐味,竟然涌向了右侧——而实际上,右侧根本尝不到任何东西。我的大脑在右侧产生了持续的味觉幻觉,因为它在那里持续接收到触觉信号。正如巴托舒克所说:“味觉感受沿着触觉路径移动。”眼见为实。
当然,我们通常所说的味觉,很大一部分是由嗅觉组成的,也就是食物在我们口中的香气。让香蕉有香蕉味的不是甜味;而是它的气味。然而,当我们吃香蕉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气味正从我们鼻子后面的烟囱里向上散发。感觉就像我们在我们口腔这个巨大的实验室里感知它,作为整体风味的一部分。这里似乎又是大脑在起作用,通过触觉和味觉将食物香气投射到口腔。
康涅狄格大学的味觉研究员瓦莱丽·达菲(Valerie Duffy)与巴托舒克合作,想出了一个简单的演示,说明味觉对于将食物气味固定在口中是多么关键。我的舌头右侧麻醉后,我将舀一勺香蕉酸奶,在口中搅拌,然后告诉巴托舒克,香蕉味——也就是香气与味觉的组合——是否在我口中的某个部位更强烈地传来。果然,我无法在舌头没有味觉的一侧很好地感知香蕉味——但在有味觉的一侧,我清晰响亮地感知到了香蕉味。“是的,你成功了,”巴托舒克说。然后我们结束了这一天。
像这样的味觉幻象实验表明我们是用大脑来品尝的。但是当我们进食时,大脑不仅仅是将味觉、嗅觉和触觉融合在一起,为我们提供食物的复杂风味和质感体验。它还会回忆起与我们正在吃的食物相关的愉悦和不悦。“甜味是一种深刻的生物学愉悦,”巴托舒克说。它在自然界中预示着安全的卡路里,这种愉悦可能 innate。但大多数进食的愉悦是习得的,通过经验学习而来。“美食家享受他的昂贵巧克力慕斯是否比我享受我的好时巧克力棒更多呢?我不这么认为。我非常喜欢我的好时巧克力棒,”巴托舒克带着一声富有感染力的大笑说道。
所以,当谈到快乐时,我们是超级品尝者、中等品尝者还是非品尝者,可能并不重要。我们的大脑会努力将快乐校准到我们特定的化学感官组合,因为它希望不断摄入卡路里,以确保我们生存。我们的大脑会确保我们最大限度地享受食物——我们的最大限度。这真的是“各有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