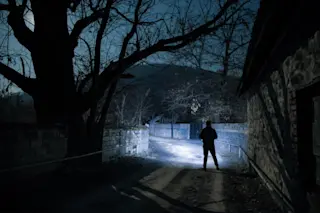十年前,弗雷德·阿耶差点在海上风暴中丧命。当巨浪击中他担任工程师的金枪鱼船时,一根坠落的横梁压碎了他的右臂。船离陆地还有五天。他的船员设法止住了失血,并让他活到上岸,但为时已晚,无法保住肢体。
十年后,阿耶坐在椅子上,上半身赤裸。他肘部以下的右臂实体早已不复存在。然而,阿耶大脑的实体却尚未被说服接受这个事实。
“看看你能不能伸出右手抓住这个杯子,”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大脑与感知实验室负责人、神经科学家维拉亚努尔·拉马钱德兰说。阿耶用他的残肢指向桌子上几英尺远的一个杯子。
“你现在感觉如何?”拉马钱德兰问。
“我感觉到我的手指正握着杯子,”阿耶说。
“好的,再试一次,”拉马钱德兰说。这次,当阿耶开始动作时,拉马钱德兰迅速将杯子移得更远,以观察阿耶想象中的手臂是否具有真实肉体的局限性,或者能否根据需要伸长以完成任务。结果令他震惊。
“哎哟!”他的病人痛苦地咧着嘴说。“你为什么那样做?”
“做什么?”
“感觉你把杯子从我手里抢走了。”
弗雷德·阿耶对那个杯子出奇顽固的抓握,是幻肢症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即截肢者的虚空肢体和事故受害者的神经坏死肢体产生生动感觉的感知。一名失去双腿的老兵抱怨脚背上无法抑制的瘙痒感漂浮在空中。一名双臂截肢者报告说,幻肢在他的行走过程中会随步伐正常摆动。阿耶是一位狂热的网球运动员,他设法将比赛改为左手,但当他的幽灵般的右臂也坚持握拍时,他的发球动作就会遇到麻烦。拉马钱德兰的另一位病人,一位天生就没有双臂的年轻女性,在激烈的讨论中,她感到她的手臂随着她提出的观点而做出手势。几乎所有截肢者都会经历这种感觉。
更令人不安的是疼痛。患者抱怨灼烧感或刺痛感、可怕的肌肉痉挛,或者感觉手指被扭曲变形或被推穿手掌。有时,一个曾经困扰真实脚部的嫩足鸡眼或碎片也会困扰幻肢,而且位置完全相同。手臂截肢者曾说,他们有时会感觉指甲被拔掉了。
“前几天晚上,疼得我简直尖叫起来,”80岁的布莱恩·希恩说,他因糖尿病失去了双腿的下半部分。“你只能学会忍受它。”
有些患者显然没有忍受,他们选择了自杀,以摆脱纯粹在幻肢中感受到的折磨。
“鸦片类药物和其他针对疼痛系统的药物都没用,因为它们不再是引起疼痛的原因了,”范德堡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乔恩·卡斯说。“那是某种其他系统,无意中发出了疼痛信号。”
自幻肢痛在十九世纪首次被描述以来,研究人员一直在试图弄清楚这些神秘感觉在触觉系统中的起源。当肢体被移除时,残肢中被切断的神经——以前从皮肤传递触觉、温度和疼痛信息的神经——在它们的切口末端形成结节,称为神经瘤。幻肢痛的经典解释是,这些截断的神经末梢继续将冲动沿脊髓发送到大脑。切断神经瘤上方或进入脊髓的神经似乎能带来一些缓解,但只是暂时的。在脊髓内进行手术也无济于事。几个月或几年之内,幻肢的痛苦就会再次出现,痛苦的证据表明,这种感觉的真正来源必须位于触觉通路的更上方,在大脑本身内部。
在追逐幻肢的过程中,神经生物学家因此得出了一个确凿的启示:触觉,以及它所带来的物理世界,更多地与我们头脑中的活动有关,而非我们的指尖。这些虚幻的感觉甚至可能即将揭示大脑最严密保守的秘密之一。如果拉马钱德兰和卡斯等神经科学家是正确的,那么幻肢这种奇异现象为我们如何与周围世界互动并从经验中学习提供了被敏锐放大的视角。
“我们正在探索通往神经生物学圣杯的新途径,”拉马钱德兰说。“即理解学习和记忆的物理基础。”
当皮肤中的神经末梢,即感受器,接收到刺激——丝绸的轻抚或针的刺痛,冰冷的水流或温暖手的握持——由感受器产生的生物电冲动通过脊髓传播到脑干中称为突触的连接处。进一步的突触将信号发送到大脑中一个重要的中继站,称为丘脑。从那里,冲动被传送到体感皮层。这个感觉的投射屏幕排列得像一个法国花园一样整齐。源自拇指的神经冲动刺激皮层中专门负责拇指的区域,该区域紧邻响应食指神经的区域,依此类推。手臂皮层紧邻肩部皮层,肩部紧邻躯干,只有少数地形上必要的奇特配对。(例如,脚趾将其信号放置在来自生殖器的冲动旁边。)皮肤区域活跃的感受器越多,其在感觉皮层中的分配就越大。(在我们人类中,近四分之一的皮肤皮层专门用于我们高度敏感的手。)就好像有一个微小、有序但扭曲的自身版本——一个小人——勾勒在大脑的褶皱表面上。
在寻找幻肢根源的过程中,研究人员遇到了这个一丝不苟排列的小人。它向他们展示了神经科学的一项基本信条。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神经科学家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除了婴儿时期灵活生长的关键时期,大脑的神经元回路是硬连接的,其连接像房屋的电气系统一样固定不变。关键期理论主要来源于戴维·休贝尔和托斯坦·维瑟尔的实验,他们于1981年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休贝尔和维瑟尔发现,在小猫神经生长关键期,如果用眼罩遮住它的一只眼睛,会导致那只眼睛永久失明。当眼睛被遮住时,来自功能正常眼睛的输入会接管被剥夺眼睛的视觉皮层分配区域。一旦眼罩被移除,失明的眼睛就无法恢复,因为此时重新定向输入已经太晚——它们已经固定下来。其他关于眼睛、耳朵和触觉接收的研究也支持了成年大脑是严格组织化的观点。
当然,皮层中的感觉小人是那个硬连接大脑的一部分。那么,它怎么可能成为幻肢的来源呢?在硬连接系统中,死亡的部分就是单纯的死亡;一旦皮层不再接收来自截肢或瘫痪肢体的神经冲动,分配给该肢体的皮层区域就应该永远像电话线被切断的电话一样沉寂。因此,在将幻肢追溯到大脑本身之后,大多数临床神经生物学家都在半解释和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迷雾中失去了它的踪影。正如两位研究人员最近在《加拿大医学会期刊》上总结的那样,这种感觉“可能是精神性的,有证据表明某种与失去身体一部分的可怕创伤相关的强迫性神经症。”
他们写道:“我们认为,采取一般性的心理治疗措施可能会有益。”换句话说,就是心理辅导。
通过这个僵局的可能通道——或许能瞥见其深处闪耀的圣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迈克尔·默兹尼奇及其与范德堡大学的乔恩·卡斯等人首次探索。默兹尼奇和他的同事们想看看当皮层皮肤地图被剥夺正常输入时会发生什么。在一个实验中,他们截掉了一只成年猴子的一根手指,等待了几周,然后记录了到达猴子皮层地图相关部分的信号。根据关键期理论,这个缺乏触觉感受器输入的皮层区域会像被租客遗弃的办公楼一样死气沉沉。然而,研究人员发现,当触摸缺失手指旁边的两根手指时,该区域内的神经元就会放电。显然,来自相邻区域的神经冲动正在被重新映射到空置区域——这表明成年大脑比大多数科学家想象的要灵活得多。
“一直以来,主流观点中都有一个反对的声音,怀疑大脑可以做出这种调整,”默兹尼奇说。“我们亲眼目睹了它们的发生。”
然而,默泽尼奇和他的同事们所看到的重映射量仍然可以用不威胁硬连接大脑教条的方式来解释。猴子感觉皮层相邻区域的神经冲动只侵犯了一到两毫米。这恰好是一根神经轴突的长度,它是神经细胞的“工作端”,与从丘脑到感觉皮层的其他神经建立连接。当默泽尼奇和他的同事们切除猴子的两根手指时,皮层重映射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大。因此,最可能的解释是,轴突现有的、未使用的分支已经跨越皮层区域的边界进行了接触。当一根被截肢的手指的正常输入停止时,这些休眠连接被揭示出来,新的冲动被发送到空置区域——但仅限于单个轴突可以到达的范围。换句话说,你可以教一个“老大脑”新技巧,只要你使用预先存在的硬连接回路来进行学习。
1991年,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蒂莫西·庞斯宣布了新的证据,这些证据既支持了梅泽尼奇的观察,又彻底推翻了任何对这些观察的简洁解释。庞斯的研究偶然利用了臭名昭著的“银泉猴”,这是一群猕猴,在12年前的一次无关实验中,它们的一只手臂的感觉神经在进入脊髓的地方被切断。这些猴子成为了一场著名的动物权利审判的焦点(参见《发现》杂志,1992年1月)。当伦理问题在法庭上激烈争论时,这些猴子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无法用于研究,但状况恶化到法庭同意其中四只被安乐死会更好。然而,在它们被杀死之前,庞斯被允许在它们的皮层中植入电极,以观察12年的休眠对曾经专门接收来自断开肢体冲动的大脑地图部分造成了什么影响。他预计会发现梅泽尼奇结果的证实:来自两个相邻感觉区域(在这种情况下,是面部和躯干)的一两毫米的侵犯。当然,这种侵犯应该不超过单个神经轴突所能达到的长度。
“我们惊呆了,”庞斯说。“我们发现,面部区域完全侵入了相邻的皮层,而不是来自两侧的一点点侵犯。在这四只动物中,当我们刺激面部时,整个手和手臂区域都做出了反应。”
实际上,整个触觉地图的三分之一——超过半英寸的皮层——已经改变了它的归属。由于没有来自麻木肢体的指令,它将自己的命运与面部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大规模的神经重组,在硬连接的大脑中是不可想象的。来自相邻轴突休眠分支的输入不可能是答案,因为它们不够长,无法在如此广阔的灰质区域建立连接。
“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真是一个谜,”庞斯说。“我们还没有解释它的机制。”
考虑到猴子的神经被切断已经过了好几年,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神经元之间实际上已经长出了新的连接,从面部皮层直接跨越了整个空置区域。然而,考虑到成年大脑从未被发现能够生长任何新的神经元连接——它们只会失去连接,这种皮层组织的大量生长似乎不太可能。另一方面,对猴子的实验表明,新的轴突可以从脊髓中已有的细胞中萌发。庞斯推测,猴子皮肤地图中观察到的巨大变化可能是由于触觉通路更下方、更受限制的地方发生的相对适度的生长所致,在神经冲动到达皮层本身之前。
一个明显的狭窄点是丘脑。在这个中继站内,从面部到皮层的神经冲动必须穿过同时接收来自手和手臂输入的区域。通常,面部通路穿过丘脑的手臂和手部区域,不建立任何连接,就像一条公路穿过高速公路却没有交汇处一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这些面部神经穿过肢体在丘脑部分的小范围局部萌芽,也可能产生新的突触——并将整个面部输入投射到皮层地图的手臂和手部区域。庞斯更喜欢用将您的电话线连接到邻居家的比喻。在这个受限的局部层面,不需要太多电线就可以将您的电话呼叫发送到他们整个长途网络中。
无论其最终解释如何,庞斯在银泉猴身上目睹的公然重映射,在日益壮大的相信大脑可塑性的神经科学家群体中激起了一股兴奋的浪潮。其中受到启发的是拉马钱德兰。几年来,他一直在探究视觉系统盲点的奥秘。每个人在每只视网膜上都有一个小的自然盲区,偏离中心约15度。然而,我们没有人会带着视觉领域中相应的黑洞行走,因为大脑会用周围背景的信息填充缺失的部分。中风或头部受伤的患者可能会有更大的盲点——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会自动用背景中的细节填补空白。拉马钱德兰和其他人强烈怀疑,这种神经戏法是通过将通常传递到视觉皮层相邻部分的冲动进行重映射来实现的。
当拉马钱德兰看到庞斯的论文时,他开始思考,在幻肢症患者的触觉系统中,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填充。他招募了一些截肢者来帮助检验他的假设。其中一名志愿者是一位名叫维克多·昆特罗的少年,他四周前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左臂。当维克多蒙着眼睛坐在椅子上时,拉马钱德兰用棉签轻轻触摸他的脸。
“你感觉到哪里了?”他问道。
“你正在摸我的脸,”少年说,“但我也觉得我的左拇指发麻。”
“这里呢?”拉马钱德兰问,抚摸着维克多上唇上方的皮肤。
“你摸到了我的食指。”
“现在呢?”棉签移到了维克多的下巴。
“我的小指。”
拉马钱德兰继续他的探测,触摸着病人的胸部、腹部和他完好的手臂上的各个部位,幻肢没有任何反应。只有当他将棉签触及维克多残肢上方的一个区域时,那种奇妙的感觉才重新出现。
“那里,我的拇指又麻了……现在是我的食指……我的拇指球……”
实际上,拉马钱德兰的棉签已经找到了维克多虚幻之手的物理、肉体实质。从神经学上讲,这只手根本没有缺失——事实上,它现在是两只左手,一只细致地排列在他的下半脸上,另一只则在他的肩膀下方摆动着手指。在映射到维克多体感皮层中的版本中,这两个区域恰好与以前接收来自截肢手臂信息的区域接壤。这表明,庞斯在他猴子身上目睹的那种完全、有序的接管,在幻肢患者身上也确实发生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入侵是来自两个相邻区域的侧翼攻击,而不是仅仅来自面部。
拉马钱德兰对其他六位病人进行了类似的实验。所有病人都至少拥有一个重塑后的身体缺失部分,这种转移以惊人的有序性和生动的清晰度完成。另一位病人,他的右臂和部分肩膀都被移除了,当他感觉到拉马钱德兰的棉签在他脸上描绘出他完整的缺失前臂时,他感到惊讶——肩膀塞进了下颌关节,肘部刻在了下颌肘部般的弯曲处,手和手指伸向他的下巴。截肢区域的另一个版本映射在他的躯干上,躯干非常敏感,以至于在某个点轻触一根体毛,他的幻肢肘部就会感到剧烈的刺痒。在与另一位病人合作时,这位病人的左臂在一次车祸中神经被从脊髓中拉出后,完全失去了感觉,拉马钱德兰不小心从棉签上滴落了一些温水。水顺着病人的脸流下,流到了他的衣领下。
“嘿,那真奇怪,”病人说,“感觉你真的在往我手臂上倒水。”
或许最令人惊讶的观察是重映射完成所需的时间之短——在维克多·昆特罗的案例中,仅仅四周。对拉马钱德兰来说,如此迅速的输入重映射使得庞斯的萌芽假说不太可能,因为即使是适度的新神经组织生长,时间也根本不够。相反,他认为,隐藏的回路必须已经存在于神经线路中,允许一个皮层区域扩展到相邻区域。只要从触觉感受器接收到正常、更强的输入,这些回路就处于休眠状态。但当感受器突然关闭——例如,当肢体被截肢或瘫痪时——潜伏的回路就会被揭示出来,整个肢体皮层就会开始唱它邻居的调子。
“这就像是不同回路之间正在进行一场竞争,”拉马钱德兰说,“最强的回路宣称拥有整个争议领地。”
如果他是对的,那么“揭示假说”可能蕴含一些治疗智慧。通常,中风后失去手部功能的患者会被鼓励尽可能多地锻炼手臂,以促进相邻手部感觉的恢复。但如果“揭示”是皮层重映射的秘密,那么从逻辑上讲,手臂应该被固定,其输入尽可能地被抑制,以使手部虚弱的回路有机会重新建立其对皮层区域的昔日霸权。
然而,庞斯坚持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存在能够侵入整个皮层区域、等待被揭示的潜在回路。“这就像说,当你的电力中断时,你的备用发电机就会启动,”他说,“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备用发电机。”
像庞斯一样,拉马钱德兰承认,目前他关于重映射发生方式的首选解释不过是猜测。但他仍然充满信心。“我们现在知道幻肢的来源在大脑本身,”他说,“与失去肢体相关的皮层远非大脑中的赘生物,它活得很好,继续向上游系统传递信息。这些信息可能不再源自肢体本身,但大脑的其他部分并不知道这一点。”
那么,大脑的其他部分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被皮层中的输入转换所蒙蔽了吗?在幻肢中,系统更上游发生了什么?蒂姆·庞斯在他的猴子身上观察到大规模重映射的精确区域——简称初级体感皮层(S1)——实际上只是皮层中一系列十几个或更多日益复杂的皮肤地图中的最初接收站。每一个都提供了塑造和细化从更下方传入的感觉的机会——以及输入重新映射的另一个机会。这条触觉通路与另一系列皮层地图并行——这些地图响应肌肉和关节中的感受器——管理本体感觉,这种感觉让您了解四肢和其他身体部位的位置。触觉系统和身体位置系统都与控制肌肉运动的皮层区域进行交流,它们共同向大脑的一个区域(顶叶)输送信息,该区域负责身体意象和识别。该区域的脑损伤可能导致一种称为单侧忽视的病症——一种与幻肢症截然相反的奇怪镜像。患者不是从一个不存在的附肢感受感觉,而是否认他身体中一个功能完全正常的部位属于他;他可能会顽固地只刮脸的一侧,或者推开莫名其妙地附着在他自己身体上的陌生人的腿。
拉马钱德兰怀疑,沿着这条本体感觉通路上的区域也必须进行重映射,才能出现幻肢现象。但这能否解释为什么弗雷德·阿耶会感到一阵剧痛,当杯子从他只存在于脑海中的手中被夺走时?根据这位神经科学家的说法,阿耶的不适可能可以用大脑中运动控制中心的参与来解释,这些中心正在向缺失的肢体发送信号,命令它抓住杯子。在没有来自手本身的本体感觉反馈的情况下,运动指令几乎淹没了通路,以比正常情况更强大的力度发出指令——抓住杯子!同样的现象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位天生就没有双臂的年轻女性在争论中对她手臂所做的生动手势异常敏感。或者也许不能。
“她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在22年从未收到手臂反馈后,她仍然感觉到幻肢,”拉马钱德兰说,“我们还不能解释所有事情。”
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神经心理学家罗纳德·梅尔扎克认为,这种全面的解释只能通过对广泛神经矩阵回路的理解来实现,这些回路超越了感觉通路,延伸到大脑的边缘系统,而边缘系统对情感和动机至关重要。“重映射对我来说很好,”他说,“但你不能只关注初级体感皮层,就好像所有警钟都在那里敲响一样。它只是画面的一部分。”
然而,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它正是令人深感兴趣的部分。谈论庞大的神经元网络互动是众所周知的空谈;瞥见这样一个网络的一部分正在物理重组本身是无价的新奇事物。当然,主要问题是为什么。
“我怀疑把他们缺失的胳膊映射到脸上,或者遭受极端的幻肢痛,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卡斯说,“但这些事情表明,成年大脑的灵活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它们是大脑可塑性的结果,这种可塑性却对人不利。”
卡斯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大脑重构自身的能力可能正是让人们从头部受伤中恢复的原因,头部受伤会使大脑中的轴突断裂并切断关键连接。在一段混乱期之后,正常功能恢复——大概是因为大脑其他相邻区域能够接管死神经的工作。神经元损失实际上是一个自然过程,在成年生活中持续进行,无论你是否头部受到重击。在某个年龄之前,也许我们的大脑通过重新将皮层中仍然活跃的区域分配给以前由失效回路处理的任务,来应对自身的持续退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通过使用替代回路来保持其强大。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随着年龄增长仍然保持精神活跃的人似乎能更长时间地保持他们的敏锐度。
“一直以来都有‘不用则废’的民间说法,”卡斯说,“这项工作为这种信念提供了理论依据。”
最宏伟的希望是,对大脑可塑性的理解最终将解开学习和记忆的奥秘。当一个网球运动员练习新的反手击球或一位钢琴家掌握奏鸣曲时,他们的大脑中必然会发生一些物理变化,使他们能够毫不费力地完成最初困难的任务。大脑更高层次的重映射可能就是这种变化。最近,梅泽尼奇和他的同事们训练猴子用中指识别不同的振动。随着猴子在区分不同振动频率方面变得更加熟练,它们中指皮层地图中的神经元连接变得更强,地图本身也扩展到相邻区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神经生物学家阿尔瓦罗·帕斯夸尔-莱昂已经表明,训练盲人阅读盲文同样会使他们新获得读写能力的手指所对应的皮层地图膨胀。
“训练实际上能改变大脑微观结构的想法对未来有着巨大的影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大脑研究员弗农·芒特卡斯尔说,“如果结构能在这些低层次范围内被改变,为什么不能在更高层次上呢?你最终也许能以更好的方式进行特定技能的训练。”
然而,在我们能把孩子送到神经学实验室去提升他们的数学能力之前,还有很多东西需要理解。第一步是解决重映射机制这个令人困扰的谜团——它是新轴突的萌芽,正如庞斯所怀疑的,还是潜在回路的显现,正如拉马钱德兰所相信的?两位研究人员可能很快就会合作进行新的实验,使用一种强大的新型大脑扫描技术,称为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来测试截肢者。该技术对患者无害,能清晰地捕捉大脑快照,以确定缺失肢体的输入在触觉通路中最初在哪里出错。了解这一点可能有助于倾向于其中一种解释。然而,一开始,每位科学家都承认,他们自己偏爱的假设似乎比其对手的可能性只高一点点。
“这才是所有这一切真正令人兴奋的地方,”庞斯说,“我们被迫考虑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