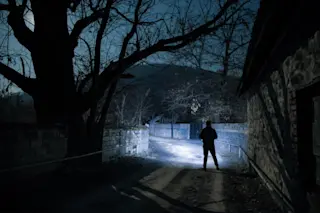你的鼻子是个矛盾体。在某些方面,人类的嗅觉非常精确。例如,天然气公司会在本身无味的天然气中添加一种叫做正丁硫醇的带有气味的分子,这样人们就能闻到燃气泄漏。只需要十亿个甲烷分子中有一个正丁硫醇分子就足以起作用。为了说明这种精度,想象一下你正站在两个奥林匹克标准游泳池前。其中一个泳池里有区区三滴正丁硫醇,而另一个泳池则什么都没有。你的鼻子就能分辨出区别。
但不要得意忘形,因为在其他方面,你的嗅觉几乎是无用的。为了自己评判,找一个人帮你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在你的伙伴翻找你的冰箱并把不同的食物拿到你鼻子下时,闭上眼睛。试着说出每种气味的名字。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肯定会搞砸。在一些研究中,科学家发现,在自己厨房和车库里的物品测试中,人们至少有一半的时间给出错误的答案。而且,我们平时辨别气味的能力很差,我们很容易被愚弄而表现得更差。例如,如果在樱桃味汽水中加入橙色食用色素,人们更有可能说它闻起来像橙子。
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Noam Sobel及其同事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琢磨这个悖论。他们认为,嗅觉科学中一直缺失的是一种有意义的测量方法——一个嗅觉标尺。现在他们已经建造了一个。
长期以来竟然没有人提出一个嗅觉标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愤慨的。例如,研究视觉的科学家知道,波长为620纳米的光会呈现出特定的橙色。他们完全确定,橙色在波长(和感知颜色)上比绿色更接近黄色。他们利用关于光和视觉的这种客观测量,对使我们能够看见的生物学有了很多了解。而研究嗅觉的科学家却没有任何同等客观的方法来判断,例如,玫瑰的香味是更接近留兰香还是香草。
缺乏一个气味标尺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普遍认为人类的嗅觉很粗糙。狗和其他哺乳动物的嗅觉比我们好,但它们的灵敏度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鼻子毫无用处。事实上,正如Sobel及其同事在2007年的一项实验中所展示的那样,人类可以很好地模仿警犬。
Sobel一行人走进一片开阔的场地,铺设了一条用巧克力浸染了30码长的细绳。然后,他们召集了32个人,给了他们一个任务:只靠鼻子追踪。科学家给被试者戴上眼罩,让他们看不到细绳。耳罩挡住了声音。肘垫、膝垫和工作手套保护他们免受触觉线索的影响。只有他们的鼻子能为他们提供信息。被试者四肢着地,距离气味起点约10英尺。然后他们开始闻。
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志愿者都能找到细绳。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中21个人能够从头到尾追踪它的气味。每当他们偏离方向时,他们都会闻着气味找回正确的路线。他们不仅追踪气味能力惊人,而且随着练习还有所提高。科学家安排一些被试者每天进行45分钟的训练,持续三天;他们缩短了时间,提高了准确性。
当Sobel的“人类猎犬”将鼻子贴近地面时,它们吸入的是一种包含多种分子的气体混合物——来自泥土、草地以及空气中携带的任何其他物质。这些分子会附着在鼻腔中神经末梢的嗅觉受体上。一种理论认为,只有某些分子才具有正确的形状来附着在某些受体上。一个给定的受体可以捕捉多种不同的气味分子,而一个给定的气味分子可以附着在几个不同的受体上。鼻子中的每条神经都只使用一个基因来构建其所有的受体。
嗅觉神经元是中枢神经系统中唯一直接暴露在空气中的神经元。当受体捕捉到一个分子时,就会产生一个电信号,沿着神经元从鼻黏膜传输到大脑的气味处理区域。在那里,神经元与其他数千个传递自身信号的神经元汇合。大脑并非被动地接受所有这些信号。例如,如果我们通过一个鼻孔学会区分两种气味,我们也能用另一个鼻孔区分它们。学习发生在**大脑**中,而不是在**鼻子**里。
所有这些复杂的信号处理意味着我们可以区分数千种不同的气味分子。Sobel及其同事最近开始通过确定分子结构与气味之间的关系来阐明这一过程。科学家们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1500种产生气味的分子数据库,并记录了1664种不同的特征——它们的尺寸、原子间的化学键强度等等。
接下来,Sobel和他的团队使用一种称为主成分分析的统计技术寻找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数据云中的模式,这是一种常用于分析大型数据集并提取模式的方法。他们寻找从一个分子到另一个分子始终同步变化的特征。少数关键特征解释了分子结构变化的大部分原因。例如,分子的尺寸与其原子堆积的紧密程度一起变化。Sobel利用这些模式为他数据库中的每个分子赋予一个简单、单一的分数,就像标尺上的刻度一样。
Sobel很快确定,这个标尺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抽象。它与我们闻到世界的方式有着深刻的联系。研究人员从标尺的不同间隔中选取了分子,让人类去闻它们。分子在标尺上的距离越远,人类就越容易通过气味区分它们。
当Sobel让人们评价各种气味有多么令人愉悦或令人不当时,他也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果。标尺一端的分子非常难闻。另一端的分子则令人陶醉。这个标尺在衡量气味质量方面做得非常好,以至于科学家们可以用它来预测人们对新分子的评价有多么令人愉悦(或令人不悦)。
为了验证这个标尺是否普遍适用,神经生物学家Nathalie Mandairon和法国里昂大学的同事们在2008年决定在小鼠身上测试Sobel的气味排序系统。研究人员选择了一组气味,并观察了动物闻嗅它们的时间。气味越接近Sobel标尺的令人愉悦端,小鼠花在闻嗅上的时间就越长。Sobel的气味标尺似乎揭示了关于嗅觉本质的一个基本事实。他认为,当我们的祖先的鼻子进化成复杂的分子探测器时,它们就开始处理关键特征,以产生一种简单的测量——一种内在的标尺。我们的祖先在感知到象征着有益事物的气味时(例如母亲的乳头、成熟的水果)会感到愉悦,并朝它们靠近。他们对于象征着危险的气味(例如腐烂的尸体或捕食者的粪便)会感到厌恶或恐惧,并远离它们。
然而,我们的嗅觉并非一个纯粹自动化的系统。Sobel认为,气味不仅仅是分子的物理特性;它还包括这些特性唤起的**情感**。这就是学习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可以学会恐惧某些象征危险的气味,就像我们学会将危险与视觉或听觉联系起来一样。在更深层次上,我们的大脑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重新评估同一种气味。如果你饿了,培根的香味可能很诱人,但如果你吃了四份之后,同样的香味可能会让你感到恶心。科学家们可以通过观察大脑中情绪调节区域的活动变化来看到这种重新评估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利用愉悦和厌恶来指导我们不仅找到合适的食物,还能吃到适量的食物。这些与情感和学习的联系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次闻嗅就能唤起强大的记忆。
利用Sobel的标尺,科学家们或许能够开始揭开嗅觉的悖论:为什么我们如此擅长区分气味,却如此不擅长命名它们。我们的大脑似乎进化出了一种巧妙的方法,可以将我们环境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分子多样性简化为一个简单的尺度,这个尺度基于气味最重要的方面——它们闻起来好还是坏。通过将不同的气味分子放置在标尺上的位置,我们可以区分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异。尽管这种方法可能很有用且高效,但它并没有提供多少信息可以用于给不同的气味命名。想象一下,有人给你看不同种类的水果图片,让你给它们命名。现在想象一下,图片放大到每种水果的单一颜色区域。你可能很容易就能区分两种红色,但却无法说出哪种红色属于草莓,哪种红色属于覆盆子。
Sobel认为,这个类比实际上低估了我们在命名气味方面的困难。他区分了气味分子和“气味对象”。存在一个我们称为“香蕉”的视觉对象,它包含了我们看到香蕉的整体体验。还有一个“香蕉”的气味对象版本,它是水果释放的分子固有的愉悦感(由Sobel的标尺测量)以及我们遇到它们时的主观心理状态的结合。情感本身就难以用语言表达,而气味中蕴含的情感使得识别问题更加困难。
最高法院法官Potter Stewart于1964年著名地写道,色情制品很难定义,但他一看就知道。同样,我们可能无法给一种气味命名,但我们肯定知道什么东西“很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