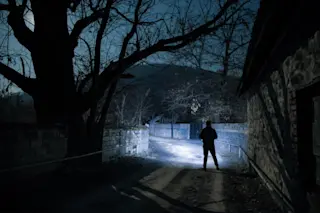当厄休拉·贝卢吉(Ursula Bellugi)发表演讲时,一位手语专家为她翻译。这位手语翻译员的手在空中疯狂地挥舞,手指舞动得仿佛着了魔。它们在空中盘旋,用短促的刺击打破空气,卷曲和展开,在空间中形成各种形状。手语翻译员的脸同样生动。表情快速地闪过,传达出细微差别、语调和语法细节,这是随便一个不懂手语的观察者无法想象的。所有这一切都以惊人的速度进行。
忙碌的神经科学家贝卢吉正在强调一个观点:她能说的任何话,手语翻译员都能“说”。手语是真正的语言。它不是哑剧,也不是口语的蹩脚、洋泾浜派生品——它本身就是一种内涵丰富的语言。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正是贝卢吉本人让一个怀疑的世界相信了这一事实。
但是,作为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索尔克生物科学研究所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主任,以及美国手语神经生物学领域的世界专家(正如一位研究人员所说,“她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这个领域最重要的人物,这个领域的老祖母”),63岁的贝卢吉对手语的兴趣不仅仅在于手语本身。手语为她提供了一扇了解大脑的窗户,一种发现语言生物学基础的途径。她和全国各地的其他研究人员正在确定大脑中独特地适合语言任务的区域。事实上,他们认为语言能力很可能是与生俱来的,由基因决定,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决定性特征之一。
贝卢吉对语言根源的迷恋始于1968年,那时她刚从哈佛大学获得语言学和心理学博士学位。乔纳斯·索尔克邀请她在以他名字命名的研究所建立一个实验室,那是一个俯瞰太平洋的朴素混凝土建筑群。在哈佛大学,她研究了儿童如何学习口语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底层规则。现在,她和她的丈夫、语言学家爱德华·克利马(Edward Klima)开始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思考语言。她想知道,语言是如何在大脑中处理的?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认为语言取决于说话能力,是人类发出声音的能力的产物。因此,贝卢吉决定比较听力正常的孩子学习说话的方式和聋哑孩子学习手语的方式。通过将语言与看似完全不同的交流系统进行比较,她希望能找出两者之间的差异。“我们对手语一无所知,”贝卢吉回忆道,“我们只是认为比较言语和手语是一个理论上有趣的问题,一个可能让我们走向语言生物学的问题。”
她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贝卢吉不仅对手语一无所知,她很快发现几乎没有人知道。“文献中几乎什么都没有,”她回忆道,“而且所记载的都是相互矛盾的。”然而,无论手语是什么,它都没有被当作真正的语言。一些语言学家说手语是“一堆松散的象形手势”;另一些人说它只是源于口语的粗糙交流系统——“手上的蹩脚英语”。还有人宣称它太模糊,另一些人则说它太具体,它“恐惧并避免抽象”。贝卢吉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但她知道一件事:“所有这些不可能都是真的——它们根本不吻合。”
然而,有一个概念吸引了她的想象力。这是威廉·斯托科(William Stokoe)的创意,他是华盛顿特区高立德大学的一位叛逆教师,这所大学是世界上唯一一所为聋人开设的文理大学。斯托科怀疑手语不仅仅是毫无关联的手势集合。他认为手语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构成部分组成的:即手语者用手做出的形状,他们在空间中放置形状的位置,以及他们手在空间中移动的方式。事实上,这些部分让他想起了口语中组成单词的模块化声音片段,称为音素。(音素大致相当于c-a-t,或th-a-t,或ch-ea-t中的三个音节;每种语言都有一套有限的这些构成要素。)1965年,斯托科和他的同事出版了《美国手语词典》,收录了数千个手语及其各种构成部分。
这只是理解手语的第一步,而且极具争议性,但对贝卢吉来说,它提供了一个线索,表明手语毕竟可能具有结构,就像“真正的”语言一样。她对此很感兴趣,决定仔细研究。“我们的大脑非常擅长分类——即使在没有秩序的地方也能强加秩序,”她说。“我们不知道这本词典是否只是出于分类的热情,还是有某种现实依据。”如果她想在语言学习过程的研究中将手语与口语进行比较,那么确定这种现实至关重要。“毕竟,”贝卢吉说,“如果你不知道某物是否具有结构,你就无法提出孩子如何学习其底层结构的问题。”
于是,贝卢吉和她的实验室从零开始着手研究。这并不容易。首先,她必须掌握手语。“我以前常去一个聋人常去的保龄球馆,”她回忆道,“我会缠着他们教我。那是一种老式的学习方式。现在有手语结构课。但在那些日子里,请记住,我们正试图找出手语是否真的有结构。”其次,她不知道如何进行实验来回答这个问题。如何在纯视觉-空间交流形式中辨别结构?(“我们当时没有任何工具包,”她哈哈大笑地回忆起早期的挑战。)为了设计她的研究,她向聋哑手语者寻求帮助。(如今参观她的实验室,你会惊叹于它那一片片寂静。并不是说没有事情发生:研究人员经常专心交谈。只是大部分交流都是手语。)
显然,你需要对语言有敏锐的理解,才能发现另一种交流系统是否遵循相同的原则。对贝卢吉来说,语言的本质是它的语法。单词或手语的集合只是词汇;它的使用仅限于相当粗糙的交流。但是,要达到语言的盛放——无论是莎士比亚,纳博科夫,还是你日常的闲聊——你需要单词通过某些规则相互关联,并能进行调整。这让你能从有限的词汇中生成各种有意义的可能性。
考虑一个非常简单的句子:“小女孩看着小男孩。”在英语口语中,句子的意思由词语的顺序决定。“小女孩看着小男孩”与“小男孩看着小女孩”有不同的意思。这种顺序关系——主语、动词、宾语——是句法的一个方面,句法是语法中将词语组织成句子的部分。现在聚焦在“looks”这个词上。用语言学家的行话来说,一个词中最小的有意义的片段被称为语素。“looks”包含两个语素:词根“look”和词尾“-s”,这里表示人称和时态。合乎逻辑的是,如果你改变语素,你就会改变意思。因此,例如,将“look”末尾的“-s”换成“-ing”会传达一种更连续的动作。“小女孩正在看着小男孩”与“小女孩看着小男孩”有着明显不同的意味。句法和形态学——这是语法的两个基本特征。
贝卢吉通过研究手语使用者发现,美国手语(ASL)也由语法定义,但其语法依赖于空间、手形和动作。口语者通过线性声音序列表达的意思,手语者则在三维空间中进行交流。例如,在ASL中,“看”这个基本手语类似于和平手势,但它不是向上举起,而是将两根稍微张开的手指水平弯曲并指向被看的事物。要表达“小女孩看着小男孩”,手语者将“小女孩”的手语放置在空间中的一个点,将“小男孩”的手语放置在另一个点,然后将“看”的手语从一个点移向另一个点。(对于“小男孩看着小女孩”,则“看”的手语在两个点之间向相反方向移动。)
贝卢吉发现,ASL不仅有其独特的空间句法,还有其生动的形态学。要表达“小女孩正在看着小男孩”,“看”的手语通过手部动作的形态变化进行修改:通过像摩天轮一样将手从女孩移向男孩再回到女孩,完成一个完整的圆圈,来传达持续的看。更重要的是,面部是语法信息的宝库。非常特定的面部动作(比如以某种方式抬高和放下眉毛,撅起和紧闭嘴唇)补充了关于关系从句、疑问句和副词细微差别的信息。这些面部标记,姑且称之为,远远超出了普遍用于表达情感的面部表情的范围。
到1979年,贝卢吉和克利马在他们的开创性著作《语言的符号》中得出结论,手语无疑是语言。“手语的表面形式截然不同,”贝卢吉说,“但其基本内容,即底层组织,与口语相同。”他们发现,手语作为一种语言,与口语一样丰富,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丰富;对于那些熟悉它的人来说,它具有口语所不具备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视觉戏剧性。“我记得有一天我回家对我的丈夫说,‘好像有一个舞台。在空间中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平面,就在这里’”——贝卢吉勾勒出她面前的一个区域,从腰部到脸部,从肩膀到肩膀——“‘表演正在这里进行。’”而“听者”,实际上是剧中的观众,则看着动作在他们眼前展开。
贝卢吉的一个实验强调了这个视觉世界的力量。她将小灯固定在手语者的手上,然后让受试者置身于黑暗的房间中,以遮蔽他们手和脸部的物理细节:当他们做手语时,他们的“言语”纯粹以跳动的光线模式表达。在不了解的人看来,这就像萤火虫的闪光,但在其他手语者看来,这显然是语言。即使当词语难以辨认时,手语者也能识别出独特的语法模式——比如传达持续动作的“看”的摩天轮式动作。贝卢吉还确定,外国手语遵循类似的语法原则,尽管从表面上看它们与美国手语(ASL)毫无相似之处。她解释说,就像汉语口语有不同的发音一样,你在中国手语中也会发现不同的手形和动作组合。“一个美国手语使用者无法理解一个中国手语使用者。甚至你握手的方式都不同。”(一个常见的美国手语音素包括一个拳头,大拇指放在食指上;它的中国对应物看起来更像一个搭便车的手势。)“事实上,当一个中国母语手语者来到美国学习美国手语时,他通常会带着口音打手语。”她高兴地笑了。“让你不寒而栗,不是吗?”
然而,证明手语是语言,却引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显然,人类进化的很大一部分都投入到口语的创造中,”贝卢吉说。“口语确实是我们的设计目的。”然而,这里有一种在空间中默默表达的视觉语言,而人类大脑显然也能掌握它。“这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我想知道手语在大脑中是如何组织的。”
到1970年代末,人们已经很清楚大脑的两个半球有不同的功能。当我们说话和听别人说话时,左半球占主导地位;右半球让我们感知空间关系。但这里有一个奇怪的例外——一种视觉和空间兼具的语言。大脑是如何处理的?“如果手语是双侧处理的,或者因为其空间性质更多地在右半球处理,那将是说得通的,”贝卢吉说。
为了找出答案,贝卢吉调整了传统上用于研究口语的技术,其中一种是观察遭受脑损伤的人的语言障碍。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必须是终身聋哑的手语使用者,并且其损伤特定于其中一个半球——“这确实是一个罕见的群体,”贝卢吉说。“但到那时,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由大约500名聋人组成的全国性网络。他们为我们找到了遭受中风的聋哑手语使用者。”
这些实验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仍在进行,充满了惊喜。一位志愿者在一次中风损伤了她大脑右半球的一部分后,曾是一名艺术家。她仍然可以绘画,但无法完成她画作的左侧——这是右脑控制左视野注意力的部分受损的结果。因此,她省略了大象、房屋和花朵等图形的左侧。然而,当被要求打手语表达包含大象、房屋和花朵等词语的句子时,她一如既往地流利,用完整的手势“说话”,并使用身体左侧和右侧的空间。“她的手语绝对无可挑剔,”贝卢吉说。“没有任何困难,语法完全正确,两侧空间都用到了。”
其他右脑损伤的手语使用者也表现出类似的怪癖。当被要求画出她卧室的布局时,一位女士把所有家具都堆在画面的右侧,左侧留空。当她打手语时,她描述所有家具都在右侧,因为她对空间中位置的感知被扭曲了。但是,尽管她的空间感知被扭曲了,她的手语能力本身却完好无损。她可以像以往一样准确地形成手语,即使这些手语涉及到她身体左右两侧的三维空间。
遭受大脑另一侧(左侧)中风的聋哑手语者的表现恰恰相反。与右半球受损的患者相比,他们能够画出卧室的图片,所有家具都摆放在正确的位置。但他们不能有效地使用手语——他们的左半球损伤损害了他们的语言能力。
结论是不可避免的:“手语,像口语一样,主要在大脑的左侧处理,”贝卢吉说。当涉及到手语时,左右脑之间所谓的视觉空间/语言二分法并不成立。
现在,贝卢吉发现,患者的损伤程度因中风发生在其左脑的确切位置而异。例如,一名患者的左额叶受损,导致手语断断续续、费力;她无法将手语串联成句子。贝卢吉研究对象中其他左脑区域的损伤导致了不同的问题——形成和理解手语困难,句法和语法错误。一名左半球中部有病变的女性在音位方面有问题,这相当于在口语中将“gine”替换为“fine”,或将“blass”替换为“glass”。
有时——但并非总是——损伤部位和由此产生的缺陷与口语受损的中风患者的类似损伤-缺陷关系相对应。这表明手语和口语的一些神经网络是共享的,而另一些则不是。如果幸运的话,这些相似之处和差异应该能让研究人员确定大脑中对语言不同方面至关重要的系统。“这就是我们将追踪口语和手语的神经系统的方式,”贝卢吉说。
贝卢吉的结论——语言,无论其形式如何,都源于左脑——与关于大脑半球作用的公认观点相悖。但她的观点得到了全国各地同事的其他证据支持。其中一位是她的索尔克研究所的邻居,神经心理学家海伦·内维尔(她的实验室就在贝卢吉实验室的正上方)。
内维尔与聋人和听力正常的人都有合作,记录他们在执行语言任务时的大脑活动。在实验中,她的志愿者戴着一个镶有电极的帽子,这些电极测量他们在阅读和听英语句子,或观看视频屏幕上显示的美国手语句子时的大脑电波。她也发现,“左半球在语言功能上存在强大的生物学偏向。”这并不是说没有一些有趣的例外。例如,虽然几乎所有右撇子都依靠左脑处理语言,但只有三分之二的左撇子是这样。另外三分之一中,一半在右脑显示语言活动,一半在两侧都显示。内维尔说:“但左撇子只占总人口的10%左右,所以我们谈论的不是很多人。”
一个半球或另一个半球的主导地位也与一个人学习一门语言的年龄有关。人们早就怀疑,学习语言越早,掌握得越好。早期习得与左脑密切相关。“如果你到18岁才学习英语,你就不会对英语表现出左半球的专门化,”内维尔说。“如果你到青少年晚期才学习美国手语,你就不会对美国手语表现出左半球的专门化。它会分散在大脑各处。”然而,由于大多数人在儿童时期学习他们的主要语言,左脑的偏向仍然是主要的——对于口语和手语都是如此。“想到如此不同的语言形式是由相似的大脑系统调节,这真是令人惊奇,”内维尔指出。“这暗示着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不变性,仿佛语言能力是与生俱来的。”
贝卢吉同意语言功能似乎是人类大脑固有的。“左半球对语言有先天倾向,”她坚定地说,“无论表达模式是什么。”
这一说法触及了语言学界长期以来的一个核心辩论。语言更多是先天还是后天的产物?一方是“经验派”,他们认为掌握一门语言主要是一个技能掌握问题,然后是实践、实践、再实践。“天赋派”则指出,孩子从来没有被教导过语言的所有基本规则。他们是零碎、随意地接触语言,但在他们两岁左右的某个时候,他们开始说话,表现出对语法的掌握,这与他们所接触的贫乏语言环境完全不符。他们怎么能在接受如此之少的情况下,取得如此之多的成就呢?因为,这种说法认为,他们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实际上,语言存在于我们体内——它只是在寻找机会显现出来。
许多支持先天学派的证据来自于手语。三年前,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认知心理学家、贝卢吉的前学生劳拉·安·佩蒂托(Laura Ann Petitto)发表了一项关于牙牙学语婴儿的引人入胜的研究。父母给他们打手语的聋哑婴儿像父母对他们呢喃细语的听力正常的婴儿一样牙牙学语——区别在于聋哑婴儿用手进行牙牙学语。佩蒂托后来表明,接触口语和手语的听力正常的孩子(因为他们父母中的一方是聋人)对口语没有偏好。他们会发出牙牙学语的声音和手势,并且同时学习口语和手语。至于没有接触口语的听力正常的孩子(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是聋人),他们学习手语就像任何聋哑孩子一样容易,并且在后来接触口语时能够流利地使用双语。佩蒂托说,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婴儿如何掌握语言的基本结构,无论它是口语还是手语。“我们人类生来就有一种机制,它会梳理环境,寻找语言的节奏模式,无论这些模式是用手还是用舌头表达的。”
关于语言本能的进一步有趣证据来自对尼加拉瓜聋哑儿童的一项研究。在1979年革命之前,这些儿童散布在全国各地——孤立无声。由于尼加拉瓜几乎没有遗传性耳聋(与美国不同,美国4%到6%的聋哑儿童是聋哑父母的孩子),因此没有手语传统代代相传。孩子们用手势与听力正常的亲戚交流,但一个孩子的手势与另一个孩子的手势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1980年,尼加拉瓜各地建立了聋人学校。聋人儿童首次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社区雏形。这些孩子也首次开始相互交流。鲁特格斯大学的行为神经科学家朱迪·凯格尔(Judy Kegl)将发生的一切描述为“有记录以来第一次语言的诞生”。
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孩子们聚在一起后不久,就根据他们在家庭中使用的手势,创造了一套共享的洋泾浜手语。这些手语让他们能够以一种粗糙的方式进行交流,但并没有表现出构成真正语言的语法特性。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奇迹。“三四岁的小孩子接触到那种临时的洋泾浜手语,并将其吸收,”凯格尔说。“然后,凭借他们自身的语言生成能力,他们创造出了一种成熟的语言。”
十多年来,这些大约500名儿童一直在无中生有地创造一种语言。它显示出语法特征规则,如名词和动词的一致性,主谓宾句式结构,以及一定数量的手形和动作构建模块。但与代代相传的美国手语不同,这种新语言是凭空产生的。“他们没有任何可以作为模型的语言,”凯格尔说。“这清楚地证明了人类拥有先天的语言能力。”
那么,语言是否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呢?麦吉尔大学语言学家米尔娜·戈普尼克(Myrna Gopnik)认为如此。“一个或几个遗传因素显然会影响语言的习得,”她说。戈普尼克的观点基于对一些正常听力家庭的研究,这些家庭表现出一种非常具体的、遗传性的语言障碍——本质上是无法构建和应用语法规则。在因纽特人、希腊人、日本人和美国人等不同人群中,可能高达3%的人存在这个问题。请这些人将一个简单动词转化为过去时,他们就做不到——或者至少不能不费力地遍历所有语法规则来得出适当的结构。他们无法自发地选择正确的词。他们断断续续的言语暗示着更深层次的残疾,而实际上他们在其他方面都是正常的。
休斯顿贝勒医学院的遗传学家帕特里克·邓恩(Patrick Dunne)正与戈普尼克合作,寻找可能导致这种损伤的基因。如果他们找到它——一个很大的“如果”——它可能会为理解正常的语法处理打开大门,并可能指向其他语言基因。(“这就是遗传学的基础,”邓恩说。“你追踪导致问题的突变基因。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在正常情况下是如何运作的。”)
这一切都源于贝卢吉的认识:手语的无声世界让她能够解剖大脑中的语言。“她拥有新颖的洞察力,卓越的洞察力,认识到在没有声音的情况下进化的语言是通往我们大脑的极其强大的途径,”佩蒂托说。
“手语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人类语言能力的信息,”贝卢吉说。“经过26年的研究,我可以说这句话了。我一直有一种动力,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想要理解语言和大脑。我也让聋人对这一切产生了好奇。这真是一次非常激动人心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