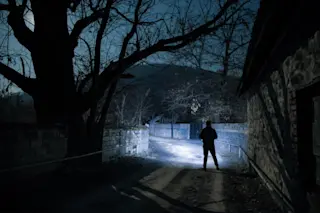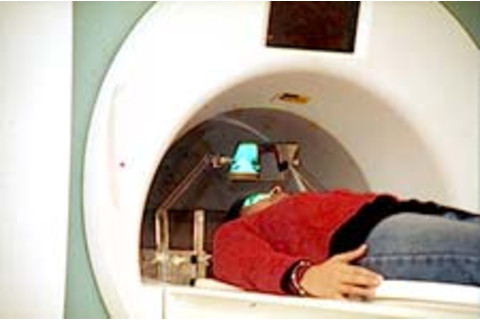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这里正在研究生梅丽莎·萨恩斯身上进行,它跟踪大脑中的血流。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人员在斯坦福大学与索尔克研究所合作,使用同样的技术绘制了迈克·梅视力恢复后的视觉处理图。
麦克劳德在大学的实验室是一个由文件柜、光学设备和奇特摆放的办公桌组成的迷宫。“这里布满了陷阱,”他说道,在一个下午,他引导梅走向众多测试中的第一个。“但是梅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导航复杂布局的能力。”梅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尽管头发花白,但面容英俊,如果不是因为他失明的一些副作用,他会是一个很好的詹姆斯·邦德。与身体其他部位不同,他的眼睑从未进行过终生锻炼。它们总是半闭着,使他的脸呈现出一种坚忍的空白,只有偶尔的微笑才能打破这种空白。他还没有学会面部表情。
梅顺从地坐在一个老旧的电脑显示器前,看着屏幕上出现粗壮的黑橙色条纹。麦克劳德和菲恩正在测试他分辨细节的能力。他的任务是用轨迹球调整对比度,直到他刚好能看到这些条纹。点击鼠标会弹出另一组条纹,比上一组更细,他又摆弄这些,直到也能看到它们。尽管他的右眼应该提供20/20的视力,但实际上接近20/500。他无法在25英尺外辨认视力表上的字母 E,只能在两英尺外才能看到。过去,视力恢复者视力模糊的原因被归咎于手术留下的疤痕组织。但干细胞手术不会留下疤痕。信号到达了梅的大脑,但它们没有被很好地解读。
三百多年前,爱尔兰思想家威廉·莫利纽克斯在致哲学家约翰·洛克的一封著名信件中,预料到了梅所见的情景。莫利纽克斯认为,一个突然获得视力的盲人,将无法区分立方体和球体。视觉是一种感知,触觉是另一种感知;它们只能通过经验联系起来。
这一理论最引人注目的证明来自于理查德·赫尔德和艾伦·海因于1963年发表的一项实验,当时他们是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布兰迪斯大学的教授。赫尔德和海因在完全黑暗中养育了两只小猫。但他们会时不时地将小猫放在单独的篮子里,将篮子悬挂在一条单一的圆形轨道上,然后开灯。两个篮子都悬挂在离地面不远的地方,但其中一个有供小猫腿伸出的洞;另一个则没有。有自由肢体的小猫在地板上绕圈跑,将另一个篮子拖在后面;另一只小猫别无选择,只能坐着观看。虽然活跃的小猫学会了正常视物,但被动的小猫实际上仍然是盲的:它的眼睛能看到,但它的大脑从未学会解释感官输入。
赫尔德和海因的实验从未被复制过。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对视力恢复的研究,最著名的是奥利弗·萨克斯和理查德·格雷戈里的研究,已经证实有些事物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是无法理解的。物体、面孔、深度——几乎所有帮助我们在世上运作的事物——对于一个从未见过世面的人来说,在获得视力时都是毫无意义的。“婴儿出生在一个明亮、嘈杂的混乱世界中,但我们无法问他们是什么感觉,”菲恩说。“在某种程度上,与迈克·梅交谈就像与一个7个月大的婴儿交谈。”

艾昂·菲恩和唐·麦克劳德使用这台干涉仪,将分裂的激光束射入梅的眼睛,以测试他处理视觉信息的能力。他们也对自己进行同样的测试。“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里,”菲恩说,“戴着眼罩,嘴里咬着咬合杆。这很恶心……真是旧塑料。”
在手术后的最初几个月,梅证实了莫利纽克斯的预测:他无法区分球体和立方体。从那时起,他的视力有所改善,但幅度很小。他对球体和正方形的理解更深了(“我们给他看了很多很多,”菲恩说),并且通过练习,他能理解他反复看过的东西。但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他已经过了学习立即识别物体的关键期。
“我拥有的两个主要线索是颜色和语境,”梅说。“当我在篮球场上看到一个橙色的东西时,我假定它是圆的。但我可能并没有真正看到它的圆度。”面孔给他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尽管他从视力恢复的第一天起就到处看到面孔,但它们根本无法融合成可识别的人。他们的表情——他们的情绪和个性——完全逃脱了他的理解。甚至他的妻子,他也只能通过她的步态特征、头发的长度和穿着的衣服来熟悉。“如果一张脸没有头发,并且有假胡子,我们仍然可以判断性别,”菲恩说。“但他无法处理。大脑中负责这部分的功能没有起作用。”
对此最好的证明可以在地下室看到,那里放置着麦克劳德的干涉仪。这台机器旨在测试大脑处理视觉信息的能力,它通过将分裂的激光束射入受试者的眼睛来工作。当光束传播时,它们的光波相互干涉,绕过角膜的光学系统,在视网膜上投射出图案。大多数坐在干涉仪前的受试者会看到明暗条纹,无论其光学质量如何。但当梅睁开眼睛接收光束时,他什么也看不到。
干涉仪的结果得到了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的支持,该扫描追踪梅大脑中正在发生的活动。扫描显示,当梅看到面孔和物体时,大脑中应该用于识别它们的区域处于非活跃状态。但这里有个问题。当他看到一个运动中的物体时,大脑中负责运动检测的部分会像迪斯科球一样亮起来。他能够像任何正常视力的成年人一样解释电脑屏幕上的运动,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似乎也具备相同的技能。“我们开车时,一辆小货车从他那一侧快速驶来,”菲恩回忆道。“它从他身边飞驰而过,他说它开得很快。这是一个复杂的计算。视网膜上的运动取决于汽车的大小、距离和速度。”
我们很难逃避这样的结论:运动检测,除了颜色之外,与所有其他视觉体验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最好的例证可能再次由猫来提供。“如果你把一个球沿地板滚动,猫会一直追逐它,只要它在移动,”菲恩说。“一旦它静止不动,猫就很难看到它,并且会忽略它。”这就是老鼠害怕时会僵住的原因。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连一个静止的球都难以辨认的梅,却能很好地接住一个移动的球。这是他最喜欢的新感官用途。“我不知道谁玩得更开心,”他说,“是我8岁的儿子还是我。”

梅走在街上,他无法辨认透视线,所以他利用视觉地标来保持方向感。“我一次学习一帧,”他说。
盲人一生都通过双手来理解世界。他们的记忆、他们所知道地方的心理地图、他们对拉布拉多犬、门把手和滑雪坡上雪包的理解,都是触觉的。突然引入一种新的感觉,并不能改变这种体验宇宙的基本方式。相反,从光线中获得的新信息,只是简单地叠加到原始的触觉地图上。“认为皮层表面只有一张世界图的旧观念太简单了,”麦克劳德说。“事实上,我们有几十张完整的地图。”对于一个刚开始学习如何融合所有这些信息的人来说,这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困惑。但它也可能提供比我们这些从未失明的人所感知到的更丰富、更真实的世界感。
有一天,麦克劳德坐在实验室里,像一个正在策划恶作剧的学童一样,狡黠地笑着,把一张画推到梅的桌子对面。纸上有四个立方体。右上角的立方体和左下角的立方体是暗的;另外两个是亮的。这幅画的阴影处理得好像光线是从上方照射下来,所以正方形的顶部比正面更亮。这使得暗正方形的顶部与亮正方形的正面具有相同的色调。经验告诉我们,暗立方体的顶部被隐藏的光线照亮了,但它看起来仍然比亮立方体的正面更暗。这是一种基于知识的错觉。自然地,梅没有上当。
“他实际上更接近现实,”菲恩说。“我们曾给他看两个圆圈——一个小的靠近他,一个大的远一些。对你我来说,它们看起来大小相同。但当我们问,‘它们的视大小是多少?’他却不明白。他一直说,‘我知道它更大,因为它在远处。’”同样,梅对走廊和公路的触觉经验告诉他,它们的侧边是平行的,所以他根本无法感知汇聚的透视线。“走廊看起来一点也没有收窄,”他说。“我看到路径两边的线条,但我并不真正认为它们在远处会靠拢。”他停下来沉思。“或者也许我的大脑不相信我的大脑正在感知的东西。当我看到一个物体时,我绕着它转圈,它对我来说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我知道车辆周围的橙色锥筒是锥筒,是因为语境,而不是因为我看到了形状。如果我设想俯视一个锥筒,它看起来仍然像一个锥筒。”
对梅来说,学习看,实际上是学习我们所有人都会遇到的同样幻觉,将某些颜色和线条的集合称为他的儿子,将另一组颜色和线条称为一个球。
四月的一个早晨,在眼科手术几周后,梅带着他的滑雪板和家人前往内华达山脉的柯克伍德山度假村——一个他像手背纹理一样熟悉的地方。他在这里第一次学会了滑雪,后来也在这里遇到了他的妻子。阳光普照,树木葱郁(比他想象的还要绿),山坡被美丽的悬崖环绕(是几英里远还是几百码?)。缆车在上方轰鸣,穿着蓬松滑雪服的滑雪者在他视野中掠过,时隐时现。他的妻子作为向导,不得不提醒他停止张望,开始滑雪。
梅只有一个眼睛能工作,已经缺乏深度感知。但他也很少有阅读地貌阴影和轮廓的经验。下山时,他几乎无法区分阴影和人、杆子或岩石。起初,他试图有意识地计算地形:如果某个斜坡是从侧面被照亮,并且阴影以这种方式落下,那么斜坡一定是凸的。但一旦他碰到第一个颠簸,他就想闭上眼睛,以他熟悉和喜爱的方式滑雪。
只有少数成年人曾通过新生儿的眼睛看世界,其中许多人后来都希望自己仍然是盲人。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曾说服他们,视力将提供一种奇妙的、对世界全新的欣赏和理解。然而,即使是最简单的行为——走下楼梯,过马路——也变得异常困难。沮丧和抑郁,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回到了盲人的世界,喜欢黑暗的房间,闭着眼睛走路。
如果梅感受不同,那可能是因为他的期望值如此之低。对于一个过去喜欢盲目地独自玩风帆冲浪,并且通常能从出发的码头返回的人来说,视力只是他充满活力的障碍人生中的又一次冒险。在重返柯克伍德山两年后,梅已经学会将他在滑雪坡上看到的东西与他反复的身体体验相匹配。“他给自己搭建了一个相当实用的系统,”菲恩说。“他知道这种阴影会形成这种隆起,那种阴影会形成另一种隆起。”现在,即使在最简单的斜坡上,他也不再闭上眼睛,他可以无需向导就能通过雪包。
“人们认为视力在实际生活中非常重要,”梅说。“我说从娱乐角度来看它很棒。我一直在寻找那些对视觉来说独特的东西。跑步和接球就是其中之一——我一生都在追逐球。看到我两个儿子的眼睛蓝色差异是另一个。或者如果你掉了东西,你可以找到它。”
最终,视力的馈赠对那些从未失明的人来说,可能显得最为神奇。但梅仍然能在世界上找到令他着迷的事物。有一天,他坐在菲恩汽车的副驾驶座上,他的狗乔什在他的脚边喘着气,他忽略了左边蔚蓝的太平洋,以及路边高耸、头重脚轻的桉树,那些树看起来像是苏斯博士笔下的东西。相反,他凝视着透过车窗洒在他膝盖上的阳光。他说:“我简直不敢相信灰尘就这样飘浮在空中。”海洋和树木,无论是苏斯博士笔下的还是其他的,他一生都通过触摸来认识。但这在拉霍亚明媚的阳光中闪烁的尘埃,却是一种全新的感知。他挥舞着手穿过那闪闪发光的束光。“就像有许多小星星围绕着你一样。”
你看到我看到的了吗?

迈克·梅的右眼通过干细胞手术和角膜移植已恢复,视力应该达到20/20。然而,他的视力接近20/500——或者说像右侧的例子一样模糊。“基本上,结果表明,你只能在生命早期,在关键时期获得精确视力,”唐·麦克劳德说。“我们不知道梅最终会怎样,但他并没有以很快的速度接近正常视力。”

迈克·梅保持着盲人高山滑雪的世界速度纪录。在他的竞技生涯中,他曾以每小时65英里的速度沿着最陡峭的黑钻坡道回转滑行,前方10英尺处有向导喊着“左”和“右”。这些指令只是明显的提示。其余的则来自于风刮过脸颊的感觉和向导滑雪板刮过雪的声音。但梅作为世界级盲人运动员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不再是盲人。
迈克·梅在3岁时,因一罐矿灯燃料在他脸上爆炸而失明。这导致他左眼失明,右眼角膜受损,但在接下来的43年里,他从未让这些残疾阻碍他。他在小学时玩过夺旗橄榄球,大学时踢过足球,成年后几乎参与了所有不涉及投掷物的活动。他获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事务硕士学位,在中央情报局工作,并成为Sendero集团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该公司为盲人制造语音全球定位系统。在此期间,他还抽空帮助开发了第一台激光唱机,结婚,育有两个孩子,并在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买了一套房子。“有人曾问我,如果我能拥有视力或者飞到月球,我会选择什么,”他曾写道。“毫无疑问——我会飞到月球。很多人都有视力,很少有人去过月球。”
1999年11月的一天,他在旧金山圣玛丽医院找回了知觉。外科医生丹尼尔·古德曼将角膜干细胞环状物置于梅的右眼(他的左眼损伤严重到无法修复)。这些细胞取代了疤痕组织并重建了眼表,为角膜移植做准备。2000年3月7日,当纱布被取下时,梅第一次看到了他的妻子、孩子,以及自蹒跚学步以来第一次看到了他自己。
视力恢复是一种周期性的奇迹——对于接受者和有幸研究他们的科学家来说都是如此。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埃及外科医生就用针将患者被白内障覆盖的晶状体推离瞳孔,使他们获得一定程度的视力。最近,在20世纪60年代末,外科医生学会了用超声波去除白内障。对梅进行的干细胞手术是在日本开发的,并于1999年引入。自那时以来,已有数百人从中受益。但在历史上所有视力恢复的病例中,只有大约20例是自幼失明,而且其中大多数人在手术后角膜状况不佳。当古德曼在手术后检查梅的眼睛时,他看到一个应该能提供清晰视力的晶状体。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远非如此。尽管梅的光学硬件完好无损,但他的大脑从未被编程来处理它接收到的视觉信息。梅仍然带着他的狗乔什旅行,或者用拐杖轻敲人行道,并称自己是“一个有视力的盲人”。这种悖论令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实验心理学家唐·麦克劳德和艾昂·菲恩着迷。婴儿学习理解世界的速度表明,他们生来就具备处理视觉某些方面的能力。但究竟是哪些方面呢?哪些是学习而来的,哪些又是天生的?在过去的一年半里,菲恩和麦克劳德对梅进行了一系列身体和心理测试,包括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它追踪大脑中的血流。这些结果正在为我们如何学习看提供第一个清晰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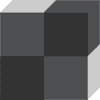
右图:一生的盲症使梅对视觉错觉免疫。大多数人会认为暗色立方体的顶部比亮色立方体的正面更暗。对梅来说,它们是完全相同的色调。只有当麦克劳德解释这种错觉时,梅才能明白正方形本应看起来是三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