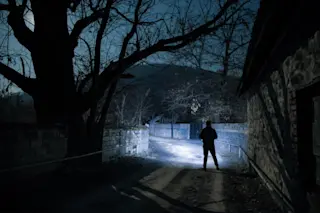大约20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固定的演讲,介绍虚拟现实的基础知识。我会回顾视觉、听觉以及触觉和味觉的基本原理。最后,会开始提问,第一个问题通常是关于气味的:我们很快就能在虚拟现实设备中体验到气味了吗?
也许可以,但可能只有几种。气味与图像或声音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后两者可以分解为计算机构处理起来相对直接的基本组成部分。每种声波实际上是由许多正弦波组成的,每个正弦波都可以用数学方法轻松描述。可见光只是不同波长的光的代名词。
换句话说,图像和声音都可以用几个数字来描述;对这些数字进行插值就可以描述广泛的图像和声音。人类视网膜只需要对少数几个波长或颜色敏感,我们的大脑就能感知所有中间的颜色。计算机图形学的工作原理类似:一个由像素组成的屏幕,每个像素都能呈现红色、绿色和蓝色,就能生成人眼几乎能看到的所有颜色。音乐合成器可以被看作是生成许多正弦波,然后将它们分层组合以创建各种声音。
气味则不同,大脑感知气味的方法也不同。在鼻腔深处,被黏膜包裹着,有一片组织——嗅上皮——上面布满了检测各种化学物质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每个都有杯状蛋白质,称为嗅觉受体。当一个特定的分子恰好落入匹配的受体中时,就会触发一个神经信号,作为一种气味被传送到大脑。太大而无法进入某个受体的一个分子是没有气味的。实际上,独特气味的多少仅受能够与它们相互作用的嗅觉受体数量的限制。弗雷德·休切森癌症研究中心 (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 的琳达·巴克 (Linda Buck) 和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的理查德·阿克塞尔 (Richard Axel)(两人都是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发现,人类鼻子包含大约1000种不同类型的嗅觉神经元,每种类型都能检测到特定的一组化学物质。
这造成了感官底层结构的一个深刻差异——这种差异,事实证明,引发了关于我们思维方式,甚至可能关于语言起源的引人入胜的问题。没有办法在两种气味分子之间进行插值。诚然,气味可以混合在一起形成数百万种气味。但世界的各种气味无法分解成梯度上的几个数字。没有“气味像素”。可以这样想:颜色和声音可以用尺子测量,但气味必须在字典里查找。
从虚拟现实技术人员的角度来看,这真令人遗憾。有数千种基本气味,远比少数几种原色要多。理论上,可以连接一个人的大脑来创造气味的幻觉。但这需要大量的线路来处理“心理气味字典”中的所有条目。话又说回来,大脑必须有一种方法来组织所有这些气味。也许在某个层面上,气味确实符合某种模式。也许确实存在“气味像素”。
不知何故,总会有一个合适的朋友出现,帮助我思考我一直着迷的话题。我的朋友梅兰妮是一位神经外科医生,有一天她用一种不寻常的兴奋语气(外科医生很少兴奋)给我打电话。她说她有紧急消息。“我终于找到另一个像你一样的人了。他甚至和你长得像。”直到我见到吉姆·鲍尔,圣安东尼奥德克萨斯大学的计算神经科学家,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他比我瘦得多,头发是直的,但脸上确实有几分相似。
梅兰妮偶然发现一个可以假扮我替身的人,这真是运气。一方面,当我无法参加一场我本应发表演讲的美国国家科学院会议时,吉姆相当成功地冒充了我(当然,得到了我的祝福)。显然,这对吉姆来说是保守的演讲行为;他曾有过在室内骑马进行神经科学演讲的经历。
更巧合的是,吉姆恰好是嗅觉领域的顶尖专家。他以制作生物学上准确的大脑计算机模型而闻名。多年来,他和他的实验室团队一直致力于理解大脑的“气味字典”。他们怀疑嗅觉系统的组织方式与有机化学家组织分子(例如按碳原子数量)的方式几乎无关;相反,它更接近于现实世界中化学物质的复杂关联方式。例如,他们认为许多有气味的化学物质——那些能触发嗅觉神经元的物质——与有机材料成熟和腐烂的多个阶段有关。事实证明,腐烂有三个不同的化学途径,每条途径似乎都在大脑的气味字典中定义了一个条目流。
吉姆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要“解决”嗅觉问题——让复杂的气味世界快速可识别——人类大脑必须进化出一种特定类型的神经回路。这种回路可能构成了大脑皮层的基础——我们大脑中最大、也许对塑造我们思维方式最关键的部分。因此,吉姆提出,从根本上说,我们思考的方式是嗅觉驱动的。
请记住,气味不是像图像或声音那样的能量模式。要闻到苹果,你需要将数百或数千个苹果分子吸入鼻腔。语境至关重要:如果你蒙着眼睛,被要求闻一种美味的法国奶酪,并且你知道你正站在一间浴室里,你对这种气味的解读很可能与你在厨房里的解读大相径庭。同样,如果你能看到奶酪,你就可以相当肯定你闻到的是奶酪,即使你身处洗手间。
最近,吉姆和他的学生们一直在研究不同动物的嗅觉系统,以寻找大脑皮层整体是否起源于嗅觉系统的证据。他经常将大脑的嗅觉部分称为“老工厂”,因为它们在不同物种之间惊人地相似。由于气味识别通常需要其他感官的输入,吉姆特别有兴趣了解这些输入是如何进入嗅觉系统的。
在鱼类和两栖类(早期脊椎动物)中,嗅觉系统紧邻大脑皮层的多模态区域,不同感官的处理在这里重叠。爬行动物也是如此,但大脑皮层还增加了新的区域,感官在这里是分离的。在哺乳动物中,传入的视觉、听觉和感觉信息会经过许多处理步骤,然后才到达重叠区域。可以将嗅觉想象成一个城市中心,而其他感官系统则像是蔓延的郊区,随着大脑的进化而生长,最终比老城区更大。
这一切都让我们和吉姆不禁想:嗅觉和语言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语言是人类大脑皮层著名的产物?也许字典的比喻有一个真实的物理基础。嗅觉和语言一样,是由目录中的条目构建起来的,而不是由无限可变的模式构建的。此外,语言的语法从根本上是一种将这些字典中的词语置于更大语境中的方式。也许语言的语法根植于气味的语法。也许我们使用词语的方式反映了我们大脑处理化学信息的深层结构。吉姆和我计划通过研究在嗅觉神经学计算机模拟过程中出现的数学特性来检验这一假设。
如果这项研究能够成功,它可能会揭示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一些其他联系。碰巧的是,嗅觉系统实际上有两个部分:一个检测一般气味,另一个是信息素系统,检测来自其他动物(通常是同一种)的非常具体、强烈的气味,通常与恐惧或交配有关。(嗅觉科学远未定论,关于信息素在人类中的重要性存在激烈争议。)语言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平行。除了我们用来描述物体和活动的正常语言之外,我们还保留了一种特殊的语言来表达极端的情绪或不满,并警告他人注意。这种语言称为脏话。
这种言语有特定的神经通路;例如,有些妥瑞氏症患者会无法控制地骂人。而且,很难忽视许多脏话与排放信息素嗅觉信号的器官或活动有关。这些“淫秽”的两个通道之间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联系?进一步的研究很可能会确定这一想法是否有根据,还是我们只是在胡言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