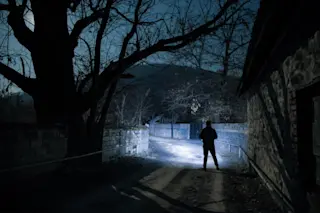那个穿着黑色T恤、头发稀疏的少年惊呆了。我们都站在旧金山牛宫外潮湿的暮色中,等着Megadeth演唱会的大门打开,而我问了他一个显然很疯狂的问题。
“演唱会戴耳塞?”他茫然地重复道,“我为什么要那么做?耳塞就像是给耳朵戴的避孕套。”
他对于用115分贝的重金属音乐轰炸耳朵的漫不经心令人悲哀,但可以理解:听觉一直是感官中的灰姑娘。海伦·凯勒认为失去听觉比失明更痛苦、更孤立,但大多数人却说他们宁愿失去听觉也不愿失去视觉。这种二等地位对研究经费(低)、吸引到该领域的科学家数量(少)以及进展速度(慢)产生了可预见的影响。就在1980年代初,听觉研究人员仍在为听觉的微观和生化基础奠定基础,而他们的视觉研究同行则可以说是在“砌墙”。至于数字,一位生物物理学家不屑地说:“去看看视觉会议,那简直就像超级碗一样。”他估计,全球范围内,严肃的听觉研究人员可能只有200人。
但灰姑娘也有她的高光时刻,看起来听觉这个灰姑娘般的感官也即将如此。实验室技术方面的技术进步,再加上人口老龄化——或许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政府婴儿潮一代,他们曾经用最大音量听过《天堂阶梯》——预示着该领域的光明前景。事实上,已经有了一丝暗示,科学家们将来可能能够恢复我这位年轻朋友随意牺牲的一些听觉感受器。
这些听觉感受器被称为毛细胞,是专门的感觉细胞,是身体中最非凡的结构之一。它们只有32000个(相比之下,眼睛有3亿个光敏细胞), постоянно受到衰老、毒品以及一个包含雪地摩托、喷气式飞机和Megadeth的世界的围攻,它们是我们与寂静之间唯一的屏障。就像公主将稻草变成黄金一样,内毛细胞将声音的机械力转化为听觉的电脉冲。
被称为听觉的神经学现象始于耳朵收集波状气压扰动——声音——这些扰动由任何物理力产生:振动的A弦、森林中倒下的树。外耳,包括肉质的耳廓和耳道,拾取并汇聚这些波向鼓膜,或称耳膜。鼓膜振动并摇动中耳的三块关节骨;反过来,这三块骨头中的最后一块,镫骨(或马镫),弯曲了充满液体、呈螺旋状的耳蜗中一个小的卵圆窗的膜。
进化被称为伟大的修补匠,它从旧结构的点点滴滴中组装出新结构,而耳朵无疑是其最漫长的项目之一。数亿年来,随着脊椎动物的最新模型从海洋到海岸再到陆地,自然选择一直在改造和重新装饰耳朵。然而,其核心的毛细胞几乎未受影响;它们在所有有脊椎动物的听觉和平衡系统中结构几乎相同。碰巧,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耳蜗使得哺乳动物的毛细胞几乎无法研究。
耳蜗是那些像黑洞或胡佛水坝一样,倾向于让观察者产生敬畏的结构之一。“它真是一个器官的珠宝盒,不是吗?”一位着迷的研究人员叹息道,在方程式中间打断了自己。另一位则说:“它真是个不可思议的结构!当我结束显微镜操作时,我感到迷失方向,就像我一直在洞穴潜水一样。”耳蜗确实令人惊叹:一个豌豆大小、螺旋状的骨质堡垒,埋藏在颅骨最厚的部分,包含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机制。但像大多数堡垒一样,它既囚禁也保护。当生物体活着时,无法接触到毛细胞,因为所有的构造都被骨头封闭,而且内耳在死亡几秒钟后就会停止运作。直到最近,才有可能在体外维持毛细胞的存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为内耳设计的安全系统阻止了研究人员大军的入侵,但它在保存其居民方面却表现不佳:我们从出生起就开始失去毛细胞。它们只是因为使用而磨损,特别是那些处理高频声音的细胞。随着时间的推移,暴露在噪音中会使它们变硬。没有人了解导致僵硬的细胞事件序列,但已知的是,当毛细胞长时间保持这种僵硬姿势时,它们就会倒下死亡。
因此,我们不断地损失毛细胞:这边耳边一颗爆竹,那边窗外一把电钻,也许还有高中军乐队中大号旁的几个橄榄球赛季,我们就损伤了几个甚至上百个。到了中年,这种损耗就变成了雪崩:研究表明,65岁的男性平均失去了超过40%的毛细胞天赋。而且,在一个糟糕的日子里,你可能会觉得这证明了宇宙中存在一种恶性力量的现象是,我们的毛细胞无法再生。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它们听力能力非常一般,生活方式也不群居,它们一生中都在补充毛细胞。而我们哺乳动物,拥有高保真度的耳朵,是依赖听力来生存的生物——对于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来说,这包括身体上和情感上。然而,我们这一群体却被困在一个相对微薄且不可再生的配额中。
在耳蜗内部,毛细胞的结构功能极其强大。16000个细胞排列成四排平行行,一排内侧和三排外侧(相对于它们与耳蜗中心极的距离);它们夹在两层膜之间,下方是基底膜,上方是盖膜。这两层膜共同形成一个沿耳蜗长度螺旋下降的隔板。当镫骨推动耳蜗的卵圆窗时,它会通过内耳中的液体(外淋巴)发送一个压力波,从而引发一系列事件:压力波使基底膜振动,基底膜振动毛细胞,毛细胞顶部的刷毛群与盖膜摩擦。每个人的毛细胞上大约有100根这样的刷毛,或称静纤毛,它们根据高度排列成行,就像在拍集体照一样。不活动时,它们呈圆锥状捆绑在一起。但当它们活动时,它们与盖膜的摩擦最终会导致信号沿着听觉神经发送。因此,毛细胞整体充当微型传感器,将它们从耳蜗液中接收到的机械冲动转化为大脑解释为声音的电能。
这一连串事件无疑带有鲁布·戈德堡式的色彩,而阐明这链条中的最后一个机械环节(如果耳朵是戈德堡那些奇思妙想的装置之一,比如制造甜甜圈的装置,那么这个环节就是面团碰到脂肪的地方)占据了神经科学家吉姆·哈德斯佩斯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哈德斯佩斯现在是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基础神经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回忆起他最初的目标:“我认为重要的是要从宏观系统——整个耳蜗——过渡到微观和细胞系统。”这涉及到忽略一些诱人的问题;他坦言,这迫使他放弃了耳朵复杂而有趣的力学和流体动力学。他也顺其自然地忽略了大脑途中发生的复杂而有趣的事情。“我只想以亲密的方式处理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就是毛细胞的机械输入。
他和他的研究小组要回答的问题是:毛细胞的静纤毛是如何运动的,以及当它们运动时会发生什么?在1970年代末,他们以青蛙作为实验动物,发现用一根极细的石英纤维——鉴于静纤毛仅有百万分之一英寸大小,这种方法被称为“电话杆法”——拨动静纤毛束时,电流会通过细胞。(这种电流产生兴奋神经的化学物质,神经通向大脑。)他们发现了两个令人惊讶的现象:拨动方向至关重要,而且使静纤毛产生反应所需的拨动幅度极小。
哈德斯佩斯发现,只有从前或后推动才能产生电流;左右推动则没有任何效果,原因后来才对研究人员明朗。此外,哈德斯佩斯计算出,如果细胞的偏转量相当于听觉阈值声音产生的偏转量,纤毛会使毛束移动大约千分之三度。(只是为了衡量,一排几个原子加起来才是一整度。)因此,整个临时搭建的机制——鼓膜到中耳骨、中耳骨到卵圆窗、卵圆窗到外淋巴液中的压力波、外淋巴液中的压力波到基底膜振动——最终归结为:以原子直径的几分之一来衡量的运动。哈德斯佩斯观察到:“这就像埃菲尔铁塔移动了拇指的宽度。”
哈德斯佩斯最初从事研究时,生物学家们已经理解了细胞信号传递的基本机制:刺激导致细胞膜上微小的孔洞——离子通道——打开,带电粒子从细胞外移动到细胞内,表现为微小的电流变化。例如,视觉已被确定为一个过程,其中光线照射到眼睛的光感受器,引起化学反应,从而打开离子通道并激发神经纤维。
哈德斯佩斯和他的团队因此推测,当他们拨动静纤毛时,毛细胞中的离子通道必然会打开和关闭。困扰他们的是,这些相对迟缓的生化事件如何在耳中发生,而耳是为速度而生的。毕竟,你可以欺骗眼睛,让它相信自己以每秒30帧的速度看到了运动,这是一个第一批动画师直观理解的现象。但这种速度对耳朵来说是极其缓慢的:每秒30次循环(或30赫兹)的频率太低,我们几乎听不到。然而,一个年轻的人耳可以处理小提琴的最高泛音,即每秒20000次振动的频率。我们的耳朵可以辨别当一个声音在比另一个耳朵晚六到十微秒传入时所产生的延迟。生化级联需要千分之一秒——慢了三个数量级——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为了解决时间问题,哈德斯佩斯的小组假设,耳中可能存在某种离子通道的机械门,一种能够像耳的敏锐度要求的那样迅速——实际上是瞬时——打开它们的装置。如果存在这样的装置,它将是听觉系统独有的,但它至少具有符合耳部设计规范的优点。
哈德斯佩斯明确表示,机械门的存在有理论依据和间接证据。即便如此,他说,当这些结构开始出现在扫描电子显微照片中时,那简直是奇迹。它们最初是由英国的一个实验室识别出来的,哈德斯佩斯回忆说,这有点令人尴尬。“我们自己也见过一些,但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解读它们。”这些被称为“尖端连接”的线状结构,将每个静纤毛与其最高的邻居连接起来,很像连接着一队电话杆越过山脉的电线。
尖端连接的前后路径是静纤毛侧向拨动不产生电流的原因。哈德斯佩斯将这些连接比作系在门把手上的橡皮筋,门把手被顶部那些发出噪音的门闭合器关着。“那是传导通道固有的弹性;它保持门关闭,除非你采取行动。如果你拉动橡皮筋——那就是毛束的偏转——这种张力就会传递到门上。当毛束移动时,你实际上是在把通道拉开一点。当门关闭时,寂静就降临了。”
毛细胞刷毛上微米大小的装置仅仅是耳朵如何听觉的展开故事的一部分。细胞体内部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三排外毛细胞的细胞体——同样引人入胜。
耶鲁大学医学院的听觉生理学家约瑟夫·桑托斯-萨奇就是其中一个着迷的人。他与许多同事一样,对外界毛细胞及其滑稽行为怀有一种近乎父亲般的感情:“这是一个有趣的系统,值得研究。”他说。为了展示毛细胞如何运动以及它有多么有趣,他制作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一个毛细胞随着说唱歌手Hammer的《Can't Touch This》摇摆。
令桑托斯-萨奇着迷的外毛细胞是哺乳动物对低等动物中更原始毛细胞的改良。尽管外毛细胞与内毛细胞通过它们在耳蜗中的位置而区分开来,但它们的区别远不止地理位置——真正的区别在于神经解剖学领域。
神经是一条单行道:它要么通向大脑,要么远离大脑。大多数内毛细胞与大脑之间的神经都是从外向内走的,正如你所预料的;毕竟,我们的耳朵应该将外部事件的信息传递给大脑。然而,奇怪的是,大多数外毛细胞与大脑之间的神经却是反方向的,从大脑到耳朵。大脑会告诉外毛细胞什么呢?
20世纪80年代初,外毛细胞的故事变得更加离奇。研究人员发现,外毛细胞不仅连接方式奇特,它们的行为也异常。它们不是被动地与基底膜同步振动(内毛细胞大致如此),而是像狂躁的孩子在蹦床上一样上下跳动。事实上,它们伸缩的速度比身体中任何其他细胞都能达到的速度快了几个数量级。
外毛细胞这种出人意料的个性表现——被称为快速运动——现在是听觉研究最热门的领域之一。(桑托斯-萨奇绘制了自1985年以来发表的论文数量与时间轴的关系图,并表示由此产生的曲线可以描述为指数曲线,趋于无穷大。)无论其研究轨迹如何,快速运动之所以热门,是因为它提出了两个引人入胜的问题:外毛细胞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以及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更容易回答。看来,外毛细胞跳动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加速基底膜的运动。
盘旋在耳蜗内部的3.2厘米长(约1.25英寸)的膜本质上是一个声学解码器。它处理构成语音等声音的纠缠在一起的听觉频率,将它们分类为独立的频段。例如,对高频声音的反应,基底膜在耳蜗螺旋基部的振动会比在顶端更强烈。反之,低频声音在顶端振动膜的强度会比在基部更强。(就像一个倒置在最高音上的微型螺旋键盘,基底膜每毫米处理大约八分之一的音程。)
但是——这就是谜团所在——基底膜的振动频率比它仅仅通过内耳外淋巴液中的声波所能接收到的任何运动都要快一百倍。外毛细胞是否在跳舞以改变基底膜的运动?大脑和外毛细胞之间的连接是否在那里,以便大脑可以告诉毛细胞以多快的速度跳舞?
桑托斯-萨奇这样阐述问题:“外毛细胞的运动能力能否像我们都希望的那样在活体动物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细胞能否以耳朵工作的高频率摆动并改变内耳的机械结构?”有理由认为它们可以;毕竟,它们一定有移动的原因。而且,实验性地用于消灭毛细胞的药物确实改变了基底膜的机械结构。
这是“为什么”;“快速运动如何发生”的答案可能更难找到。在实验室里,毛细胞的移动速度不能超过每秒几千次,远不及活体动物必须达到的频率。桑托斯-萨奇怀疑他的实验设备可能阻碍了细胞真正自由摆动。他认为限制因素是他用来向细胞传递刺激的电极的电阻:“这就像我试图测量一辆汽车能开多快,但我的脚踝受伤使我无法踩下油门。”
然而,另一个问题却并非那么容易解释。在基底膜的底部,高频声音被解码的地方,毛细胞似乎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改变基底膜的振动。那么,研究人员面临的是两个显著现象——高度调谐的基底膜和快速移动的细胞——但却没有明显的桥梁将它们连接起来。“这里缺少一些东西,”桑托斯-萨奇承认,“事情还没有完全吻合。”但他确信这种联系是存在的。“想想看,”他反问,“进化会白费力气吗?”
当然,普通的重金属乐迷可能会争辩说,进化并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听觉系统虽然精巧、敏感、巧妙,但在其主人衰老之前就已经衰退了,尤其是在嘈杂环境中生活的人。然而,即使是这个缺陷也可能最终通过研究得到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人员对鸟类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这可能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大家都曾认为,我们这些听觉相对敏锐的带羽毛的朋友,在毛细胞方面和哺乳动物一样:用坏了就没了。但在1985年,南卡罗来纳大学的道格·科坦奇(Doug Cotanche)和华盛顿大学的埃德·鲁贝尔(Ed Rubel)都发现,雏鸡的毛细胞可以再生。
在鲁贝尔的案例中,这是一个经典的科学偶然发现故事。他的实验室当时使用小鸡作为实验动物来研究一类抗生素的耳毒性——也就是说,他们想了解这些药物对听觉器官的损害程度。负责这项研究的医学住院医师劳尔·克鲁兹发现,“受损毛细胞的数量在给药后最多,”鲁贝尔回忆道,“但过了一段时间,似乎有越来越多的健康细胞。他把结果拿给我看,而我,像任何完全接受自己领域教条的人一样,说:‘劳尔,你肯定把毛细胞数错了。回去再数一遍。’”
嗯,正如任何熟悉好莱坞电影或收银台科幻小说的人都会告诉鲁贝尔的那样,计数没错,但教条错了。确实有更多的毛细胞,因为新的毛细胞正在生长。与此同时,在南卡罗来纳州,科坦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成年鸟类因噪音受损的耳蜗上看到了类似胚胎毛细胞的结构,这让他们也怀疑听觉器官可能正在自我修复。随后,大家齐声“啊哈!”,接着便开始了旨在分离毛细胞再生的实验。这些实验证实了鸟类毛细胞确实会重新生长。
新毛细胞确实有效。研究人员训练八哥对特定音调啄击按键,并奖励食物颗粒。在服用耳毒性药物后,受过训练的鸟类会无法通过音调测试,但随着毛细胞的再生,它们会逐渐恢复这项技能。
此外,这些鸟的耳朵听起来也好像恢复了功能。尽管目前尚无人理解其原因,但事实证明,在功能正常的耳朵中发出的咔嗒声或其他轻柔的音调会在几微秒后产生回声。如果毛细胞受损,回声就会消失。这些耳声发射是迄今为止诊断婴儿耳聋的最佳工具,这正是苏珊·诺顿(Susan Norton)——一位与鲁贝尔合作的研究临床医生——通常所做的工作。然而,最近,她一直在利用这些发射来追踪鲁贝尔鸟类受试者听力的恢复情况。诺顿发现,毛细胞受损后立即没有发射;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毛细胞的再生,发射会恢复,首先是对高强度声音的发射,然后是对低强度声音的发射。
当然,最大的问题是这项工作对人类听力意味着什么。“关于哺乳动物的研究很少,”鲁贝尔提醒道。他的团队观察了沙鼠的耳蜗,发现细胞生长有少量增加,尽管他们没有看到新的毛细胞发育。其他实验室也发现了毛细胞再生的少量情况,但仅限于内耳中控制平衡的部分。今年3月,伦敦大学学院的安德鲁·福奇以及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的杰弗里·科温及其同事宣布,他们观察到了豚鼠的毛细胞再生。弗吉尼亚州的研究人员还在培养皿中发现了人类毛细胞再生的迹象,方法是使用取自耳蜗(称为椭圆囊)负责平衡区域的人体组织。尽管这些是平衡毛细胞,但研究人员对这对于听觉毛细胞再生的意义感到兴奋。
但首先要解决的是:目前的任务是分离出刺激鸟类毛细胞增殖的分子。(或者,如果某种分子抑制哺乳动物的增殖,就找出那种分子。)目前有几个实验室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在生物技术公司的协助下,这些公司渴望参与这项研究,因为从长远来看,这项研究可能会为2800万听力受损的美国人生产出有用的药物。
鲁贝尔对这些可能性侃侃而谈:“在生物学史上,我们发现这一点正处于一个绝妙的时刻,”他高兴地说,“我们正在学习很多东西,而且我们拥有在读研究生时无法想象的强大技术。现在还很早,”他特意指出,“你必须记住,毛细胞再生这个领域才四年。但我们做得非常棒!而且在我看来,”他补充道,“当谈到实际恢复听力时,毛细胞再生是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