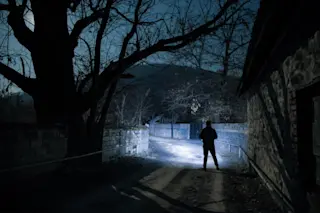“我们去跳伞吧”这个想法是在一个周五晚上的派对上萌生的,但现在我周六早上酒醒了,却不知怎么还要去跳伞。更糟糕的是,那是在1984年,虽然串联跳伞于1977年发明,但这个概念尚未普及到我所处的中俄亥俄州机场。所以我的第一次跳伞不是和教练绑在一起处理可能遇到的任何困难。相反,我独自从2000英尺高空跳下,我唯一的安全网是一个笨重的老式军用降落伞,被称为“圆伞”。
谢天谢地,没人指望我自己拉开伞绳。一根静态绳,只不过是一根短绳,已经固定在我的伞绳和飞机地板之间。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当我在飞机外15英尺处到达绳子末端时,它就会拉开降落伞。达到这一点要复杂得多。
当飞机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飞行时,我必须爬出侧门,无视令人眩晕的景色,踩在一个小金属踏板上,双手抓住机翼,并将一条腿抬到身后,使我的身体形成一个巨大的T字。从这个姿势,当教练发出指令时,我就要跳下去。如果这一切还不够糟糕的话,当我最终跳出飞机时,我也跳出了我的身体。
就在我松开机翼的那一刻,它发生了。我的身体开始在空中下坠,但我的意识却在大约20英尺之外盘旋,看着我下落。在训练中,教练解释说,降落伞在部署的最初几毫秒内会先打开,然后关闭,再打开。他还提到,这发生得太快,人眼无法看到,我们不必担心。然而,在我开始下坠的那一刻,我却感到担忧。我还看着降落伞的“开-关-开”动作,尽管我知道我所看到的从技术上讲是不可能看到的。
我的身体开始倾斜,歪向一个尴尬的姿势,当降落伞张开时会产生相当大的震动。在可以最好地描述为一次体外清醒的时刻,我告诉自己要放松,而不是冒颈部扭伤的风险。下一瞬间,我的降落伞猛地打开。这一下把我从意识中拉回到身体里,一切恢复正常。
出体体验属于一种不那么寻常的现象,广义上被称为超自然现象,尽管字典将这个词定义为“超出正常经验或科学解释的范围”,而出体体验两者都不是。这种类型的体验在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被报道了几个世纪。几乎所有信仰的神秘主义者,包括世界上所有五种主要宗教,长期以来都讲述着星体投射的故事。但这种现象并非只保留给宗教人士。极限运动的年鉴中充斥着摩托车手回忆自己飘浮在摩托车上方,看着自己骑行的故事,以及飞行员偶尔发现自己飘浮在飞机外,努力回到飞机内的故事。然而,大多数出体体验的故事并非发生在极端环境中。它们是在正常生活中发生的。
出体体验与濒死体验非常相似,对其中任何一个的探索都必须包括另一个。虽然出体体验仅由意识上的感知转变定义,不多也不少,但濒死体验始于这种转变,然后沿着特征轨迹进行。人们报告进入一条黑暗的隧道,走向光明,并感受到一种包罗万象的平静、温暖、爱和欢迎。他们回忆起沿途被已故的朋友、亲戚和各种宗教人物所安慰。偶尔会有一次人生回顾,然后是“我应该留下还是离开?”的选择。1990年盖洛普对美国成年人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近12%的美国人,大约3000万人,表示他们有过某种濒死体验。
1982年,医生梅尔文·莫尔斯(Melvin Morse)遇到一个案例,激起了他对这些极端意识状态的好奇心。莫尔斯在西雅图儿童医院儿科完成住院医师实习期间,兼职直升机辅助急救服务。一天下午,他被派往爱达荷州波卡特洛,对8岁的水晶·梅尔茨洛克(Crystal Merzlock)进行心肺复苏,她显然在社区游泳池的深水区溺水了。莫尔斯到达现场时,孩子的心跳已经停止了19分钟;她的瞳孔已经固定并散大。莫尔斯让她心脏重新跳动,然后跳上直升机回家了。三天后,水晶恢复了意识。
几周过去了。莫尔斯回到水晶正在接受治疗的医院,他们在大厅里偶然相遇。水晶指着莫尔斯,转向她母亲说:“他就是那个在游泳池给我鼻子插管子的人。”莫尔斯惊呆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以前从未听说过 OBEs [出体体验] 或 NDEs [濒死体验]。我站在那里想:这怎么可能?当我把管子插进她鼻子时,她已经脑死亡了。她怎么会有这段记忆?”
莫尔斯决定对水晶的经历进行案例研究,并发表在《美国儿童疾病杂志》上。他将此事件标记为“迷人症”(fascinoma),这既是医学俚语,指一种异常病理,也是当时我们知识状况的恰当总结。他是第一个发表儿童濒死体验描述的人。
他首先回顾了文献,发现经典的解释——妄想——最近已升级为由多种不同因素引起的幻觉,包括恐惧、药物和大脑缺氧。但药物引起了莫尔斯的注意。他知道,越南战争期间用作麻醉剂的氯胺酮经常会产生出体体验,其他药物也被怀疑是诱因。莫尔斯决定研究另一种常用麻醉剂氟烷,他相信他的研究可能有助于解释急诊室里不断涌现的许多濒死体验报告。“现在想起来很有趣,”他说,“但当时,我确实着手进行一项长期、大规模的揭穿研究。”
莫尔斯1994年的报告,通常被称为西雅图研究,并发表在《儿科当前问题》上,历时十年。在此期间,他采访了西雅图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的160名从假性死亡中复苏的儿童。这些儿童中的每一个都脉搏停止或呼吸停止超过30秒。有些人处于这种状态长达45分钟;平均假性死亡持续10到15分钟。作为对照组,他使用了数百名其他也在重症监护室、也濒临死亡的儿童,但他们的脉搏和呼吸没有中断超过30秒。这是唯一的区别。在其他方面——年龄、性别、给药、所患疾病和环境——两组是相同的。在环境方面,莫尔斯不仅包括重症监护室本身,还包括插呼吸管和机械通气等可怕的医疗程序。这些是重要的补充,因为恐惧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濒死体验的诱因(也可能是我跳伞时发生的事情的诱因)。
莫尔斯根据格雷森量表(Greyson scale)对受试者的经历进行评分,这是一个由弗吉尼亚大学精神病学家布鲁斯·格雷森(Bruce Greyson)设计的16点问卷,至今仍是判断异常经历是否应被视为濒死体验的基准。通过这项测试,莫尔斯发现26名经历过假性死亡(心跳和呼吸停止)的儿童中,有23人报告了典型的濒死体验,而对照组中其他131名儿童均未报告任何此类经历。
莫尔斯后来录下了孩子们回忆经历的视频,其中包括长长的隧道、巨大的彩虹、已故的亲戚和各种神祇等标准内容。但许多描述——辅以蜡笔画——包含了对所进行的医疗程序的记忆,以及关于医生和护士的详细信息,这些医生和护士与孩子的唯一接触发生在孩子看似死亡的时候。
其他科学家也重复了莫尔斯的发现。最近,荷兰阿纳姆Rijnstate医院的研究员、心脏病专家Pim van Lommel进行了一项为期八年的研究,涉及344名心脏骤停患者,他们似乎已经死亡,后来又被复苏。总共282人没有记忆,而62人报告了典型的濒死体验。就像莫尔斯的研究一样,van Lommel检查了患者的记录,寻找传统上用来解释濒死体验的任何因素——例如环境、药物或疾病——但没有发现任何影响的证据。假性死亡是唯一与濒死体验相关的因素。他还发现,他研究中的一个人对他在被推定死亡期间医院里发生的事情有着难以解释的记忆。
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的研究发现了一些可能解释这些异常状态生物学基础的线索,当时海军和空军引入了新一代高性能战斗机,这些飞机经历了极端加速。这些速度产生了巨大的G力,将过多的血液从飞行员的大脑中抽出,导致他们昏迷。这个问题被称为G-LOC,即G力引起的意识丧失,非常严重,航空航天医学专家詹姆斯·惠纳里(James Whinnery)负责解决这个问题。
在16年的时间里,惠纳里在宾夕法尼亚州沃敏斯特海军航空武器中心的一个大型离心机上,让战斗机飞行员进入G-LOC状态。他想确定在多大的重力下会出现隧道视野。研究期间有500多名飞行员意外昏迷,惠纳里从他们身上了解了飞行员在加速下失去意识需要多长时间,以及加速停止后他们昏迷了多长时间。通过研究这个子集,他还了解了他们在脑损伤开始之前可以昏迷多长时间。
他发现G-LOC可以在5.67秒内诱发,平均昏迷持续12到24秒,并且至少有40名飞行员在昏迷期间报告了某种出体体验。由于对出体体验一无所知,惠纳里将这些发作称为“梦幻小品”,详细记录了其内容,并开始查阅有关异常无意识体验的文献。“我正在阅读心脏病学中猝死事件的文章,”惠纳里说,“这直接把我带入了濒死体验。我意识到我的飞行员中一小部分(大约10%到15%)的梦幻小品在内容上更接近经典的濒死体验。”
惠纳里审查他的数据时,注意到一个关联:飞行员昏迷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接近脑死亡。他们越接近脑死亡,出体体验就越有可能演变成濒死体验。这是第一个确凿的证据,证明了长期以来的猜测——这两种状态并非两种不同的现象,而是连续体上的两个点。
惠纳里发现,G-LOC,如果逐渐诱导,会产生隧道视野。“进展首先是灰视(失去周边视力),然后是黑视,”他解释道,失明发生在人失去意识之前。“这很有道理。我们知道枕叶(控制视力的脑部区域)是一个受保护良好的结构。也许当来自眼睛的信号因血液供应受损而失灵时,它仍在继续工作。从灰视到失去意识的转变类似于在黑暗隧道中平静地漂浮,这很像濒死体验的一些定义特征。飞行员还回忆说,在恢复意识时感受到一种平静和安宁。”
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的最简单结论是,除了某些无法解释的记忆外,这些现象只是在异常情况下发生的正常生理过程。毕竟,一旦科学家们抛弃了将妄想作为这些异常心理状态来源的传统诊断,并开始寻找生物学相关性,就会有大量的可能性。视神经受压可能导致隧道视野;血清素、内啡肽和脑啡肽等神经化学物质可以帮助解释欣快感;而LSD和麦角酸胺等精神药物常能产生生动的过去事件幻觉。但没有人直接测试过这些假设。
研究人员已经研究的是濒死体验的影响。范·洛梅尔(Van Lommel)对他的心脏骤停患者研究组进行了长时间访谈,并进行了一系列标准的心理测试。经历过濒死体验的子集报告比其他人有更高的自我意识、社会意识和宗教情感。
两年后,范·洛梅尔再次重复了这一过程,发现经历过濒死体验的小组仍然对事件有着完整的记忆,而其他人的回忆则明显不那么生动。他还发现,与其他人相比,经历过濒死体验的小组对来世的信仰增加,对死亡的恐惧减少。八年后,他再次重复了整个过程,发现这些两年后的影响显著增强。经历过濒死体验的小组更加富有同情心,情感上更脆弱,并且经常表现出直觉意识增强的证据。他们仍然对死亡没有恐惧,并坚信来世。
莫尔斯在他最初的研究之后也进行了长期的后续研究。他还进行了一项独立研究,涉及在幼年时期有过濒死体验的老年人。“两组的结果是相同的,”莫尔斯说,“几乎所有有过濒死体验的人——无论是在10年前还是50年前——仍然绝对相信他们的生活有意义,并且存在着一条普遍的、统一的爱之线,提供了这种意义。与对照组相比,他们在生活态度测试中得分更高,在死亡恐惧测试中得分显著更低,向慈善机构捐赠更多钱,服用更少的药物。没有其他方式可以看待这些数据。这些人只是被这种经历改变了。”
莫尔斯继续撰写了三本关于濒死体验及其引发的关于意识本质的问题的畅销书。他的研究引起了亚利桑那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候选人威洛比·布里顿(Willoughby Britton)的注意,她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感兴趣。布里顿知道,大多数曾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人都会患上某种形式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而那些如此接近死亡却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则没有。换句话说,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对危及生命的创伤有非典型的反应。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布里顿还知道传奇神经外科医生和癫痫专家怀尔德·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在20世纪50年代所做的工作。彭菲尔德是现代神经科学巨擘之一,他发现用微弱电流刺激大脑右颞叶(位于耳朵上方)会产生出体体验、天籁之音、生动的幻觉,以及与濒死体验中人生回顾部分相关的全景式记忆。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右颞叶癫痫长期以来以其最突出的症状来定义:以强烈的灵性感、神秘幻象和上帝之声般的听觉幻觉为特征的过度宗教性。鉴于惠纳里的发现,他的飞行员濒死般的“梦幻小品”可能与颞叶血流受损的短暂发作有关。
布里顿假设,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可能会表现出与颞叶癫痫患者相同的异常脑电放电模式。确定某人是否患有颞叶癫痫的最简单方法是监测睡眠期间的脑电波,因为此时癫痫活动的可能性会增加。布里顿招募了23名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和23名既未经历过濒死体验也未经历过危及生命的创伤事件的人。然后,她在睡眠实验室中,将受试者连接到测量大脑(包括颞叶)所有区域脑电图活动的电极上,并记录了他们在睡眠期间发生的一切。
然后,她请一位对实验一无所知的亚利桑那大学癫痫专家分析脑电图。两项特征将濒死体验组与对照组区分开来:他们所需的睡眠时间大大减少,并且在睡眠周期中进入快速眼动(REM)睡眠的时间比正常人晚得多。“一个人进入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间是抑郁倾向的一个绝佳指标,”布里顿说,“我们在这类研究中做得非常好。如果你对100个人进行睡眠研究,我们可以查看数据,通过他们进入快速眼动的时间,就知道谁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变得抑郁,谁不会。”
正常人在90分钟进入快速眼动睡眠。抑郁的人在60分钟或更早进入。布里顿发现,绝大多数经历过濒死体验的群体在110分钟进入快速眼动睡眠。凭借这一发现,她确定了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的第一个客观神经生理学差异。
布里顿认为濒死体验以某种方式重塑了大脑,她已经找到了一些支持其关于颞叶活动改变的假说的证据:22%的濒死体验组表现出颞叶同步,这与颞叶癫痫的放电模式相同。“22%听起来可能不算多,”布里顿说,“但实际上这是非常异常的,以至于超出了偶然的范围。”
她还发现了一些与她的假设不符的东西。颞叶同步并没有发生在脑的右侧,即彭菲尔德研究中与颞叶癫痫中的宗教情感相关联的部位。相反,她发现它发生在脑的左侧。这一发现让一些人感到不安,因为它与那些比彭菲尔德更详细地确定了在深刻宗教体验期间大脑中最活跃和最不活跃的精确位置的研究相呼应。
过去10年,包括科罗拉多大学神经学家詹姆斯·奥斯汀(James Austin)、神经科学家安德鲁·纽伯格(Andrew Newberg)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已故人类学家兼精神病学家尤金·达奎利(Eugene D'Aquili)在内的多位科学家,对佛教徒冥想时和方济会修女祈祷时的大脑进行了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SPECT)。他们发现顶叶(大脑后上方区域)活动显著减少。这个区域帮助我们确定自己在空间中的位置;它让我们判断角度、曲线和距离,并知道自我从何处结束,世界的其他部分从何处开始。这个区域受损的人在驾驭最简单的生活场景时会遇到很大困难。例如,坐到沙发上会变成一项艰巨无比的任务,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的腿在哪里结束,沙发在哪里开始。SPECT扫描表明,冥想会暂时阻断双侧顶叶内感官信息的处理。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正如纽伯格和达奎利在他们的著作《上帝为何不消失》中所指出的那样,“大脑将别无选择,只能感知自我无尽地与心智感知的一切事物紧密交织。这种感知会感到完全且毋庸置疑的真实。”他们利用脑部扫描结果来解释佛教徒所体验到的相互联系的宇宙统一性,但这些结果也可以解释莫尔斯所说的濒死体验者始终报告的“普遍、统一的爱之线”。
这些脑部扫描显示,当顶叶安静下来时,右颞叶的部分区域——其中一些正是彭菲尔德展示的,能产生过度宗教性、出体体验和生动幻觉的区域——变得更加活跃。纽伯格和达奎利还认为,宗教仪式中常见的活动,如重复吟唱,会激活(和去激活)大脑中相似的区域,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一些更令人费解的出体体验报告,比如那些飞行员突然漂浮在飞机外的情况。这些飞行员就像冥想者专注于咒语一样,全神贯注于他们的仪表。同时,引擎旋转的声音会产生一种重复的、有节奏的嗡嗡声,很像部落鼓声。纽伯格说,如果条件合适,这两件事足以产生相同的颞叶活动,从而触发一次出体体验。
加拿大劳伦琴大学的神经心理学家迈克尔·珀辛格(Michael Persinger)进行了其他研究,探索异常精神状态的产生。珀辛格制造了一个能产生微弱、定向电磁场的头盔。然后,他要求900多名志愿者(大部分是大学生)佩戴头盔,同时他监测他们的大脑活动并改变电磁场。当他将这些磁场导向颞叶时,珀辛格的头盔诱发了那种神秘的、脱离身体的体验,这在右颞叶癫痫患者、冥想者和有过濒死体验的人身上很常见。
所有这些工作并非没有争议,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现在认为我们的大脑天生就能产生神秘体验。研究证实,这些体验与任何其他体验一样真实,因为我们与宇宙其他部分的互动是由我们的大脑介导的。这些体验仅仅是右颞叶活动,正如许多人猜测的那样,还是如布里顿的研究暗示和莫尔斯所相信的,是整个大脑的影响,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珀辛格认为,对于濒死体验者为什么会记得他们在显然死亡期间发生的事情,有一个简单的解释。他说,记忆形成结构位于大脑深处,在外部皮层的大脑活动停止后,它们可能仍然活跃几分钟。然而,克里斯特尔·梅尔茨洛克(Crystal Merzlock)却记住了她心脏停止跳动后超过19分钟发生的事件。没有人能完全解释这种现象,我们仍然处于那种非常熟悉的神秘状态:我们仍然没有所有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