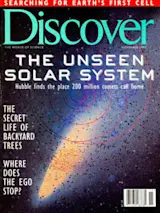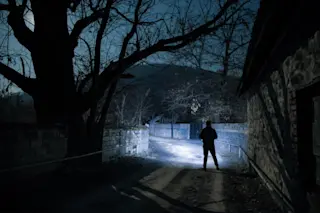我一直在思考一个人需要多少个身体。这通常不是我作为一名科学家会感兴趣的问题,但最近它悄悄潜入我的意识中,我发现自己不再确定答案了。
一天下午,我看到一个人拥有两个身体。斯蒂芬·霍金,这位天体物理学家因其渐进性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渐冻症)导致的瘫痪和他的研究而同样闻名,他来到我的研究生院讲授时间的开始和结束。那是十年前,当时霍金还能稍微动一下嘴巴,发出一种咕噜作响、难以理解的声音。尽管我们不指望用我们初级的物理知识理解这次讲座,但我们挤满了礼堂,生物化学家、生理学家和遗传学家,只为见证霍金被疾病侵蚀的身体和他的心智对时间何时开始或是否开始的认知。
四位物理学教授,没有一个年轻,把霍金抬上舞台。他们气喘吁吁,但似乎只有他们才能完成这项任务,仿佛如果你不理解狭义相对论,触碰他的轮椅,你可能会被汽化。他们将霍金连同轮椅一起放置,背对我们,然后教授们离开了。接着,在寂静中,电动轮椅嗡嗡作响并旋转,露出了一个戴着角质眼镜、面容枯槁的身影。
当我们坐在那里,被这位来自墓穴的木乃伊大脑所震撼时,一个穿着牛仔裤、头发蓬乱的年轻人漫步走上舞台。他看起来像是刚从床上爬起来,仍然沉浸在他离开的人身上。他走到霍金身后,甩了甩头,整理了一下金色的鬃毛,突然猛地推了一下轮椅。
天啊,霍金要从舞台上滚下去了。这个摇滚明星般的刺客正在谋杀伟大的斯蒂芬·霍金。在最后一秒,那个年轻人伸出手,勉强停住了轮椅。他让霍金面向观众,然后弯下身子对着麦克风。他用傲慢的英国公学口音说:“你知道,你不是在教堂里。”
显然,这就是霍金的翻译。当霍金开始时,傲慢的声音翻译着那嘶哑的声音。今天我将讨论我的一些关于时间开始和结束的理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理论已经通过实验得到证实。在另一些情况下,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证实它们。我们窃笑——这个傲慢的混蛋——然后我们才意识到。你怎么能对斯蒂芬·霍金有这样的想法呢?
随着讲座以缓慢而极其清晰的方式展开,时间在没有开端的情况下闪烁而生。无线电波,违抗可能,从黑洞中逃逸。方程式出现,夹杂着顽皮的幽默。
但那个孩子变得更糟了。当霍金挣扎时,他百无聊赖地把粉笔抛向空中。他掉了粉笔,迫使“木乃伊”重新开始这项艰巨的任务。有一次,当他翻译错一个句子时,霍金不得不重复自己。翻译员怒目而视,嘟囔着:“你没有让人听懂。”
这是什么生物?我们渐渐明白过来。霍金,在他剑桥曾由牛顿坐过的椅子上,选他作为他的学生,他的密友。这是他选择的声音。我们对“木乃伊大脑”的看法开始转变。
在生病之前,霍金是个爱出风头的人,他故意以半速工作,勉强完成一些任务,然后回到派对,一切都带着一种放荡不羁的才华。他一定就像这个孩子一样。我们突然明白:他们计划好了这一切——横冲直撞的轮椅,那种漫不经心——是为了让我们的体验去神圣化。我们感受到的这种阴谋如此亲密,以至于霍金似乎借用了他学生的存在。一个小时里,那个木乃伊大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正在聆听一位傲慢的剑桥大学教授的精彩讲座——他只是碰巧需要两个身体才能完成这一切。
霍金的表演是一个比喻,一出戏。人们也认为,它只是暂时的。然而,它仍然提出了许多问题:身体和意识的数量可以不一致吗?它们可以长时间保持不一致吗?这个问题很少引起神经科学家的兴趣,但裂脑病人是一个重要的例外。虽然大脑大致对称,但其功能可以偏侧化——左右两边执行不同的任务。左半球通常专长于语言,而右半球则擅长非语言空间能力、面部识别和音乐。尽管新时代(New Age)的荒谬主张声称人们以左脑或右脑的方式进行各种可能的行为,但偏侧化的科学是扎实的。
两个半球通过一束粗大的连接线——胼胝体——进行交流,通常这种交流是有益的。但在某些类型的癫痫中,一次发作可以引发对侧半球的镜像部分再次发作。发作在胼胝体上来回追逐。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一些癫痫病人的胼胝体被手术切断,从而阻止了他们的癫痫发作,但患者留下了两个断开的半球。神经科学家罗杰·斯佩里因对这些病人的实验获得了诺贝尔奖。在一些实验中,他只向一个半球输入信息,而在另一些实验中,他同时向每个半球输入不同的信息。他的结果表明,两个半球可以独立运作,具有独立的分析能力。例如,如果一个物体呈现在病人的视野中,使得信息只进入语言半球,病人可以轻易识别图片。但当相同的信息呈现在非语言半球时,他甚至无法说出他看到了任何东西——但他可以通过触摸识别物体。
斯佩里的实验表明,每个半球都能学习、记忆、推理、有观点、启动行为、自我意识、感受时间流逝、想象未来并产生情绪。这提出了一个棘手的前景,即一个头骨中可能存在两个人。更糟的是:也许正常人也由两个独立的个体组成,通过胼胝体连接在一起。心理学家朱利安·杰恩斯在一本极其古怪的著作《意识的起源:二分心智的崩溃》中探讨了这种可能性。他认为,一种连贯的自我感、一个边界清晰的自我,直到大约3000年前才发展起来。在此之前,他写道,大脑是二分式(即双室的),两个半球几乎没有整合。一个半球说话,无论是隐喻还是字面意义,另一个半球服从,将声音归因于神。杰恩斯断言,现代的自我感代表着二分心智的崩溃。他声称精神分裂症患者仍然是二分心智,并用考古学、神话、经典著作和《圣经》中大量的琐碎细节来支持他的观点。学者们认为这本书令人眼花缭乱地博学、启发人心又有些疯狂。
与杰恩斯不同,斯佩里驳斥了任何人脑中存在两个个体的说法,大多数科学家也同意他的观点。尽管裂脑病人可以被操控以展示两种独立的认知风格,但潜在的观点、记忆和情感是相同的。这可以用解剖学来解释。即使胼胝体被切断,对情绪和生理调节至关重要的大脑深层结构仍然保持连接。裂脑并非真的裂成两半,而是形成一个Y形。可能存在两个独立的意识,一个通过记住街道名称在城镇中导航,另一个通过记住城镇外观的空间地图导航——但它仍然是同一个个体。一个身体,一个人。
关于一个身体内能有多少个“自我”的争论,围绕着多重人格障碍展开。我们个性的不同方面在不同情境下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可能在老板面前表现得像另一个人,而不是在下属面前,或者在女人面前表现得像另一个人,而不是在男人面前。但我们并非真的是不同的人。然而,在多重人格障碍患者中,不同的个性似乎在不同时间完全控制着患者的行为。大多数心理健康专业人士认为,存在这样一些个体,其个性的不同方面如此脱节和分离,以至于构成了疾病。这些患者通常描述曾遭受过可怕的童年虐待,一些理论家认为,将不同个性分隔开来是一种保护策略。但是,这些不重叠的身份真的代表不同的个性吗?
一些临床医生报告了数百例此类患者,并相信这种疾病的生物学真实性,他们引用研究表明,当人格转变时,眼镜或药物处方也会随之改变。其他临床医生则对这种说法勃然大怒,坚称真正的多重人格患者职业生涯中只出现一次,而那些不同眼镜的故事只是故事。
精神病学界的元老们普遍持后一种观点。在最新版精神病学“圣经”《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对该疾病的定义进行了谨慎的修改;其诊断不再涉及多重人格的存在。相反,前提是存在“独特的身份或人格状态”,甚至该疾病也有了新名称:分离性身份障碍。换句话说,患有该疾病的患者以多种方式认同自己,但专家们拒绝说明这些身份是否构成人格。此外,套用一位帮助修改手册的精神病学家的话说,使这成为一种悲惨疾病的原因是,患者没有不止一种人格;当这些碎片被拼凑起来时,他们实际上连一种人格都算不上。
分离性身份障碍和裂脑患者都提出了自我可能分裂成多个自我的可能性。然而,更合理的是,自我可能会偶尔为另一个自我腾出空间。弗洛伊德主义者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发生,而且当它发生时,可能反映了深刻的精神病理学。
面对失去,我们都会带着某种悲伤和退缩而哀悼。我们大多数人最终都会痊愈。然而,有些人失去亲近的人后会陷入长期的、使人丧失能力的悲伤——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是“忧郁症”,或者我们现在称之为“重度抑郁症”。除了通常的哀悼症状外,深度抑郁的人通常会憎恨自己,声称对死亡负责,沉溺于对过往行为的内疚,并从事惩罚性的自毁行为。弗洛伊德写道,在健康的哀悼状态下,是世界变得贫瘠和空虚;在忧郁症中,则是自我本身变得贫瘠和空虚。
为什么哀悼会演变成令人沮丧的悲伤和自我憎恨呢?弗洛伊德认为,根源在于矛盾心理。哀悼者不仅爱逝者,也恨逝者。关键在于,失去让抑郁者潜意识里感到愤怒——对被逝者抛弃的愤怒,对他们之前的冲突的愤怒,对永远无法解决这些冲突的愤怒。出于愤怒,抑郁者在内心为逝者的一部分腾出空间。情感上的敌人消失了,别无选择,只能在内心重建逝者,然后继续这场战斗。
而且,正如弗洛伊德也观察到的那样,抑郁的哀悼者内化的不仅仅是逝者身上任何特征,而是那些最受憎恨的特征。弗洛伊德写道,如果一个人耐心倾听一个忧郁者许多不同的自我指责,最终就无法避免这样的印象:其中最激烈的指责常常几乎完全不适用于患者本人,但稍加修改,它们确实适用于另一个人,一个患者爱过、或曾经爱过、或应该爱的人。通过继承这些特质,人们仍然可以争论(你看,你难道不讨厌我那样做吗?你相信我忍受了50年吗?),并通过重度抑郁症的巨大痛苦,惩罚自己争论的行为。
因此,科学偶尔才会考虑自我分裂或萎缩足以容纳另一个自我的案例,即一个身体中可能居住不止一个自我的案例。对于一个自我占据多个身体的可能性,人们的关注甚至更少。总而言之,这些思考并未产生多少关于“自我”究竟是什么的科学确定性。
我自己对这个定义既不确定,也一直不特别感兴趣,直到最近父亲走到生命的尽头。那时,我突然感到自我界限在我耳边轰然崩塌。起初,我以为我可以使用科学话语来完全解释我的经历,将极端的表现视为病态。
随着父亲年迈,他遭受了继发于神经损伤的认知问题。他常常说不出是哪个十年,他身在何处,甚至他的孙辈的名字。他的自我界限也开始溶解,他逐渐窃取了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他独子的生活。我们之间早已存在相似之处。很久以前他曾从事医学研究,我现在也是。他曾是教授,我也是。我们一直共享品味、风格和性情,但现在我们生活的细节开始交织。当我搬到旧金山时,他1919年进入美国的地点从纽约的埃利斯岛变成了旧金山,他第一次看到美国时还包括一座尚未建成的金门大桥。他的医学研究因大萧条而中断,原是癌症生物学,但现在他充满了对神经生物学(我的专业)的空洞记忆。
我不认为这是竞争或我们之间需要更多的共同点——我们已经有太多的共同点了。很容易将我视为他的一个版本,没有难民身份、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厄运,享受着他痴迷的辛勤工作为我带来的回报,展望着可能长达半个世纪的未来生活,而他的阴影却越来越长。随着他的迷失感袭来,他 clinging to我的故事,越来越不确定他结束在哪里,我开始在哪里。
这感觉有点过于侵扰,但我用一套诊断方法和超然、居高临下的理解来保护自己。我会在脑海中想象自己讲课说:“这是痴呆患者的另一个特征,偶尔会见到……”晚上,他会在房子里焦躁不安地游荡,确信看到了愤怒的陌生人或早已去世的同事。他分不清我们俩谁爱上了加州红杉,这似乎是他最不严重的问题了。我想,别对他太苛刻了;他遭受了一些神经损伤。
他最近的去世把我从诊断的高高在上打了下来:突然间,是我自己有了界限问题。一开始还算 manageable。我开始说我父亲的口头禅,并模仿他的举止。这不是弗洛伊德式的忧郁症——虽然我很悲伤,但我并没有临床上的抑郁,而且我模仿的他的行为也不是那些几十年来一直用竞争性的冲动激怒我的行为。它们是那些微不足道的怪癖,正是它们造就了他。我发现自己像他一样摆放餐具,或者哼唱他最喜欢的意第绪语小调,很快我就放弃了自己的蓝色法兰绒衬衫,穿上了他的。我对他的职业——建筑学——产生了兴趣,心不在焉地画着我公寓的平面图。
起初,我的反应似乎很合理。年轻时,我会对体内带有他的一些痕迹感到恼火。然而,多年来,我已与我们的异同点和解,现在我觉得我可以向他致敬,而无需像以前那样充满怨恨。随后,事情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转折。
他去世后不久,我在家里哀悼了一周,遍布各处的硝酸甘油小瓶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最终的虚弱,这些小瓶都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我带了一个回加州,令人不安的是,我发现我需要随身带着它。我与妻子做爱,在健身房锻炼,参加讲座,这瓶药总是在附近。有一天我短暂地放错了地方,一切都停了下来,我焦虑地寻找。我感到一种紧迫的危险感。是我的心脏现在病了,还是我体内某个地方他病了的心脏,我警惕地守候着准备用药?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相信神、天使,也不相信灵魂转世。说实话,我也不相信灵魂,或者飞碟。是我的固执的个人主义让我对这种混淆感到不安吗?还是我父亲的个人主义?
一个月后,当我讲课时,混乱达到了顶点。尽管我的班级有400名本科生,人数众多且不近人情,但父亲去世后,许多学生表达了温暖和支持的慰问,我感到与他们亲近。在学年最后一节课结束时,我想告诉他们父亲是一位多么出色的讲师,传承一些我从他的教学中学到的东西。我本打算致悼词,但有些地方混淆了,很快,我穿着他的衬衫,替他讲课,说着一位八十岁老人的脆弱建议。
我警告他们,在雄心勃勃的计划中要预料到挫折,因为每一个承诺都意味着背弃许多其他的选择。我告诉他们,尽管他们想改变世界,但也应该为难以置信的事情做好准备——总有一天他们会感到疲惫。这不再是充满天真乐观的我,而是经历过风霜、充满失望的他。最后,我怀疑如此多的情感是否会引发他的一次心绞痛发作,我替他向一片充满生机和未来的20岁海洋说了再见。那天晚上,我收起了硝酸甘油。
那个月,我的脑海里充满了教科书中那些解释这种混杂现象的不太可能的疾病。现在,一年过去了,再次安全地回到了我个体化的战场上,那段经历对我来说开始变得更有意义。我确信我所经历的并不需要诊断,我也不再相信父亲对我们之间界限的混淆真的与他的神经问题有关。我作为一名科学家的训练所带来的病态后果是,我将无病之处视为病态;而我们时代的贫瘠在于,我只能将人类经验中固有的某种东西视为短暂的闪光。
我偶尔能够观察到那微弱的光芒燃烧得更旺盛。作为我研究的一部分,我在东非的一个野生动物公园断断续续地工作了17年。我经常陪同我的一位或几位非洲朋友回到他们依山而建的小村庄的家中。每次去,我都会发现我的朋友在家中也像我一样成了外人。我认识的那些人都是离开家乡的——次子,不安分的那些人,受过一些教育并在远方找到工作的人,他们发现自己用母语说话时磕磕绊绊,带着新的生活方式和一位白人朋友回家。
我的朋友们总是离开了同样的世界,一个世界里有一个人人皆知的典型老人,一个受伤的村里傻瓜在山坡上游荡,一个打老婆的酒鬼。在我朋友的家里,我总是会遇到他的哥哥,长子,那个留下的人。他坐在年迈的父亲旁边:两位农民,他们不说英语或斯瓦希里语,也许去过县城一次,但再没去过更远的地方。他们不耐烦地一起哼哼着,对我的朋友讲的一些关于大城市的夸张故事,半是觉得好笑,半是感到困惑。
这是一个没有我们西方个体化狂热的世界,在那里没有父母会认为“我希望我的孩子更好”,询问孩子长大后想做什么更是荒谬。在那里,没有人认为加入家族企业是独立性不足的担忧。在这个艰难的世界里,如果你最终能像你的父母那样耕种同样的土地,用同样的方式抚养孩子,或者像这些哥哥们一样,你变成了你的父母,你的身份融合了,那你就很幸运了。
托马斯·曼在他的小说《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中捕捉到了这种连续性,其中一位名叫埃利泽的老仆人以第一人称叙述了早期埃利泽(圣经族长亚伯拉罕的仆人)的经历。曼告诉我们,人们认为,老人的自我界限不甚清晰是正常的,它仿佛在背后开放,溢出到空间和时间上超出他个人性的领域;在他自己的经历中包含了那些……实际上应该用第三人称来描述的事件。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代的埃利泽变成了神话中的埃利泽,社区也期望他这样做。
每个传统社区都必须有其原型:埃利泽,智慧的仆人;以扫和雅各,为病弱父亲的祝福而战的兄弟;亚伯拉罕,原始的族长。这些需求超越了对一个有界限的自我的个人权利,传统社区中的人被命名并被培养成连续的化身。在这样的社会中,亚伯拉罕总是活了900年——他只是时不时地找到一个新的身体来居住。这不是杰恩斯所说的没有自我意识的二分心智社会。相反,自我存在,但它从属于更大、更部落化的事物。
我们不再敬畏延续性,要想感受到哪怕一丝闪光,就像我一样,需要一场情感危机,也许还需要一些磨砺。我的学生通常拥有像外骨骼一样的自我边界。他们大多不信宗教、不循先例、不重传统。他们希望自己的仪式是新近铸造的,在同龄人之间横向共享,而不是纵向传承。我培养成科学家的学生像战士一样投入,推翻主导范式,每一次发现都是对他们科学祖先的“谋杀”。如果我把他们训练得很好,那么我必须从有朝一日成为他们俄狄浦斯目标这一必然性中获得任何满足感。这些学生在相信他们可以在自身内部重塑世界方面,正处于成熟期的正确轨道上,如果他们碰巧发现自己对“我从何而止,他人从何而始”感到困惑,他们知道他们正在处理一些科学上、可证实的异常情况。
我自己也变得不那么确定了。我仍然可以没有宗教,但有些仪式会很好。还有其他的变化。我看着那些该死的孩子在我踢足球时飞奔而过,我支吾着回答一个高中生选手抢答的《危险边缘》问题。我的胡子开始变白;我的脊椎可能已经开始萎缩。再过几个生日,定期让医生检查我的前列腺将是明智之举。我开始觉得我那受自我边界限制的自我不再那么了不起了。
部落心态无法重新获得;我们无法回头。它只能作为一种被延续性包裹的感觉的回响,在我们的个体化世界中暗示着,对自我边界的一些困惑可能是一种健康的表现,是对敬意和爱的表达。像我父亲和我这样的经历,在我们不断扩展的科学标签中,是一堂关于过度病理化的风险的课。如果最终有人把你误认为是他,那可能也没那么糟糕——甚至可能是一种值得骄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