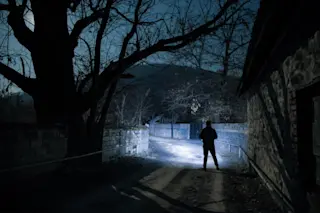不久前,我做了一个关于视力的实验。目的是体验一下处于视觉技术前沿的感觉。这项测试,幸运或不幸地,我非常适合进行。你看,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4岁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可怕的事故。我姐姐卡米尔和我拿到了两瓶那种老式的长颈百事可乐,瓶盖未开,装满了汽水。我们真是傻瓜,开始玩《三剑客》,用玻璃瓶击剑,像剑一样互相敲击。一块碎片飞进了我的右眼;卡米尔的腿也受了点伤(我们可怜的父母……)。手术挽救了我的眼睛,但我一直视力极差。我几乎只能勉强辨认出斯内伦视力表上最大的字母。

这些由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罗利分校的Wentai Liu和Chris DeMarco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开发的眼镜,有朝一日可能会与视网膜植入物一起,帮助盲人重见光明。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对象哈利·沃赫勒(Harry Woehrle)佩戴了这种眼镜:镜架上的微型摄像头传输模拟信号,该信号被数字化并——如果顺利的话——发送到大脑。
幸运的是我的左眼很好,但我想知道我的右眼能看得多清楚。我用棉花和胶带盖住我的好眼,然后散步。房间灯火通明。我能辨认出门口,把家具看成模糊的形状,足以区分椅子和桌子。我走到外面的报摊,买了Wint O Green LifeSavers,没有绊倒或摔倒。我不能看电视。我当然不能阅读。我不能真正认出人脸。但我能看到一个朋友张开双臂给我一个拥抱。
这不算多。但即使是我那只坏眼睛的视力,对像哈利·沃赫勒这样因视网膜色素变性(一种遗传性疾病,会破坏眼睛的光感受器细胞)而失明的人来说,也意味着整个世界。他年轻时就开始失去视力。现在他几乎记不起孩子们的脸。他最近再婚,却从未见过他的妻子卡罗尔。
今天,沃赫勒希望能再次见到他所爱的人。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威尔默眼科研究所眼内视网膜假体研究组的受试者,该研究组是人工视觉研究领域的领先项目之一——该领域旨在利用芯片驱动的微电极刺激盲人视觉通路中休眠的神经组织。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哈利可能会是第一批接受眼芯片测试的人之一。
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计划将豌豆大小的芯片阵列植入一小群像沃赫勒这样的盲人志愿者的眼睛中,作为一项为期一年的、经FDA批准的安全性和可行性试验的一部分。该阵列由信号处理器和微电极组成,它们将以与眼镜上摄像头捕捉到的世界视图相对应的模式刺激视网膜中的神经元。
没人指望奇迹。如果能让患者拥有我那只受伤的眼睛所能体验到的那种视力,那将被视为巨大的成功。“如果我们最终能帮助一些盲人仅仅看到一点点,足以让他们无需帮助就能四处走动,那将非常令人兴奋,”霍普金斯项目主任、眼外科医生马克·胡马云说。如果视网膜芯片植入物起作用,它们只能帮助一小部分盲人。(它对那些生来失明或没有功能性视神经的人没有帮助,因此其他研究人员正试图将模式化的电子刺激直接输送到大脑的视觉皮层,即视力实际形成的地方——参见“直达大脑”。)
眼睛是一个极其精巧、高度组织的器官,它实际上充当着数字图像处理器。不同频率的光线通过晶状体和角膜进入后,会射到视网膜,即眼睛后部的图像捕捉膜。视网膜厚度不足0.04英寸,但密度极高,有10层组织,包含超过100万个神经细胞和超过1.5亿个光感受器细胞——即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光子促使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释放出电化学脉冲。这些脉冲启动了一个信号处理链,将光线数字化为神经信息,然后通过视神经传送到视觉皮层。这条路径上的任何故障都可能中断传输。“人类用于视觉的感官处理电路与蝙蝠用于听觉的电路一样多,”正在为霍普金斯团队研究电子设备与视网膜之间接口的生物医学工程师詹姆斯·韦兰说。“替换哪怕是其中一部分电路,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团队和哈佛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同样杰出的团队都选择了一种“视网膜上”芯片,它将贴在眼球内壁上。成功远未得到保证,但对这个想法的信心部分基于人工耳蜗植入的成就,这种设备已帮助许多聋人重新听到声音。人工耳蜗植入有些令人困惑:科学家们不完全理解大脑如何能像它利用植入物提供的有限信息那样很好地识别语音。大多数耳聋的原因是“毛细胞”的损失——这些细胞像触角一样排列在耳蜗中,耳蜗是内耳的蜗牛形部分。在健康人中,毛细胞接收声音振动并将其转化为电化学信号,然后发送到听觉神经。人工耳蜗植入则通过麦克风和声音处理器接收声音,并将脉冲发送到耳蜗中的电极,电极再将信号传递给听觉神经。该设备已为25,000人恢复了一定程度的听力。

去年,这个微电极阵列被植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名人眼中。当阵列以E形图案充电时,患者成功看到了字母E。图片由眼内视网膜假体研究组2001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威尔默眼科研究所提供。
视觉研究人员寄希望于大脑在人工耳蜗植入后所表现出的惊人可塑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神经假体项目负责人威廉·赫特德克斯(William Heetderks)表示:“这项植入物让很多人想知道听觉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考虑到进入大脑的信息如此之少,植入物能发挥如此好的作用令人惊叹。”他补充说,如果大脑如此具有弹性,“视觉假体也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
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和霍普金斯大学团队设计的视网膜植入系统与人工耳蜗植入物的操作类似:数据被获取、编码,然后以模式刺激的形式传输。几乎相同的视网膜上植入物将这样工作:一个微型电荷耦合器件(CCD)摄像头,安装在眼镜架上,捕捉并数字化外部世界的图像。数字信号被发送到腰包,腰包提供电源并通过无线电波将数据传输到视网膜芯片。这个一英寸长的芯片,沿视网膜内壁弯曲,包含一个信号处理器和多达100个盘状铂电极,每个电极大约有人类睫毛尖端大小。来自CCD的解码信号控制电极的放电模式,这些电极刺激位于视网膜内表面下方的健康神经细胞。
尽管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系统,但这种方法充满了挑战——在功能完全的眼内芯片可用之前,还有大量工作要做。首先,没有人知道视网膜是否能容忍异物存在多年。眼睛很脆弱,难以抵抗感染。理想情况下,视网膜上芯片将是永久性植入,但霍普金斯大学的团队从未将芯片留在人眼内超过45分钟。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小组曾将阵列留在眼内几个月。这将是那种“只有一种方法能知道”的情况。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相信眼睛可以与芯片共存;他们更担心微电子设备浸泡在相当于一桶盐水——玻璃体液,即赋予眼球膨胀度的水凝胶中。“想象一下把电视机扔进大海里,”霍普金斯大学团队前成员罗伯特·格林伯格说。这只是问题的一半,可能是比较简单的一半。韦兰认为“人体会保护自己。我们需要做的是保护芯片免受身体的伤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团队为芯片设计了一个由钛和陶瓷制成的密封外壳,即使是比水分子还小的氦原子也无法穿透。
视网膜膜的精细程度,特别是再加上眼睛的快速运动,带来了另一个挑战。“将一块计算机芯片,这块硅片,放在视网膜上的想法是有问题的,”哈佛/麻省理工学院项目联席主任约瑟夫·里佐和约翰·怀亚特说。“视网膜是眼睛最脆弱的部分,你需要一种精细的方式与之沟通。将这块砖放在像湿纸巾一样的表面上,然后来回晃动湿纸巾——这不会是好事。”理想情况下,里佐说,需要一种机制,既能保持植入物的稳定,又能将设备悬浮在视网膜正上方。他的团队尝试了一种藏在虹膜后面的环形平台。该平台支撑植入物的信号处理器,而微电极阵列则通过硅酮涂层导线带轻轻地垂至视网膜,并由粘合剂固定到位。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打算使用微型金属钉来固定他们的植入物。
视网膜与刺激电极接触点的性质,提出了既涉及物理学又涉及生物学的难题。研究人员试图刺激的视神经元位于视网膜表面下方50至100微米处——仅相当于几根头发的宽度,但在细胞学意义上却是巨大的距离。足够强到足以充分刺激这些神经元的电荷可能会产生过多的热量,从而烧伤视网膜组织。然而,较小、较安全的电荷可能根本无法刺激神经元。研究人员还一直在努力解决使用何种频率和类型的电流的问题。由于视网膜组织会积累电荷,他们计划使用交流电,以便负相抵消电荷的正相,从而防止电荷在眼睛中积累。
最后,是电极大小的问题。科学家们在努力创造详细视觉时,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假设每个电极旨在创建一个像素,就像电视屏幕上那样。小电极将对神经细胞进行非常局部的刺激,从而可能产生更多像素和更清晰的图像。但由于小电极发出的电荷更集中,电荷更有可能烧伤视网膜。大电极则发出更安全、更分散的电荷,但会产生更大的像素和不那么清晰的图像。经过多年在人类和动物受试者身上的工作,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确定使用200至400微米大小的电极——实际很小,但仍然是人类神经细胞大小的10到20倍。目前,团队成员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折衷方案——合适的电荷水平、合适的频率,以及能够提供安全电荷和有用刺激的电极。其他人工视觉研究人员对此并不满意。“这些视网膜已经非常退化,为了使其产生反应,你必须比正常视网膜更强烈地刺激它们,”里佐说。“在我们的实验中,这种电荷量可能不安全。我认为这个问题将如何解决,目前尚不清楚。”

哈利·沃赫勒和他的妻子卡罗尔希望他能接受视网膜植入。“我一点也不害怕,尽管在植入物进去之前,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
即使研究人员克服了这些挑战,一个更大的问题依然存在:大脑能否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能理解一个健康、有视力的人头脑中发生的事情,那会有所帮助。但我们不了解。“没有人理解为什么以及感知是如何存在的。这是困扰神经科学的问题,”犹他大学皮层植入项目负责人理查德·诺曼说(见“直达大脑”)。“为什么停车标志被看作红色?为什么草是绿色的?没有人知道。”霍普金斯大学的受试者辨认出了盒子形状。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小组的患者,多年失明,看到了光斑。
这是一片未知的科学领域。现有的技术可以告诉身体改变行为:起搏器刺激心脏有节奏地跳动,电刺激器让四肢瘫痪者能够抓握,但这些设备仅仅引发肌肉收缩。人工耳蜗植入基本上是为大脑提供“食材”,然后让它自己“烹饪”。但人工视觉的目标是告诉大脑一些具体而明确的信息:我们正在按照代表门的模式激发电极——看,那是一个门。目前,这就像科学家在试图与大脑沟通时,给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外星人写纸条一样。“我们不知道语言,”里佐说。“这有点像拥有字母却不知道如何将它们组合成单词。我们甚至不知道所有的字母。在这项工作中,我们知道信号的频率和强度很重要,但毫无疑问,还有一些我们尚不了解的关键变量。”
霍普金斯大学的胡马云愿意让答案在植入物进入人体后自行揭晓。他将可用于商业的视网膜假体投入使用时间表定为三到五年。里佐表示,“如果能制造出一种安全且成功几率相当高的植入物”,可能需要五到十年。里佐的团队近期不打算进行试验。“率先实现固然好,但这并非首要任务,”里佐说。“要推进植入,研究人员必须高度确信设备能够安全地长期留在体内,并且有合理程度的信心认为该设备将为我们提供有用的信息并造福患者。目前,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就他个人而言,胡马云说:“我希望作为科学家,我们有足够的诚信和对患者的爱,不会草率行事,只为患者植入最好的设备。只要我们以道德的方式工作,并谨慎行事,我认为我们需要加快速度,以便数百万盲人能够尽快看到光明,我们希望如此。”
哈利·沃赫勒是同意这一观点的人之一。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想要进行这项试验。“我有九个孙子,”他说,“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一种遗传性疾病。谢天谢地,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任何问题。但如果我能做些什么可能对他们或后代的孩子有益,我全力支持。”
视觉的滋味
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人员没有试图复制眼睛的复杂功能,而是找到了一种将粗略图像传输到大脑的捷径。由保罗·巴赫-伊-里塔(Paul Bach-y-Rita)和库尔特·卡奇马雷克(Kurt Kaczmarek)开发的舌头人机界面是一个由微小金盘组成的小贴片,附在柔性带状电缆上,包含144个电极。该贴片可以连接到摄像头和发射器,并通过模式激活,在人的舌头上描绘出一个粗略的草图。
这个贴片可以放置在身体的任何部位,但皮肤并不是电信号的良好导体,所以研究团队选择了舌头作为理想的界面。舌头神经密集,并不断浸泡在导电性强的唾液中,它只需要指尖产生相同感觉所需电压的3%。
那些试用过这种贴片的人形容这种感觉是轻微的刺痛、振动或瘙痒。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使用模式脉冲来导航迷宫或识别简单的图形,并发现他们的大脑很快适应并开始“看到”场景。巴赫-y-里塔指出,“大脑非常具有可塑性”,因为它习惯于通过神经接收脉冲信息,“一旦大脑经过训练以视觉方式处理这些脉冲,它们是来自眼睛还是大脚趾都无关紧要。”
目前的原型看起来像一个宽大的、镶有电极的压舌板;巴赫-y-里塔计划在五年内建造一个更小的模型,它可以巧妙地隐藏在类似矫正器框架中。由此产生的图像可以提供相当于20/830的视力。“我不认为有人能够坐下来用这东西看电视,”他说,“但在识别形状和基本导航方面,它绰绰有余。” — 乔斯林·塞利姆和克里斯汀·索亚雷斯
谁的眼睛好?
如果你有老鹰的视力,你可以在一个足球场外阅读这篇文章。(缺点:你的眼睛将有网球那么大。)如果你有蜻蜓的视力,你可以把杂志放在脑后阅读。(缺点:眼睛有篮球那么大。)如果你有猕猴的视力,你可以在一英寸以内阅读这一页。(缺点:你会成为一只猕猴。)在所有生物中,我们的眼睛,嗯,还不错。“在1到10的等级中,我们大约是7分,”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兽医眼科医生菲利普·皮克特说。“猛禽是10分。老鼠大约是1分。它们善于探测运动,但也仅此而已。”正如皮克特所指出的,在视力方面,“最好”可以用几种方式定义。一个衡量标准是距离。鹰和老鹰可以在数百英尺高的空中发现田野里的老鼠。然后是颜色。人类能看到三种颜色——红色、绿色和蓝色。鸽子能看到紫色、蓝色、蓝绿色和黄色;蜜蜂能感知紫外线,使它们能够辨别花朵在产生花蜜时形成的紫外线颜色模式。这些进化适应使动物擅长于特定任务。人类的感官平衡进化,所以我们不依赖于任何一种感官。看不见的人的生活和任何人一样充实而丰富。事实上,可以说我们的发展受到了视力的限制。“想想早期的哲学和宇宙学是如何由我们所能看到的东西决定的——平地球理论、地心说等等,”国家动物园前园长迈克尔·罗宾逊说。“直到我们借助望远镜等工具扩展了我们的视觉能力,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在宇宙中的真正位置。” — G.C.
直达大脑
“我们不是用眼睛看,我们是用大脑看”是视觉研究人员最喜欢的一句格言——因此,直接接入大脑的视觉皮层似乎是向其发送图像最直接的方法。然而,大脑比眼睛复杂得多。神经科学家仍在努力弄清视觉皮层如何将来自眼睛的电脉冲编码转化为我们感知到的3D彩色动态图像。弄清如何模拟这种效果仍然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早在1929年,大脑研究人员就知道,将电极接触意识清醒的受试者的视觉皮层会产生光斑的感知,称为光幻视。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研究人员致力于开发视觉皮层假体,最终在1995年进行了一项人体实验。38个电极被植入一名42岁盲女的大脑,NIH团队试图激活它们。结果喜忧参半。研究表明,即使在失明22年后,仍能引发光幻视感知,并且可以从光幻视构建简单的形状。然而,该女性看到的光幻视的亮度和持续时间与刺激之间没有可预测的对应关系。到测试的第二个月,一半的细电极已经损坏。NIH停止了进一步的人体实验,结论是视觉皮层工作“尚未准备好在人类身上进行黄金时段的尝试”,美国国立神经疾病与中风研究所代理副所长奥黛丽·佩恩说。
如今,犹他大学的理查德·诺曼相信他即将通过他的犹他电极阵列(Utah Electrode Array)解决视觉皮层假体的潜在硬件问题。UEA是一个单一单元,大约0.16英寸见方,有100个硅电极,每个电极的宽度是人类头发的三分之一。UEA插入后,每个电极都嵌套在许多神经元之间,因此植入物随大脑在颅骨内的自然运动而浮动,从而降低了电极断裂或组织损伤的风险。由于电极尖端与神经元直接接触,产生光幻视所需的电量远低于眼芯片需要穿过视网膜组织才能发送有用信号所需的电量。诺曼认为,最终,一个625电极版本的UEA可以产生大约625像素的世界视图——可能足以阅读文本,并且可能足以导航日常地形。— 克里斯汀·索亚雷斯

要了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眼内视网膜假体研究组正在进行的研究,请访问 www.irp.jhu.edu。
麻省理工学院视网膜植入项目主页可访问 rleweb.mit.edu/retina。
有关舌头传感器以及照片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engr.wisc.edu/news/headlines/2001/Mar26.html。
理查德·诺曼的主页是 www.bioen.utah.edu/faculty/RAN,神经接口中心网页可访问 www.bioen.utah.edu/c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