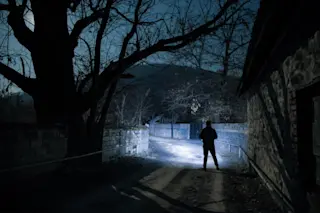在明尼苏达州的达尔文,现代朝圣者可以看到声称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人制作的麻绳球。这个球高十一英尺,重达 17,400 磅,陈列在一个有机玻璃的亭子里。那些在巴黎博物馆里消磨下午时光、徜徉在明代花瓶或恐龙骨盆中见多识广的肤浅之人,可能会认为一个麻绳球,无论多大,公共吸引力都有限。但达尔文镇的人们深知其价值,并将其作为一年一度的麻绳球日节庆的中心。这类事物并非特例。再看看密苏里州布兰森展示的由集体努力制作的世界上最大的麻绳球,周长竟达 41.5 英尺。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你可以找到世界上最大的铁丝网球,重达 5,290 磅。
为什么理性的人会想看这些东西?为什么平庸的表演者会被宣传为“独一无二”?为什么一张印有倒置飞机的百万分之一的邮票会价值数十万美元?又为什么我们无法抗拒看《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关于世界上最长胡须的照片?这并不是因为它们让我们反思人性的愚蠢。也不是因为挑战——“就这样了;我今天就不刮胡子了。”
为什么我们不仅被几乎任何东西的最大版本所吸引,也被最小、最奇怪、第一个、最后一个或唯一的版本所吸引?为什么仅仅因为稀有和真实的东西就会增加价值——看到乔治·华盛顿可能在渡过特拉华河时紧握过的餐具盒里的盐罐和胡椒罐被展示出来,那种奇怪的偷窥式快感?这仅仅是好奇心,还是有更深层的原因?
稀有性是情境问题。在马来西亚,Papilio palinurus(翠绿燕蝶)是濒危物种,但在南美洲常见的 Anteos menippe(柑橘菜粉蝶)身边,它看起来却很普通。
为了理解这种食欲,让我们考虑它是否有适应性优势,这个问题将把我们从明尼苏达州达尔文的麻绳球带到另一个达尔文。对稀有性和对比的 선택性反应似乎是我们感觉系统的特征,这种现象被称为对比增强。反复闻到同一种气味或听到持续的背景噪音,比如嘈杂的空调,相关的感觉系统就会开始适应,变得迟钝和无响应。然后,突然出现完全不同的东西,感觉系统就会被激活,甚至可能夸大新刺激与之前重复刺激之间的差异。白天走进明亮的房间没什么大不了。在黑暗中坐一个小时,然后走进那个房间,就会感到刺眼。
对比增强在捕食行为领域可能有一些优势。考虑一下鬣狗捕猎的原型方式。它会激起一群斑马跑起来,然后挑出那个与众不同的——最慢的。捕食者拥有心理学家所说的“搜寻图像”来寻找离群者。几十年前,一位在塞伦盖蒂的研究人员试图研究角马的个体行为。问题在于识别个体——角马看起来都差不多。这位研究人员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在草原上开着吉普车快速行驶,靠近一只角马,然后用一个连接着长杆的画笔,将颜料泼洒到动物的一条后腿上,留下独特且随机的图案。令他沮丧的是,他发现每只被泼了颜料的角马很快就成了捕食者的目标。这被称为“奇特效应”。捕食者必须擅长挑出年老体弱的动物,或者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挑出不同的动物。正如任何蝴蝶收藏家都可以告诉你,在一群棕色蝴蝶中捕捉一只黄色蝴蝶,比捕捉一只棕色蝴蝶更容易。
我们感觉系统的运作及其与捕食行为的相关性,可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对稀有的感官事件做出反应。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着迷于它们。它也不能告诉我们关于对思想和事实的稀有极端(而非感觉——比如一把钢琴会因为贝多芬曾弹过这些琴键而增加其珍贵性)的吸引力。
我们对神圣钢琴的迷恋将我们引向了哲学、心理学、语言和文化这些独特的人类领域。在这些领域,研究稀有和极端可以获得重要信息。它提供了范围,让我们知道某个测量值可以有多大或多小,这通常非常有益。假设你不会游泳,但不得不涉水进入一个浑浊的湖泊。知道湖的平均深度是两英尺是有用的。但了解一个极端情况——距离岸边约 40 英尺的一个泉水有 10 英尺深——则更有用。
地点,地点,地点
意想不到情境下的稀有性可能会令人震惊或不安。因此,我们很想在动物园里看到世界上最大的眼镜王蛇,但不会想在我们的淋浴间里看到它。1904 年的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展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活生生的“土著”——仿制的阿帕奇人、爱斯基摩人和祖鲁人的村落,还有人类学家宣扬土著人低劣的科学证据。对于那些兴奋地戳一下俾格米人以观察其反应,然后 seizes(夺取)他们微薄的财产作为纪念品的普通圣路易斯市民来说(在这次展览中这是一个常见问题),看到如此稀有人文文化是极其有益的,只要这些人是博物馆展品,而不是邻居——或者更糟,女婿。
尽管这种对稀有性的吸引力是一个引人入胜且开放式的智力问题,但它对环境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启示。其中一个启示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并非总能迅速发现稀有性。我们非常擅长识别一个与大多数其他事物不同的模式,或者得出结论说,绕在那个男人脚踝上的胡须是我们见过的最长的,但我们并不擅长识别过程。等到我们注意到某件事时——嘿,你有没有注意到野鸽子越来越少了?——可能就太晚了。几十年来,斯坦福大学的部分土地上的活橡树数量一直在下降,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些树能活几个世纪,只有生物学家才注意到幼苗的缺席。有多少个温暖的冬天和干旱的夏天过去,才有人注意到全球变暖?我们的神经系统已经进化到能够检测突然的变化,但稀有性,尤其是在其他物种中,往往是通过逐渐消失实现的。
另一个问题 arises(出现),因为我们对某些稀有迹象的情感反应不如对其他迹象。尽管许多自然爱好者被所谓的“最后的最佳之地”——即濒危生态系统——所吸引,但我们通常更关注动物而非自然系统,并且更关注某些物种——那些可爱、聪明或特别令人兴奋和危险的物种。因此,世界自然基金会使用大熊猫作为其标志,而不是维持熊猫生存的日渐消失的竹林。但是,如果不拯救它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你就无法拯救熊猫,而稀有的熊猫(或山地大猩猩或加州秃鹰)的吸引力有时会导致的干预措施,使得人们忽略了青蛙。为圈养的加州秃鹰保护投入的数百万美元将是徒劳的,除非创造一个能模拟其原始栖息地的环境——大量的、不含杀虫剂和有毒铅弹的大型尸体;很少有人愿意用枪射击任何移动的东西。普氏野马也是一个类似的情况。它被保存在动物园里,现在正在重新引入中亚。如果环保主义者放松警惕,这个物种可能会遭受其野生祖先的命运,在与家养食草动物的竞争压力下灭绝,并被饥饿的俄罗斯人吞噬。
翠绿燕蝶独特的绿色条纹是其翅膀表面微小的黄色凹坑和倾斜蓝色侧面产生的闪烁光学错觉。
稀有的诱惑还有另一个不常被谈论的生态启示,它尤其令我们担忧。想象一个国家拥有自然界中奇妙而稀有的东西。也许它甚至是最后一种。在该国的边界内,在一个公园或残余的野生地区,生活着最后的国宝熊猫或雪豹,最后的山地大猩猩或老虎群体,或者最后一百万头角马的迁徙群体——一些宏伟、备受赞誉且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一些游客会不惜重金前来朝拜的东西。
现在,假设由于愚蠢、短视、腐败和贪婪的综合作用,该国允许一半的稀有之地被挥霍以获取即时利润。过多的旅游小屋建在里面,产生了太多的废物倾倒到河流中。专制总统的一个表兄弟发现了在保护区边缘开展伐木或采矿业的利润丰厚。一个愚蠢的内政部长决定将国家公园私有化。允许进行少量打猎以收取高额许可费,当地人贿赂护林员让他们在公园土地上放牧他们的牛。有人从中赚了一大笔,这个稀有物种的家园就大大缩水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些暴行的消息最终会出现在关注环保的媒体上。也许他们会报道使濒危物种更加濒危的过程,或者也许他们只是专注于令人沮丧的最终结果。无论哪种情况,底线都是一样的:“婆罗洲最后的猩猩?”“非洲逐渐减少的大象群”,等等。所有这些都转化为同一个信息。如果你计划去看,尽快以任何代价去看,因为它正在迅速消失。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致命的悖论——如果你控制着一些著名、有磁性、稀有的巨大事物,并且为了快速获利而挥霍掉它的一半,那么剩下的那一半的价值就会翻倍。当然,在一定次数的减半之后,你会达到收益递减、无回报的点,指数级地滑向湮灭。但在此期间,挥霍行为却得到了回报,因为我们喜欢稀有。
不要将这种令人沮丧的供需例子与恶意剥削的经济学混淆——例如,偷猎减少了犀牛的数量,那么据说具有壮阳作用的犀牛角的价值就会增加,从而增加进一步偷猎的动力,并进一步提高其价值。这是一种更为微妙的稀缺性经济学变体,具有三个组成部分——滥用脆弱生态系统的即时经济回报,这种滥用造成的后果可以广为传播,以及许多西方人渴望看到、与地球上仅存的野生之地及其居民亲近的愿望,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这个悖论不仅适用于某种生态宝藏随着其稀有性增加而增值的情况,也适用于反向情况,即濒危物种在从灭绝边缘回归的过程中价值会下降。澳大利亚公司 Earth Sanctuaries 建立保护区并繁殖稀有动物以填充它们。公司的商业价值部分基于动物的价值,而动物的价值又与其稀缺性挂钩。每只濒临灭绝的袋鼠或袋狸都具有巨大的价值,但公司在建立其种群方面越成功,每只个体的价值就越低。在生物学成功和经济成功之间存在冲突,这使得 Earth Sanctuaries 很难对“治愈”濒危问题感到高兴,从而将自己置于破产的境地。
这里可能潜藏着一些解决方案,但它们既不明显也不容易。我们当然不需要治愈我们对稀有性的吸引力。那些一生积蓄只为去塞伦盖蒂旅行的人,也不应该感到道德上的义务而放弃。如果游客不支持生态旅游,这使得人们能够观赏塞伦盖蒂的更新世动物群,那么它们很快就会沦为食物,并被牛羊取代。一如既往,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在于最不可能实施它们的人:那些受益于这种扭曲经济激励的国家和组织。
很容易看出,我们对稀有的原始吸引力如何在最坏的意图下导致我们毁灭宝贵之物——如果有一天地球上只剩下一头野生大象,也不会缺少那些卑鄙之徒愿意出天价猎杀它。但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可能会在无意中帮助毁灭宝贵之物,并在此过程中损害我们的文明,而这却是在怀揣最好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