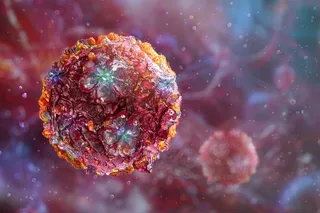2020年初,温德·戴尔(Wynde Dyer)走进了一栋将改变她一生的房子。这栋位于加利福尼亚中部的牧场坐落在一个封闭社区的尽头,拥有闪闪发光的碧蓝色游泳池。它拥有私人网球场和沙滩排球场、跑马场、落地窗和修剪整齐的草坪。整洁的外表掩盖了里面的景象。
房主是富裕的开心果农场主,他们有囤积问题。几十年来,他们积累了堆积如山的东西。然后他们搬走了,六年里几乎没有动过。戴尔接受了他们私人整理师的工作。当她到达时,她面对的是老鼠粪便、发霉的地毯、装满农用化学品和动物护理产品的车库、几十年前的洗漱用品和化妆品、无数盒香薰蜡烛、腐烂的木头和纸板——以及一具无法辨认的动物尸体。
然而,戴尔很擅长她的工作。当时39岁的她,已经从事家居整理多年,并计划将她的业务扩展到全国。戴尔以为这只是一份普通的工作,便卷起袖子开始干活。
但当她清理这些杂物时,她开始生病了。戴尔一直对环境很敏感。过去,她曾出现过轻微症状——小时候“鼻子里都是鼻涕”和阵发性疾病,成年后在整理其他房屋时出现皮肤问题和极度过敏。但在这位客户的家里,戴尔的症状加剧了。她暴露在外的皮肤开始灼热,仿佛被蒸汽烫伤。当她进食时,她的内脏感到灼烧,这种感觉她比作将外用酒精泼到开放性伤口上。皮疹爬满了她的手,手指肿胀得像浮肿的香肠,戒指勒进了她的肉里。有些日子,她醒来时被疲惫吞噬。有时,独自一人在她整理的房子里,除了她照看的一只流浪猫,她会晕倒。
戴尔去看了一位皮肤科医生,医生告诉她:“这可能只是湿疹。也许是晒伤。”然后给她开了一管可的松乳膏让她回家。一位胃肠病学家也同样无济于事。她的家庭医生束手无策。戴尔做了一次过敏测试,她的裸背暴露在80次含有不同过敏原的针刺下,结果全部都发作了。过敏症专家们感到困惑——他们从未见过病人对所有东西都产生反应。
戴尔依然出奇地专注于任务。她不得不如此——她身无分文,家里还有伴侣依靠她的收入。但坚持下去的本能不仅仅是为了钱。“我搞不清楚我的身体到底怎么了,”戴尔说。“我搞不清楚我为什么病得这么重。但我能搞清楚如何把东西整理好然后离开这里。”
随着她在房子里待的时间越长,她的病情就越严重,戴尔开始在网上寻找答案。在浏览论坛和博客的几个小时里,她的注意力被一个描述她确切症状的网站吸引住了。“天哪——这不就是我吗,”戴尔心想,“对现代世界过敏。”这个网站提到了她的几位医生曾随口提及但认为与戴尔的症状不符的观点:她的神秘疾病可能是由肥大细胞引起的。这些细胞是免疫系统中至关重要的第一反应者,存在于结缔组织中,而结缔组织几乎遍布全身:在我们的皮肤、肺、肠道、肌肉、神经,甚至大脑中。我们刚刚开始了解肥大细胞的是,常见的接触可能会导致它们在不应该激活的时候激活,从而对身体系统造成严重破坏。科学家们仍在努力找出原因。
肥大细胞的存在早于哺乳动物在5亿年前适应性免疫系统的发展。但对于如此古老的细胞,我们对其作用知之甚少。最初的理解曙光出现在1877年,当时一位年轻的德国免疫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正在接受医生培训。
埃尔利希正在完善一种新的细胞染色技术,这种技术能使细胞更清晰可见,从而更容易在显微镜下研究。在这项工作中,他发现了一种微小颗粒与染料发生反应的细胞。在显微镜下,这些充满彩色囊的饱满细胞在埃尔利希看来,就像它们滋养着周围的细胞。他将它们命名为“mastzellen”,即肥大细胞,因为在德语中,“mast”表示吸吮或增肥的功能。
直到20世纪50年代,我们才了解到肥大细胞会释放组胺,这是一种强效化学物质,导致过敏时的打喷嚏和流鼻涕,以及过敏性休克——当肥大细胞检测到过敏原,组胺和其他化学物质从细胞中喷发到血液中时引起的一种危及生命的反应。事实上,我们体内大量的肥大细胞含有足够多的组胺来杀死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倾向于认为肥大细胞是坏家伙,”哈佛医学院教授、临床医生和肥大细胞研究员玛丽安娜·卡斯特尔斯(Mariana Castells)说。科学家们看到了肥大细胞引起的问题,但无法解释这些细胞在我们体内的功能和重要性。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肥大细胞研究的爆炸式发展,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我们正处于理解肥大细胞生理作用的开端,”卡斯特尔斯说。我们现在知道,肥大细胞是免疫系统的前线哨兵,启动炎症并释放的不仅仅是组胺,还有数百种其他化学物质,称为介质,它们充当生物信号。当肥大细胞正常运作时,过敏原和病原体导致身体产生特异性分子,这些分子与像珠宝一样镶嵌在肥大细胞外部的蛋白质结合。反过来,肥大细胞释放出它们的化学信号洪流,引发一系列免疫系统过程。感谢其他德国科学家的研究,我们知道过敏的打喷嚏、咳嗽和瘙痒代表了肥大细胞的保护益处:清除体内的物质并在未来避免它们。
我们仍在研究肥大细胞为什么会行为异常。根据一种现有理论,如果一个人接触到大量或重复小剂量的化学物质,肥大细胞会对有毒物质做出反应,产生轻微的过敏症状。(有毒物质是人造物质,如杀虫剂,而毒素,如蛇毒,则存在于自然界中。)但肥大细胞会发生永久性改变,现在对一系列环境触发因素敏感,就像“细胞创伤后应激障碍”,戴尔说。这种现象的名称是肥大细胞激活综合征,或MCAS。根据细胞激活的位置,一个人可能会开始晕厥,爆发荨麻疹,出现几乎持续性腹泻,或者心率加快和呼吸困难——这些看似无关的症状,却有着相同的根本原因。
虽然像戴尔这样极端的病例相对罕见,但许多患有MCAS的人会出现中度或轻度症状。一位著名的MCAS医生劳伦斯·阿弗林(Lawrence Afrin)在学术医疗中心工作了几十年,然后加入纽约珀切斯的一家私人诊所,专注于MCAS。他估计,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已经治疗了数千名患有这种疾病的患者。由于MCAS的症状差异很大,而且很少有医生意识到这种阿弗林所说的可能非常普遍的疾病的存在,“几乎总是如此,它几十年都没有被识别出来,甚至可能伴随患者一生。”
阿弗林最早的一位患者曾患有未确诊的疲劳十年,以及全身突然发作的瘙痒。当她见到阿弗林时,她已经辗转于不同的医生之间,积累了大量的诊断,从血癌到贫血。许多相关的治疗都没有帮助。阿弗林为MCAS订购了实验室检查,最终显示患者的肥大细胞活动异常。
随着消息传开,阿弗林和少数正在不断增长的医生能够诊断出那些在大部分生命中没有得到解释或有效治疗症状的患者,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寻求帮助。阿弗林自己报告的病例包括:一位34岁的学校老师,总是疲惫和寒冷;一位24岁的患者,患有慢性头痛和时好时坏的狼疮样症状;几位被诊断为镰状细胞性贫血的患者,他们的疾病过程异常严重,因为他们还患有未诊断和未治疗的MCAS;以及一位50岁的医院工作人员,伴有盗汗、疼痛、瘙痒、眼睛刺激和体重增加。根据症状、实验室检查和治疗,他们最终都被确定患有MCAS。
如今,研究表明MCAS影响着数量惊人的人——在工业化国家中高达17%的人口——并且可能解释许多医学上神秘的症状,从良性皮疹到胃肠道症状、疲劳、肿胀、流鼻涕和喘息等等。
但阿弗林认为MCAS是一个普遍问题的观点仍然存在争议。
卡斯特尔斯担心医生在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之前,就急于诊断MCAS。MCAS的诊断可能很棘手,尤其是因为像COVID-19和莱姆病这样的疾病也可能触发肥大细胞活化。即使对于那些专门研究复杂慢性病的人来说,理清重叠的症状就像解开一团缠结的头发。卡斯特尔斯强调,每位MCAS患者所需的时间远超过临床就诊的通常分配时间。“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接纳对这些患者的评估,”卡斯特尔斯说,但“这些患者需要时间。”
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临床教授兼肥大细胞专家赛姆·阿金(Cem Akin)指出,17%的MCAS患病率数据使用了“过于宽泛”的诊断标准。德国波恩大学的医生兼教授格哈德·莫德林斯(Gerhard Molderings)和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向随机抽样的德国公民发放问卷报告症状,而不是通过进行确认MCAS所需的广泛实验室测试,得出了这一估计。阿金说,这种方法可能会将患有各种不同问题的患者归入MCAS这一大类。
当阿金本人在2018年审查代表3000万患者的保险理赔时,他发现每10000名患者中只有不到1人患有MCAS。虽然他承认随着患者权益团体争取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这个数字可能有所增长,但他仍然认为17%的估计值过高。“说17%到20%的人口会出现局部肥大细胞活化,这没错,”阿金说——这意味着由这些组织中肥大细胞活化引起的皮疹和喷嚏——但“我们不会称之为肥大细胞活化综合征。”
阿金不怀疑他的病人正在遭受痛苦。“他们确实有问题,一种真正的疾病或一组疾病,”他说。“他们有真实的症状。”但他依靠客观标准——症状、实验室证据和对治疗的反应——来做出MCAS诊断。
然而,阿弗林认为,过于狭隘的诊断标准可能会将患有该疾病的患者排除在外。MCAS不遵循单一模式,这使得该疾病难以识别和诊断。一些实验室不具备处理这些测试的设备,并且经常提供假阴性结果。因此,医生有时仅根据症状和对治疗的反应来诊断MCAS——就像帕金森病等其他疾病的诊断方式一样。
部分问题也可能在于缺乏认识——治疗MCAS的医生圈子很小。2018年,一群不到二十名MCAS专家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会议,并启动了一个医生邮件列表,以分享治疗该病症的知识。该邮件列表此后已发展到包括全球600多名医疗服务提供者,但接受保险的却不多。保险公司很少报销诊断和治疗MCAS患者所需的长时间费用,吉尔·斯科菲尔德(Jill Schofield)说,她是一位在丹佛创办私人诊所治疗MCAS和其他复杂疾病的医生。“我们的医疗模式不适合这些问题。”
互联网和患者倡导团体加速了对MCAS的认识,但很少有医生接受过正式培训来识别这种疾病,因为医学院课程只对肥大细胞疾病进行了一瞥。一些医生,包括戴尔的一些医生,几乎没有听说过它。阿弗林说,他经常接到医生的电话,他们说:“哦,天哪,你是对的。我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左右看到这种情况。我以前只是无法识别它到底是什么。过去我总是把这些病人当作有点疯癫。”
戴尔从小住在一个低收入版本的房子里,那里的环境在她成年后引发了她的症状。天花板因水渍而下垂,霉菌使墙壁变成灰色。此外,戴尔和她的家人住在加利福尼亚肥沃的中央谷大片农田的一英里范围内。她的祖父年轻时是一名农药喷洒员,戴尔记得他们两人开车穿过田野,飞机飞过头顶时,他们会停下来把头伸出窗外,农药洒向大地和戴尔。对她来说,那些农药喷洒机很神奇,从空中俯冲下来,喷洒那些从地里冒出绿叶的蔬菜。
但这些接触完全有可能让戴尔为几十年后降临在她身上的健康灾难埋下伏笔。当她走进那座车库里堆满杀虫剂、地毯散发着水渍霉味的本世纪中叶豪宅时,她的身体做出了反应——或者说过度反应——产生了巨大的免疫反应。她的肥大细胞释放出它们的化学颗粒——组胺和肝素、蛋白酶和前列腺素、类胰蛋白酶和糜蛋白酶,以及数百种其他分子警报——让戴尔病得越来越重。
在某些方面,戴尔是幸运的。在MCAS被识别之前,患有当时被称为“多种化学物质敏感症”或“环境疾病”的患者被认为是妄想症。(那些认真对待他们的医生也冒着职业风险。在20世纪50年代,一位治疗这类患者的医生被西北大学医学院开除,因为他“对医学生产生了有害影响”。)但少数研究人员坚持了下来。在20世纪70年代,过敏症专家兼环境科学家克劳迪娅·米勒(Claudia Miller)正在研究有毒物质如何影响工业环境中的人们,并开始注意到某些类型的化学物质暴露后出现的奇怪症状。到了90年代,她观察到海湾战争老兵在部署期间接触了多种危险物质,回来时出现了一系列症状:疲劳、头痛、关节疼痛、消化不良、失眠、头晕、呼吸系统疾病和记忆问题。一些老兵向米勒报告说,他们以前喜欢工业润滑剂WD-40的味道:“对他们来说就像香水一样,”她说。但在战后,仅仅闻一下就让他们生病了。
米勒还遇到过接触农药、乳房植入物、焚烧坑和化学品泄漏产生的有毒烟雾的人。后来,许多人对环境变得高度敏感,受到以前不曾困扰他们的食物、香料、废气和清洁剂的触发。这种模式——在接触后身体多个部位突然生病——似乎预示着一种新的疾病模型。
米勒对这种现象背后的机制一无所知,直到有人向她提到了拉里·阿弗林(Larry Afrin)关于MCAS的工作。他们开始合作,制作了针对化学不耐受和MCAS之间惊人相似之处的材料。他们的患者群体在身体系统上经历了广泛的症状,但以前没有人将这些群体联系起来。通过仔细的评估,米勒和阿弗林发现,最有可能患有肥大细胞激活综合征的人也极有可能对化学物质不耐受。在高端方面,这种重叠几乎是完美的——这是一个突破。在医学边缘工作了几十年之后,这些科学家找到了化学不耐受的可能机制:肥大细胞激活。
化学不耐受与肥大细胞激活之间的联系具有先见之明(尽管像赛姆·阿金这样的科学家正在等待经验数据来证明这种联系)。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被诊断出的化学不耐受率翻了两番,影响了美国超过八分之一的成年人。这相当于超过2500万人,比德克萨斯州的人口还要多。在这项研究中接受调查的成年人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报告对化学物质敏感。
这些数字可能会增加。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工业化的产物——塑料、合成香料、化石燃料、建筑材料和重型化学品。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领导的一项2021年《自然》杂志研究表明,在气候变化中,我们对花粉和霉菌的接触已经增加。热带风暴、飓风和洪水造成的水灾导致全球霉菌接触增加。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07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卡特里娜飓风和丽塔飓风袭击新奥尔良后,真菌生长增加到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水平。几十年的研究表明,杂草和害虫在二氧化碳增加和气温升高的情况下会茁壮成长,从而增加了对杀虫剂和除草剂的需求。《全球农药地图集》报告称,从1990年到2017年,农药使用量增加了80%。
所有这些暴露共同构成了专家们所说的“暴露组”:我们从受孕到死亡在环境中接触到的一切,以及这些暴露与健康的关系。虽然有些人可以承受更多的有毒暴露,但像戴尔这样的人却因此而残疾。
一旦戴尔的在线研究表明肥大细胞是她疾病的元凶,她就想要证据。几个月来,她的医生一直将她的症状视为夸大、身心失调或无法解释。她记得当她皮肤灼痛时被告知“你只是有点荨麻疹”,当她恳求答案时被告知“我们找不到任何东西”。“根本就没有,比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戴尔说。
在她生病几个月后,她恳求她的家庭医生将她转介到该地区为数不多的肥大细胞专家之一。在专家诊室里,戴尔详细描述了她复杂的症状矩阵,医生专注地听了几个小时,做着笔记,偶尔提出问题——关于戴尔在哪里长大,她何时第一次注意到健康问题,她的症状如何随着时间进展。这是第一次有人认真对待戴尔。
她回家完成了棘手的诊断测试,该测试将检测她的肥大细胞释放的组胺和前列腺素,这是MCAS的“指纹”。24小时内,她将尿液收集在一个罐子里,然后塞进冰箱以保存对温度敏感的化学物质。
然后,戴尔必须提供一份最终的尿样,模拟“发作”时的状态,即肥大细胞释放大量介质。在几个月的病痛中,戴尔学会了避免触发她症状的暴露。现在,她故意去寻找它们。她开车去家装中心时,嗅了嗅一杯蓝色的洗衣液。然后,她径直走向木材区,她的皮肤随即感到剧痛,“就像有人把汽油泼在上面一样,”她说。她原本计划在百货公司的香水柜台停留,但她已经把自己弄得病得很厉害——一次成功——所以她开车去了实验室。
她期待已久的结果显示,前列腺素水平很高,这是MCAS的一个典型标志。但她不得不重复检测,才发现她的组胺水平也比上限高出六倍。她的肥大细胞正在失控,对香水、洗涤剂和木材做出反应并释放信号,而正常肥大细胞会将这些视为无害物质。在她的健康状况开始螺旋式下降近一年后,她得知自己患有肥大细胞活化综合征。
戴尔的医生开了一种简单的治疗方法:抗组胺药。这些药物通过阻断体内对组胺做出反应的受体来减轻组胺的作用。戴尔以前曾尝试过非处方抗组胺药,但她对药物本身产生了反应,这很可能是因为药片中含有填充剂。另一种治疗方法是稳定肥大细胞膜的药物。这些被称为肥大细胞稳定剂的药物可以抑制组胺和其他炎症介质的释放。当戴尔开始服用处方抗组胺药和稳定剂时,她的症状显著改善,尽管普通化学物质仍然可以引发发作。
托马斯·普卢姆(Thomas Plum)在德国癌症研究中心研究免疫学,并领导了关于肥大细胞保护益处的开创性研究,他希望他的研究能为更好的治疗方法打开大门。“你首先需要了解事物是如何运作的,才能真正进行干预并设计出好的疗法,”他说,而“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充分。”现在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肥大细胞的机制,我们开始看到针对这些通路进行创新的治疗方法。单克隆抗体可以消除触发肥大细胞的信号。某些维生素可以降解组胺,甚至减少肥大细胞增殖。一些生物活性化合物,如黄酮类化合物(存在于许多食物中,包括浆果),可以减少肥大细胞活化。
如今,戴尔住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在一家保健食品店工作,这让她能负担得起不会让她生病的食物。她不再整理房屋——对她的健康风险太高了。多年来,戴尔一直试图避免所有她知道会引发发作的事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想找回她以前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朋友的沙发闻起来有清新剂的味道,她也会睡在那里,偶尔也会化妆,并且拒绝孤立自己。“除非你活在真空里,否则没有办法避开它,”戴尔说。“而唯一能负担得起活在真空里的人,就是有钱人。”
尽管如此,这种疾病还是扰乱了戴尔的生活。“我会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巨大潜力的人,”她说,“而这种潜力已经被这种疾病带来的精神、身体和心理影响所劫持。”
她不能再做她热爱的私人整理师工作了。她从事着最低工资的工作,收入不及以前的一小部分。她不住在没有霉菌的房子里,也不遵循昂贵的低组胺饮食。她住着和吃着她能负担得起的一切。她没有实现她作为艺术家和企业家的梦想——她的事业在她生病后停滞了。相反,她每天醒来的目标是活下去。
这不是她想象中的生活,但她生病前的生活已经不复存在。“我必须关上那扇门,”戴尔说,“我必须康复。”
本文不提供医疗建议,仅供参考。
本文发表于2025年7月和8月印刷版。
凯特·拉斐尔是旧金山湾区的一名科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