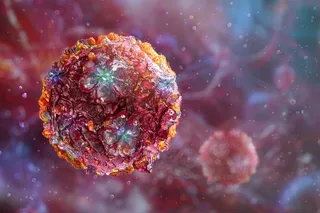这些天黑色素成为新闻焦点。有一种伪科学的观点认为,如果你有很多黑色素——给你的皮肤、头发和眼睛虹膜上色的色素——你就会聪明,对生命节奏非常敏感,并且拥有热情、外向的个性。简而言之,你将比黑色素较少的人(即白人)更友善、更有才华。
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例如纽约城市学院黑人研究系主任伦纳德·杰弗里斯,他们的结论基于一个单一的科学事实,即黑色素不仅存在于皮肤中,也存在于大脑中,他们利用这种化合物的存在赋予它魔幻般的特性。他们的“黑色素主义”方法已经超越了少数小册子和密室辩论的传播范围;它现在正在美国的一些高中和大学中教授,通常作为纠正欧洲中心世界观的努力的一部分。不出所料,这些项目在主流白人主导的媒体中引起了大量批评——黑色素主义者声称这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表现。他们反驳说,为什么对白人生物优越性的主张没有提出同等程度的不满呢?
当然,两个错误并不能构成一个正确。作为对白人种族主义的反击和解药,黑色素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从科学角度来看,它就是错误的。没有证据支持黑色素主义者关于黑人优越性的主张,就像没有证据支持几个世纪以来关于白人优越性的伪科学主张一样。这并不是说黑色素不适合进行科学探究。恰恰相反:研究表明,黑色素的真实故事比任何用来支持种族间分歧的魔法骗局都更有趣,并且更能说明我们自己。
我们是视觉导向的动物,陌生人的肤色,如果与我们自己的不同,往往是我们首先注意到的特征。在我们之间所有肤浅的差异中——鼻子的形状、头发的质地等等——似乎没有什么能像肤色一样让我们着迷。我们对它的高度意识不仅塑造了我们对他人,也塑造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正如心理学家所表明的,至少在这个国家的黑人中,一个群体或家庭中肤色最深的孩子往往比其他孩子受到老师、同伴甚至父母的待遇更差,因此自尊心受到反复打击。显然,肤色差异对社会影响巨大——但这些差异所产生的偏见和心理伤害是否有任何生理基础呢?
今天,像我这样的遗传学家会说不。几十年来我们已经知道肤色差异是由相当小的基因差异引起的,而且这些差异与智力、个性或能力有任何关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可悲的是,遗传学本身并非一直没有种族主义的污点。早期遗传学家用来解释肤色遗传的模型实际上带有隔离主义的偏见,反映了他们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偏见。美国白人优生学家查尔斯·本尼迪克特·达文波特在1913年通过对“黑白混血儿”遗传学的一项调查奠定了基调(可以这么说)。达文波特和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是种族主义者,他认为黑人劣于白人。然而,他确实正确地推断出有控制肤色的独特基因。但他认为只有两个基因参与其中,每个基因都有两种形式,或等位基因:“白色”等位基因和“黑色”等位基因。你的肤色深浅取决于你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四个等位基因中有多少是“黑色”的。
达文波特认为黑色和白色等位基因彼此截然不同,就像他认为黑色和白色种族本身彼此截然不同一样。我们现在知道这并不正确,不同种族携带的等位基因之间的差异很小。但达文波特在他的结论中是正确的,即相当少量的基因对肤色有实质性贡献——结果证明不止两个,但少于六个。而且,正如他所注意到的,肤色是独立于其他用于区分种族的特征而遗传的。在异族通婚的孙辈中,他看到通常有皮肤白皙但头发紧密卷曲的人,也有皮肤黝黑但头发直顺的人。因此,肤色和头发质地并非不可分割。
达文波特对基因如何运作一无所知,因此不知道他的黑色等位基因如何导致色素形成。直到最近,分子水平的研究才表明种族之间等位基因差异是多么微小,以及我们所有人从南太平洋布干维尔岛民的深色皮肤到瑞典人的苍白皮肤所需的步骤是多么少。
我们了解到的是,色素形成的机制异常精妙。黑色素细胞,即形成色素黑色素的细胞(有时会失控,导致恶性肿瘤,称为黑色素瘤),与神经细胞密切相关。两种类型的细胞都起源于早期胚胎中称为背外胚层的一部分,但神经细胞主要留在原地形成神经系统的核心,而黑色素细胞则与其他细胞一起迁移形成皮肤。随着它们的成熟,黑色素细胞和神经细胞继续共享一些属性。像神经细胞一样,黑色素细胞也会形成分支过程,附着在附近的细胞上。但是,神经细胞利用它们的分支发送信息,而黑色素细胞则利用它们的分支向相邻的皮肤细胞发送色素包。一个黑色素细胞可以通过将色素泵入与其相邻的细胞来着色相当大一部分皮肤。
我们现在知道,在小鼠中,有超过50种不同的基因影响黑色素的形成方式以及何时何地沉积。因此,人类中也可能出现类似数量的基因,尽管可能只有大约六个基因被证明具有真正显著的影响。它们产生的色素,虽然都被归类为黑色素,但实际上可以是黑色、棕色、黄色或红色。它们都以酪氨酸为共同起点,酪氨酸是一种在黑色素细胞中大量产生并由酪氨酸酶转化为称为多巴醌的化合物的氨基酸。起初,生物化学家认为多巴醌随后会发生自发化学变化,形成构成黑色素的长聚合物分子。但事实要复杂得多——从多巴醌到黑色素需要令人眼花缭乱的反应混合物,有些是自发的,有些是由酶催化的。长话短说,多巴醌遵循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通向黑色和棕色色素,另一条通向红色和黄色色素。
所有这一切中的主导酶是酪氨酸酶。如果这种酶的基因有缺陷,结果就是患有白化病的人,他们根本不产生黑色素。但分子生物学家最显著的发现是,我们大多数人,无论肤色如何,我们的黑色素细胞中都有足够的酪氨酸酶,足以让我们变得非常黑。在皮肤白皙的人中,有些东西阻止了这种酶充分发挥作用——这似乎是两种遗传机制的结合:一种导致细胞制造大部分酪氨酸酶处于非活性形式的开关,以及一种制造大量酶抑制剂的倾向。在体内,这两种或两种机制的影响都可以通过紫外线照射等环境因素来改变。白化病患者对紫外线高度敏感,紫外线很容易损伤皮肤和眼睛,但我们大多数人,无论我们拥有哪种肤色等位基因,都可以通过晒黑来保护自己。
因此,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区别并非是不同数量的明显不同的黑白等位基因,而是我们所有人所拥有的基因在调控方式上存在一系列微小的遗传差异——例如,有多少酪氨酸酶以活性形式产生,以及产生多少和多少种各种酪氨酸酶抑制剂等等。具有显著影响的突变确实会导致人类群体中的颜色变异——例如,白化病患者不产生功能性酪氨酸酶,而红发人只产生少量酪氨酸酶——但这些突变仅影响相对少数人。其他使肤色变浅或变深的突变偶尔也会发生。例如,患有白斑病的儿童出生时前额有一缕白发,额头和躯干有无色斑块。另一个更显著的例子是黄褐斑,这是一种有时会家族遗传的皮肤病。患有这种疾病的儿童出生时皮肤上有一些比正常颜色深的斑块,这些斑块随着儿童长大而扩散。在1970年代后期,墨西哥描述了一种更不寻常的疾病:一个孩子出生时皮肤白皙,到21个月大时皮肤变成了深色、均匀的黑色。(目前尚不清楚这种疾病是否遗传。)
此类突变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明尼苏达大学的分子遗传学家理查德·金(Richard King)曾研究过小鼠的颜色变异,他怀疑人类身上也必然发生更轻微的突变,但它们往往被忽视,因为它们落在正常色素沉着的范围内。他确信我们不能幸免于在进化过程中反复导致动物出现更浅和更深品种的突变和选择过程。这种进化的最著名例子是蛾类的工业黑化症,在这种情况下,由突变产生的深色形式在污染区域被选择,而在污染消失时则被淘汰。
在动物中,黑色素的增减受进化压力的支配。因此,可以合理地假设,我们人类拥有这种分子,并非因为它使我们更聪明,而是因为它主要有助于我们在各种环境条件下生存。显然,黑色素保护我们免受紫外线的侵害。世界上一些色素最深的人,如北所罗门群岛的土著居民,几乎从不患基底细胞癌或黑色素瘤,如果他们确实患有黑色素瘤,这些肿瘤也会出现在他们脚底白皙的皮肤上。另一方面,居住在夏威夷的高加索人拥有美国记录的最高皮肤癌发病率。
虽然拥有大量黑色素的保护作用是明确的,但为什么许多生活在远离赤道的人群会失去大部分色素,这一点却不太清楚。一种流行的理论基于这样的事实,即皮肤细胞暴露在紫外线下对于维生素D前体的形成是必需的,而维生素D前体又对于正常的骨骼形成是必需的。因此,该理论认为,生活在高纬度地区的人们——那里太阳低垂,人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必须遮盖皮肤——如果皮肤中含有少量阻挡紫外线的色素,他们仍然可以制造足够的这种前体。反之,热带地区人们皮肤中的大量色素应该可以防止他们产生过多的维生素D,过多的维生素D与过少一样有害,并可能导致组织中不适当的钙沉积。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大多数人拥有使我们变成黑色、白色或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切机制是合乎情理的。深色和浅色的动物“种族”非常普遍,可能是在应对捕食危险时产生的。科罗拉多州的深色和浅色斯塞洛普蜥蜴甚至会在实验室环境中移动,以使自己与适当的背景相匹配,这是一种本能的尝试,以保护自己免受目光敏锐的捕食者的侵害。我猜测,在数亿年的时间里,我们的远古动物祖先不得不反复改变颜色,原因多种多样,从保护性伪装到性吸引力。其中大部分一定发生在他们拥有足够的智力来对此产生偏见之前很久。
即使在《智人》中,也有许多群体向比其近亲更浅或更深的肤色进化的例子。例如,菲律宾吕宋岛和棉兰老岛的尼格利陀人,表面上类似于非洲和澳大利亚的其他深色皮肤群体。然而,他们的整体基因亲缘关系却与他们周围的浅色皮肤亚洲人更强。这表明尼格利陀人的祖先可能曾经是浅色皮肤,并且他们独立进化出与黑非洲人有些相似的特征,或者他们周围的亚洲人也曾经更黑,并进化出更浅的皮肤——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另一个例子是日本北部的阿伊努人,他们皮肤白皙,但在基因上与他们周围的深色皮肤群体非常相似。肤色的进化显然不是一次性事件;它在人类物种的历史中反复发生。
至于我们大脑中发现的另一种黑色素——神经黑色素,杰弗里斯和他的黑色素主义同伴们对此大做文章。他们暗示,更多的皮肤黑色素必然意味着更多的脑部黑色素——这以某种未定义的方式是好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黑色素细胞和神经细胞确实在胎儿中有一个共同的起源,而且神经细胞很可能曾经从原始黑色素细胞进化而来。但这种进化联系并不意味着皮肤色素与大脑功能有某种联系。患有白化病的人,皮肤、头发或眼睛中没有黑色素,但他们的大脑细胞中含有正常量的黑色素。尽管两种黑色素的最终来源都是酪氨酸,但导致神经黑色素的加工途径与导致皮肤黑色素的途径截然不同——在大脑中,酪氨酸被转化为多巴胺,一种神经递质,进而产生神经黑色素。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虽然神经黑色素本身在大脑组织中高度可见,但它只是大脑特有的数千种化合物之一,不太可能被赋予神秘的意义。
至于脑部黑色素的真正意义,目前尚无定论——我们不知道它的作用。我们确实知道它大量存在于黑质(“黑色物质”)中,这是一个埋藏在大脑深处的深色结构,负责制造多巴胺。我们还知道,黑质中富含黑色素的细胞最有可能在帕金森病患者中被破坏,导致震颤和僵硬。但这种优先破坏是由于神经黑色素的某些特性,还是由于恰好破坏富含神经黑色素细胞的其他过程,目前尚不清楚。清楚的是,神经黑色素与皮肤色素没有明显的关联,更不用说与热情、外向的个性有关了。
尽管如此,黑色素可能带来我们尚未了解的一些益处。有趣的是,有迹象表明,皮肤黑色素含量高的人比皮肤色素较浅的人更不容易受到听力损伤。事实证明,皮肤中的黑色素确实存在于内耳耳蜗的某些细胞中。但是,是黑色素还是这些细胞中的其他物质提供了保护作用,尚不清楚。黑色素还与吸烟的一个奇特益处有关。烟草烟雾会刺激皮肤黑色素的产生,特别是在口腔内衬细胞中,可能也在其他组织中。一项研究甚至表明,吸烟者比非吸烟者患噪声引起的听力损失更少(然而,其他研究则显示相反的结果)。即使有益处,也几乎不足以证明养成这种习惯是合理的,尽管吸烟者会感到安慰,因为如果增加黑色素的产生确实能保护他们的听力,他们也许就能继续听到他们受损肺部的每一次喘息和嘎吱声。
显然,黑色素是一种方便而迷人的化合物,具有引人入胜的进化史。但由于其在我们的皮肤上如此明显的作用,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承载着完全不应有的社会学和政治意义的重担。正如本期其他地方所详述的,构成我们称之为种族的这些随意构建的人群之间的遗传差异,远多于种族之间的差异。是时候摆脱用单一分子来解释我们所有差异的简单化努力,并关注构成我们奇妙复杂细胞——以及自我——的数万种其他分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