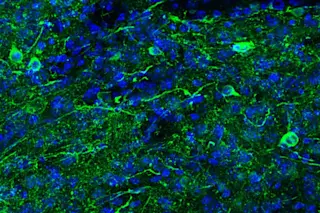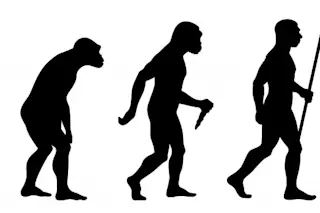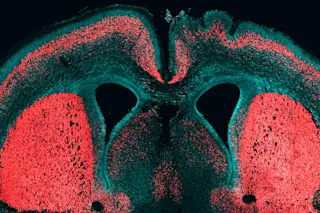有趣的故事常常隐藏在那些看似反复无常或被误解的名字中。例如,为什么政治激进分子被称为“左派”,而他们的保守派同行被称为“右派”?在许多欧洲立法机构中,最受尊敬的成员坐在主席的右侧,这遵循了一种与我们偏爱大多数人惯用右手一样古老的礼仪习俗。(这些偏见根深蒂固,远远超出了开罐器和剪刀,甚至延伸到语言本身,其中“灵巧”源于拉丁语的“右”,而“不祥”源于拉丁语的“左”。)由于这些受人尊敬的贵族和巨头倾向于支持保守观点,立法机构的左右翼便定义了政治观点的几何学。
在我自己的生物学和进化领域中,在这些看似反复无常的名称中,没有哪个比将欧洲、西亚和北非的浅肤色人群正式命名为高加索人更奇特,也没有哪个在讲座后引起更多问题。为什么西方世界最常见的种族群体要以横跨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山脉命名?约翰·弗里德里希·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这位德国解剖学家和博物学家,于1795年在他划时代的著作《人类自然变异论》(De Generis Humani Varietate Nativa)第三版中发明了这个名字,他建立了最具影响力的种族分类。布鲁门巴赫的定义引用了两个选择此名的原因——这个小区域的人们拥有极致的美丽,以及人类最初很可能是在这个地区被创造的。
高加索变种。我从高加索山脉取了这个变种的名字,既因为其附近,特别是其南坡,产出了最美丽的人种,我指的是格鲁吉亚人;也因为……在该地区,如果说有哪里的话,似乎我们最有可能将人类的本土形式(autochthones [original forms])置于此处。
布鲁门巴赫是启蒙运动中最伟大、最受尊敬的科学家之一,他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担任教授,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他于1775年,当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民兵开始美国独立战争时,首次将《人类自然变异论》作为博士论文提交给哥廷根医学院。随后,在1776年,当费城一场决定性的会议宣告美国独立时,他再版了该文本以供公开发行。1776年三份伟大文献的巧合——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关于自由政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关于个人主义经济学)以及布鲁门巴赫关于种族分类的论著(关于人类多样性科学)——记录了这些年代的社会动荡,并设定了更广阔的背景,使布鲁门巴赫的分类学,以及他后来决定将欧洲人种称为高加索人的决定,对我们的历史和当前关注的问题如此重要。
大谜题的解决常常取决于微小的细节,这些细节很容易被忽视或忽略。我提出,理解布鲁门巴赫分类的关键,即当今仍在影响和困扰我们的许多事物的基础,在于他用来命名欧洲人种为高加索人的特殊标准——即该地区人民所谓的卓越美貌。首先,为什么一位科学家会如此重视一项明显主观的评估;其次,为什么审美标准会成为对原产地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比较布鲁门巴赫1775年的原始文本与1795年的后期版本,那时高加索人获得了他们的名字。
布鲁门巴赫1795年的最终分类将所有人类分为五组,既根据地理位置又根据外貌定义——按他的顺序,高加索人种(Caucasian variety)指欧洲以及亚洲和非洲毗邻地区的浅肤色人;蒙古人种(Mongolian variety)指亚洲大部分其他居民,包括中国和日本;埃塞俄比亚人种(Ethiopian variety)指非洲的深肤色人;美洲人种(American variety)指新世界的大多数原住民;以及马来人种(Malay variety)指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人和美拉尼西亚人以及澳大利亚的土著。但布鲁门巴赫1775年的原始分类只承认这五种中的前四种,并将马来人种的成员与布鲁门巴赫后来命名为蒙古人的亚洲其他人合并在一起。
现在我们遇到了布鲁门巴赫作为现代种族分类发明者的声誉所带来的悖论。正如我稍后将阐述的,最初的四种族系统并非源于布鲁门巴赫的观察,而只是代表了布鲁门巴赫欣然承认的,他的导师卡尔·林奈在分类学的基础文献《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1758年)中提出的分类。因此,布鲁门巴赫对种族分类的唯一原创贡献在于后来为一些最初包含在更广泛的亚洲群体中的太平洋民族增加了马来人种。
这个改变看似微不足道。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种族分类的创始人归功于布鲁门巴赫,而不是林奈呢?(也许可以说“不予承认”,因为这项事业如今并没有什么好名声。)但布鲁门巴赫看似微小的改变,实际上记录了一个范围无法更广、更具预兆性的理论转变。这个改变之所以被忽视或误解,是因为后来的科学家没有把握住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和哲学原则,即理论是可以通过视觉表现的模型,通常以清晰可定义的几何形式呈现。
通过从林奈的四种族体系转向他自己的五种族方案,布鲁门巴赫彻底改变了人类秩序的几何结构,从一个没有明确等级的地理模型,变成了一个基于感知美貌而奇怪地向两边散开,以高加索人为理想的价值等级体系。马来类别的加入对于这种几何重构至关重要——因此,它成为了概念转化的关键,而不仅仅是旧方案中事实信息的简单完善。(对于科学革命蕴含着这种几何转变的见解,我感谢我的朋友 Rhonda Roland Shearer,她将在其即将出版的著作《平面世界假说》中阐述这些主题。)
布鲁门巴赫崇拜他的老师林奈,并承认林奈是他最初四重种族分类的来源:“我在数量上遵循林奈,但通过其他界限来定义我的变种”(1775年版)。后来,在增加马来变种时,布鲁门巴赫以最尊重的措辞将他的改变认定为与老导师的分歧:“林奈的人类划分已无法再坚持;为此,我在这篇小作品中,像其他人一样,不再追随那位杰出的人物。”
林奈将智人分为四个基本变种,主要由地理位置定义,而且有趣的是,并非以大多数欧洲人在种族主义传统中偏爱的等级顺序排列——美洲人(Americanus)、欧洲人(Europaeus)、亚洲人(Asiaticus)和非洲人(Afer, or African)。(他还提到了另外两个奇特的类别:ferus 指“野孩”,偶尔在森林中发现,可能由动物抚养——大多数被证明是被父母遗弃的智障或精神疾病儿童——以及monstrous 指毛发浓密有尾巴的人,以及其他旅行者的臆造。)这样做,林奈并没有提出任何原创的东西;他只是将人类映射到传统制图学的四个地理区域。
林奈随后按照颜色、体液和姿态的顺序来描述这些群体。同样,这些类别都没有明确地暗示按价值进行排序。林奈在做出这些决定时,再次只是遵循了经典的分类学理论。例如,他对四种体液的使用反映了古代和中世纪的理论,即一个人的气质源于四种体液(humor在拉丁语中意为“湿润”)——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的平衡。根据哪种物质占主导地位,一个人可能是多血质(血液的快乐领域)、黏液质(迟钝)、胆汁质(易怒)或抑郁质(悲伤)。四个地理区域,四种体液,四个人种。
对于美洲人种,林奈写道“赤色、胆汁质、直立”(rufus, cholericus, rectus);对于欧洲人种,“白色、多血质、肌肉发达”(albus, sanguineus, torosus);对于亚洲人种,“苍黄色、忧郁质、僵硬”(luridus, melancholicus, rigidus);对于非洲人种,“黑色、黏液质、松弛”(niger, phlegmaticus, laxus)。
我并不是要否认林奈对自己的欧洲人种优于其他人种的传统信仰。一个多血质、肌肉发达的欧洲人听起来肯定比一个忧郁、僵硬的亚洲人好。事实上,林奈在每个群体的描述结尾都加上了一个更露骨的种族主义标签,试图用两个词概括其行为。因此,美洲人是regitur consuetudine(受习惯支配);欧洲人是regitur ritibus(受习俗支配);亚洲人是regitur opinionibus(受信仰支配);而非洲人是regitur arbitrio(受反复无常支配)。毫无疑问,受既定和深思熟虑的习俗支配胜过不受思考的习惯或信仰支配,而所有这些都优于反复无常——从而导致了欧洲人排第一,亚洲人和美洲人居中,非洲人垫底的隐含和传统的种族主义排名。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暗示,林奈模型的显性几何结构并非线性的或等级化的。当我们把他的方案在脑海中描绘成一幅基本图景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世界地图被划分为四个区域,每个区域的人们都由一系列不同的特征来描述。简而言之,林奈的首要排序原则是制图学;如果他想将等级制度作为人类多样性的基本图景来推广,他肯定会把欧洲人排在第一位,非洲人排在最后,但他却从美洲原住民开始。
从地理排序到等级排序的人类多样性转变,必须被视为西方科学史上最具决定性的转折之一——因为除了铁路和核弹,还有什么能对我们的集体生活产生更大的实际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完全是负面的影响?讽刺的是,布鲁门巴赫正是这一转变的焦点,因为他的五种族方案成为经典,并将人类秩序的几何结构从林奈的制图学转变为线性排序——简而言之,转变为一个基于假定价值的系统。
我说讽刺,是因为布鲁门巴赫是所有启蒙思想家中种族主义色彩最淡、最友善的一位。如此致力于人类团结、主张各群体之间道德和智力差异无关紧要的人,却改变了人类秩序的心理几何结构,使其成为一个此后一直服务于种族主义的方案,这多么奇特。然而再一想,这种情况其实并不那么奇怪——因为大多数科学家都相当不了解其所有理论背后的心理机制,特别是视觉或几何学上的含义。
科学中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宣称,理论的变化必须由观察驱动。由于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这个简单的公式,他们便认为自己的解释转变只记录了他们对新发现事实的更好理解。因此,科学家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对世界杂乱模糊的客观事实施加的心理影响。这种心理影响来源于多种因素,包括心理 predispositions 和社会背景。布鲁门巴赫生活的时代,进步思想和欧洲文化的优越性主导着政治和社会生活。隐含的、松散形成的甚至无意识的种族等级观念与这种世界观非常吻合——事实上,几乎任何其他组织方案都会显得异常。我怀疑布鲁门巴赫是否通过重新绘制人类群体的心理图谱而积极鼓励种族主义。他只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地,记录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观点。但思想会产生后果,无论其倡导者的动机或意图如何。
布鲁门巴赫当然认为,他从林奈的四种族体系转向他自己的五种族方案,仅仅源于他对自然事实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在其论著第二版(1781年)中宣布这一改变时就是这样说的:“以前,在该著作的第一版中,我将所有人类分为四种变异;但在我更积极地调查了东亚和美洲的不同民族,并可以说,更仔细地观察了他们之后,我被迫放弃了那种划分,取而代之的是以下五种变异,因为它们更符合自然。”在1795年第三版的前言中,布鲁门巴赫声明他放弃了林奈的方案,以便“根据自然的真相”来安排“人类的变异”。当科学家采纳理论纯粹来源于观察的神话,而没有掌握影响其思维的个人和社会因素时,他们不仅错过了其观点改变的原因;他们甚至可能未能理解新理论所蕴含的深刻心智转变。
布鲁门巴赫坚决维护人类物种的统一性,反对当时日益流行的(并且无疑更有利于传统形式种族主义的)另一种观点,即每个主要种族都是单独创造的。他在第三版结尾写道:“毫无疑问,我们很可能正确地将所有……人类变种……归于同一物种。”
作为统一性的主要论据,布鲁门巴赫指出所有所谓的种族特征都从一个民族连续地过渡到另一个民族,无法定义任何独立的有界限的群体。“因为尽管相距遥远的民族之间似乎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以至于你很容易将好望角居民、格陵兰人和切尔克斯人视为许多不同的人类物种,但当彻底考虑这个问题时,你会发现所有这些民族都彼此融合,一种人类变种如此明显地过渡到另一种,以至于你无法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他特别驳斥了常见的种族主义主张,即非洲黑人具有独特的劣势特征:“埃塞俄比亚人中没有哪个特征如此独特和普遍,以至于在其他人类变种中无法在某一方面观察到。”
布鲁门巴赫在达尔文之前80年著书,他相信智人是在单一地区被创造,然后扩散到全球。他继而提出,我们的种族多样性是由于这种扩散到其他气候和地形,以及我们在这些不同地区采用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产生的。遵循他那个时代的术语,布鲁门巴赫将这些变化称为“退化”(degenerations)——并非指现代意义上的恶化,而是指从创造时的最初人类形态(de意为“来自”,genus指我们的原始祖先)的字面意义上的偏离。
布鲁门巴赫认为,这些退化中的大多数直接源于气候和栖息地的差异——从深色皮肤与热带环境的相关性等广泛模式,到更具体(且异想天开)的归因,包括推测一些澳大利亚土著狭窄的眼睛可能是为了应对“持续不断的蚋群……收缩了居民的自然面貌”而产生的。他还认为,其他变化是由于不同地区采纳的习俗而引起的。例如,那些通过襁褓板或婴儿背带压迫婴儿头部的民族,最终会拥有相对较长的头骨。布鲁门巴赫认为,“不同民族头型几乎所有的多样性都应归因于生活方式和艺术。”
布鲁门巴赫认为,这些经过多代促进的变化最终可能会遗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布鲁门巴赫写道,“艺术可能会退化成第二天性。”但他同时也认为,大多数种族变异,作为气候和习俗的表面影响,通过搬迁到新区域或采取新行为,很容易改变或逆转。生活在热带地区几代人的白人欧洲人可能会变成深肤色,而被奴役到高纬度地区的非洲人最终可能会变白:“肤色,无论其原因是什么,无论是胆汁,还是太阳、空气或气候的影响,总之都是偶然且易变的事物,绝不能构成物种的多样性,”他写道。
布鲁门巴赫深信种族变异的表浅性,他捍卫所有民族的智力和道德统一。他对非洲黑人和欧洲白人的平等地位持有特别强烈的看法。他可能在称赞“我们这些黑人兄弟的良好性情和才能”时带有居高临下的态度,但这总比恶意的蔑视要好。他为废除奴隶制奔走呼号,并宣称奴隶在道德上优于他们的俘虏,他谈到一种“天生的温柔之心,从未在运奴船上或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中被他们的白人刽子手的暴行所麻痹或根除”。
布鲁门巴赫在他的家中建立了一个专门收藏黑人作者作品的图书馆,特别赞扬了菲利斯·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的诗歌,她是一位波士顿的奴隶,其作品直到最近才被重新发现:“我收藏了几位[黑人作者]的英语、荷兰语和拉丁语诗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无疑是波士顿的菲利斯·惠特利的作品,她因此享有盛誉。”最后,布鲁门巴赫指出,许多高加索民族在偏见和奴役这种最令人沮丧的环境下,都无法拥有像黑非洲那样优秀的作家和学者群体:“要列举出欧洲一些著名的省份,你很难立刻找到那么多优秀的作家、诗人、哲学家和巴黎科学院的通讯员,这并非难事。”
然而,当布鲁门巴赫在背离林奈地理学的决定性转变中呈现他关于人类多样性的心智图景时,他挑选了一个特定群体作为最接近被创造的理想,然后通过与这个原型标准相对偏离的程度来描述所有其他群体。他最终建立了一个将单一民族置于顶端的系统,然后设想了两条从这个理想向着越来越退化(不那么有吸引力,但并非道德上无价值或智力迟钝)的方向对称地偏离的路线。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高加索这个名字的谜团,以及布鲁门巴赫增加第五个种族——马来人种的重要性。布鲁门巴赫选择将他自己的欧洲人种视为最接近被创造的理想,然后寻找欧洲人中最完美的子集——可以说,是高尚中的最高尚。正如我们所见,他将高加索山脉周围的人民确定为原始理想最贴切的 воплощение,并进而以其最优秀的代表命名了整个欧洲人种。
但布鲁门巴赫现在面临一个困境。他已经肯定了所有民族在智力和道德上的平等。因此,他不能使用这些传统的种族主义排名标准来确立与高加索理想相对偏离的程度。相反,无论我们今天认为这个标准多么主观(甚至荒谬),布鲁门巴赫选择了身体美作为他排名的指导。他只是简单地肯定欧洲人最美丽,而高加索人是最漂亮的。这解释了为什么布鲁门巴赫在本文章引用的第一段中,将高加索人的极致美貌与人类起源地联系起来。布鲁门巴赫将所有后续的变异都视为偏离最初被创造的理想——因此,最美丽的人民必定生活在离我们原始家园最近的地方。
布鲁门巴赫的描述中充满了他的主观审美感,但他却将其呈现为似乎在讨论一种客观且可量化的属性,不容置疑或异议。他将一个格鲁吉亚女性头骨(在高加索山附近发现)描述为“确实是最美丽的头骨形态……它本身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无论观察者多么不留意”。然后,他从审美角度捍卫他的欧洲标准:“首先,这个种群展现了……最美丽的头骨形态,其他种群则以最容易的渐变方式从这个平均的原始类型分化出来……此外,它是白色的,我们完全可以假定这是人类的原始肤色,因为……它很容易退化成棕色,但深色要变白则困难得多。”
布鲁门巴赫随后将人类所有变异呈现为从高加索理想出发的两个连续偏离的系谱,最终达到人类最退化(最不具吸引力,并非道德上最无价值或智力最迟钝)的两种形式——一方是亚洲人,另一方是非洲人。但布鲁门巴赫也希望指定介于理想和最退化之间的中间形式,特别是考虑到即使是渐变也构成了他论证人类统一性的主要依据。在他最初的四种族体系中,他可以将美洲原住民认定为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的中间形式,但谁将充当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的过渡形式呢?
四种族体系中没有合适的群体。但是,创造第五个种族类别作为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的中间体将完善新的对称几何结构。因此,布鲁门巴赫增加了马来人种,并非作为次要的事实完善,而是作为重新构建整个人类多样性理论的工具。通过这一举动,他实现了从林奈无等级地理模型到隐含价值的传统等级体系的几何转变,而这种体系自那时起就引发了如此多的社会悲痛。
我将高加索人置于首位……这让我认为它是原始人种。它向两个方向分化,彼此最遥远且差异巨大;即,一侧是埃塞俄比亚人种,另一侧是蒙古人种。其余两种则占据了原始人种与这两个极端变种之间的中间位置;也就是说,美洲人种介于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之间;马来人种介于高加索人种和埃塞俄比亚人种之间。[摘自布鲁门巴赫第三版。]
学者们常常认为,学术思想最坏不过是无害的,最好也不过是略有趣味甚至具有启发性。但思想并非存在于我们通常用来形容学术无关紧要的“象牙塔”中。正如帕斯卡所言,我们是会思想的芦苇,思想驱动着人类历史。如果没有种族主义,希特勒会走向何方?如果没有自由,杰斐逊又会如何?布鲁门巴赫一生都是一位隐居的教授,但他的思想以他从未预料到的方式回荡,贯穿我们的战争、社会动荡、苦难和希望。
因此,我再次回到1776年非凡的巧合来结束本文——当年杰斐逊撰写《独立宣言》时,布鲁门巴赫正在出版其拉丁文著作的第一版。我们应该记住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和道德学家阿克顿勋爵关于思想推动历史的力量的警句:
正是从美洲,那些长期被禁锢在孤独思想家胸中,隐藏在拉丁文册页里的思想,以“人权”之名,如同征服者般横扫世界,注定要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