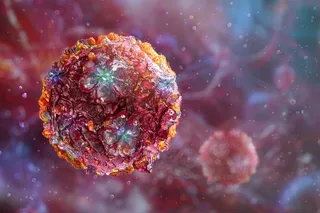人类婴儿几乎无法通过产道。即使经历了如此艰难的过程,新生儿出来时……简直毫无能力。与黑猩猩宝宝不同,它们基本上就是缩小版的成年猩猩,人类婴儿需要花整整一年的时间才能学会坐立、行走和说话。这是一个让许多人类学家困惑的难题: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进化?
臀部通常是罪魁祸首。近一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假设臀部面临着“产科困境”——它们必须足够狭窄以便我们双足行走,但又必须足够宽才能分娩出大脑发达的婴儿。他们认为,进化的解决方案是缩短妊娠期,以便发育不完全的新生儿能够挤过产道。“这种权衡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有如此脆弱的婴儿,以及分娩如此痛苦和漫长,”图宾根大学和苏黎世大学的古人类学家Nicole Webb说。
这个逻辑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也许关键证据就在那里。Webb的团队正在为此努力。但罗德岛大学的生物人类学家Holly Dunsworth等人认为,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并不多。“人们很容易被精彩的故事所吸引,”她说,“但产科困境是进化过程中一种不真实的说法。”
Dunsworth并不否认生育是困难的。但她认为,这种困难并非由产科困境引起。事实上,她表示,这种普遍存在的观点会病态化产妇的臀部,“剥夺了她们的力量”。“臀部在进化上受到损害”的有害观念会让人产生自我怀疑,并影响医疗决策,例如是否选择剖腹产。最终,它暗示医疗干预“不可避免或必须”。
臀部不会说谎
怀疑论者通过引用两个主要批评来削弱这一假设:宽阔的臀部可能不会妨碍运动,而人类婴儿可能并非比我们曾经认为的更早出生。
当然,狭窄的骨盆可能导致医疗灾难。但最近的研究对宽阔的臀部是否会妨碍运动提出了质疑。在现代人类中,没有证据表明宽阔的臀部对行走有负面影响——即使在比较男性和女性时也是如此。事实上,一些专家推测,宽阔的骨盆可能比狭窄的骨盆更有效率。
但Webb对这些发现有不同的解读。对她来说,零相关性证实了臀部确实存在一个限制;她解释说,双足行走的进化将有效的骨盆形状锁定在了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因为我们的人口已经筛选出了擅长行走的人,在这个狭窄的变异范围内寻找不会显示出任何有意义的差异。
“这就是我们被限制的范围,”Webb说,“基于这些理由就说不存在产科困境,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说法。”
当然,关于产科困境所谓的“解决方案”也存在一个问题:人类的怀孕并非早产。诚然,我们出生时大脑容量只有成年后的30%不到,是所有灵长类动物中比例最低的(包括黑猩猩,它们的出生时大脑容量约为成年大脑的40%)。而且出生后,我们必须生长和重塑整个神经系统,才能学会说话、坐立和行走等行为。
但胎儿在母体外发育大脑并不是人类独有的。事实上,所有灵长类动物的大部分大脑发育都在出生后进行。如果非要说的话,与其它哺乳动物相比,我们实际上妊娠期更长。体型更大的物种通常妊娠期更长,但我们的妊娠期比科学家们为任何其他体型相似的灵长类动物预测的要长37天。这比倭黑猩猩和黑猩猩长六到八周,比大猩猩长一到三周。
“按重量算,考虑到母体大小,我们的妊娠期最长,我们的婴儿最大,大脑也最大,”Dunsworth说。“这看起来不像我们早产。这看起来像是我们在怀孕期间从母亲那里摄取了大量营养,然后她生下了一个巨大、惊人的婴儿。”
然而,Webb认为妊娠期长度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神经发育。归根结底,我们出生时是依赖他人的,并且有很多事情需要成长。即使妊娠期不算特别长,我们的婴儿仍然异常脆弱。
新理论?
Dunsworth认为产科困境很有说服力,但站不住脚。拥有宽阔臀部没有已知的代价,即使有,如果人类婴儿并非相对早产,那么也无法解释。因此,在2012年,她和她的同事提出了一个替代机制来解释分娩的时间。
他们将其命名为EGG假说——意为能量学、妊娠期和生长。他们认为,因为孕育胎儿的成本很高,所以妊娠期受到亲代能量的限制。简而言之,像人类这样的大型哺乳动物可以消耗更多的能量,并耐受更长的妊娠期。这是所有哺乳动物面临的限制,而人类并没有打破这一趋势。“我想把它命名为HAM & EGG假说,意为‘人类是哺乳动物’,但那太俗气了,”Dunsworth说,她并非有意使用双关语。
随着胎儿生长速度加快,能量需求呈指数级增长,父母无法跟上。人类最多只能维持比基础代谢率(我们在放松时仅维持生命所需的能量)高2到2.5倍的水平。胎儿的需求在孕晚期接近这一极限,并在大约9到10个月时有越过极限的危险。父母之所以在此之后分娩,仅仅是因为他们无法再承担能量的消耗。
“日复一日地在体内生长活体组织,一定有一个能量极限,”Dunsworth说。“在我研究产科困境的证据却找不到时,这一点似乎很明显。”
与此同时,Webb认为EGG假说尚未完全推翻比它更古老的骨骼假说。她认为两者可以很好地共存。“我认为两者都是拼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不应该相互排斥。”人类生育可能更多地取决于能量储备或骨骼结构——但Webb对此没有偏见。“我们都只是希望让当今女性的生育变得更好。”
尽管研究人员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但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消除争论,并为创造一个生育尽可能安全的世界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