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施瓦茨博士下午 3 点接到电话,下午 5 点前收到剧本,第二天下午他就出现在那里,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坐在一起,探讨医学中最令人衰弱的精神疾病之一的复杂性。
迪卡普里奥正在《飞行家》中饰演霍华德·休斯,这个角色要求他像休斯一样,从天才亿万富翁变成一个被强迫症困扰的蓬头垢面的隐士。施瓦茨的著作《大脑锁》和《心智与大脑》使他成为世界上关于强迫症潜在机制和治疗的顶尖权威之一,这种疾病困扰患者以不合理的想法和恐惧,这反过来又迫使他们重复行为。
施瓦茨在第一天就宣布,他不会教迪卡普里奥强迫症患者的举止。相反,他会向他展示“如何成为一个患有强迫症的人”,这样他的大脑就会“像患有这种疾病的人的大脑一样”。
信息令人不安,但迪卡普里奥却欣然尝试。他很快就向施瓦茨指出了剧本中的一个特定片段。“就在这里,三页纸,我只有一句话,”他说。重复了 46 次“给我看看蓝图”,略有改动。
施瓦茨解释说,强迫症患者会从事各种各样的问题行为——强迫性洗手、开门、重复检查烤箱和门,甚至重复同一个词、短语或句子。在神经学层面上,其原因是两个大脑区域——眼眶额叶皮层和尾状核——之间的过度连接,产生了一股毫无根据的致命恐惧的浪潮,并触发了习惯性反应,作为获得平静的唯一方式。但最糟糕的是,尽管强迫症患者认识到所有这些想法和行为都是非理性的,但他们仍然感到不得不服从它们。
施瓦茨向迪卡普里奥详细讲解了潜在的神经学知识,以帮助他理解,对休斯来说,这四个词——“给我看看蓝图”——具有神奇的力量,让他摆脱恐惧。“这些词,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就好像他的生命依赖于它们一样,”施瓦茨建议道,“但他同时也明白,这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在最终于2004年上映的这部电影中,这一幕也许是最令人痛苦的。迪卡普里奥饰演的休斯每次重述时都会扭转句子的方向,强调不同的词语,运用不同的节奏。有时他几乎低声快速地念完句子。另一些时候,他会放慢速度,寻找正确的发音组合,正确的节奏,以摆脱内心翻腾的恐惧。与此同时,他的脸上流露出一种痛苦的自我厌恶。
迪卡普里奥凭借《飞行家》获得了奥斯卡提名,或许也患上了轻度疾病。据报道,他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才恢复正常。如今,他自愿沉迷于疾病并随后康复,这代表了我们流行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神经可塑性公开案例之一——大脑改变形状、功能、构造或大小的能力。
但施瓦茨说,主流科学尚未接受像迪卡普里奥这样的经历,这种经历基于施瓦茨所说的“自我导向的神经可塑性”,即用思想重塑大脑的能力。他说,这种力量不仅能拯救他的病人,还能拯救自由意志。
我们拥有自由意志的观念与许多现代神经科学研究背道而驰,这些研究表明,我们越来越多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先天固定的——从我们投票给哪个候选人到我们蛋筒冰淇淋上的哪种口味。事实上,大卫·伊格尔曼和萨姆·哈里斯等神经科学家已经出版了畅销书,提出我们归根结底是功能强大、妄想的机器人。
因此,在自由意志备受争议的时代,我们文化中最杰出的思想家们很少有人同意杰弗里·施瓦茨的观点——这位科学家碰巧对自己的“不合群”感到完全自在。
强迫症家庭
在一个温暖的秋日傍晚,施瓦茨带着我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园,观看一次强迫症小组治疗。施瓦茨身材矮小方正,头发卷曲紧密,肩部像一位年迈的摔跤手般佝偻着,他在停车场里漫步,直到他看到一位病人,便亲切地叫着他的名字。
“你好吗?”他说。
那人抽着烟,靠在施瓦茨大楼入口外的一堵砖墙上,挥了挥手,并用手势指了指里面,表示他会在小组会议上说话。施瓦茨点点头,当我们经过他时转向我。“哦哦,”他说,“也许他过得不太好。”
施瓦茨在我前面走了几步,打开了赛梅尔神经科学和人类行为研究所的门,那是一座由玻璃和砖块构成的三层楼,里面有教室和实验室。“嗯,”他说,对我扬了扬眉毛,“我们走吧。这些是我的病人。”
走进一个满是施瓦茨病人的房间,就像走进一群革命者的集会。他们都带着那种随意的熟悉感和安静的成就感。他们热情地问候他们的领袖施瓦茨。人们谈论着如何夺回以前因强迫症而失去的时间。一个演员说,他觉得自己足够自信,可以再次去试镜。
宝拉·斯科特,他们中的资深客户,正好说明了他们的旅程是多么戏剧性。“我第一次见到杰弗里时,”宝拉说,“我正在考虑自杀。现在,我甚至没有与我的强迫症作斗争。”宝拉的疾病仍然存在,但这种状况不再折磨她,不再控制她。强迫症只是她在日常生活中处理的一件事。
皆为苦难
施瓦茨开创性技术背后的洞察力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大屠杀蹂躏了他的血脉,一位年长的亲戚向他讲述了这段沉重的历史。“我记得他告诉我,我的职责就是为那些死去的人而活,”施瓦茨说,“他不是指某种隐喻,也不是为了激励我。他是字面意思。”
当其他同龄孩子玩耍时,他却在图书馆里长时间阅读大屠杀审判记录。一页又一页,他读到关于那些为了权力、金钱,或者仅仅是为了在一个突然陷入邪恶的国家生存而做出可怕行为的人的证词。他说,他从中得出了一个“人类堕落并需要某种帮助”的形象。
他在罗彻斯特大学度过的大学岁月产生了另一种影响:正念的专注力,这是一种佛教修行,信徒们学习以完全公正的态度看待自己的思想和冲动。在正念的帮助下,施瓦茨在学业上表现出色,被苏格兰爱丁堡接受为哲学荣誉学者。
当他开始他的医学事业时,他知道他想以某种方式将所有这些元素结合起来:他想证明佛教的正念练习可以帮助我们选择除了大屠杀之外的东西,并治愈我们堕落的人类。
施瓦茨在1983年获得了这个机会,当时他同意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精神病学家路易斯·巴克斯特合作,以阐明强迫症的机制。巴克斯特团队将使用当时新颖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扫描仪,施瓦茨回忆起这种庞大的成像机器“看起来像是《2001:太空漫游》里的东西”。
为了进行PET扫描,技术人员会向患者体内注射一种具有生物活性的示踪粒子,该粒子部分由正电子(带正电荷的电子)组成,并附着在某种在代谢中发挥作用的其他分子上,如水或葡萄糖。通过追踪示踪剂分解时发射的正电子,机器可以捕捉生物过程的图像。在这种情况下,施瓦茨和巴克斯特旨在追踪大脑中的血流量。
团队工作期间,施瓦茨查阅文献寻求洞察,发现神经科学家埃德蒙·罗尔斯一项被大多忽视的研究。罗尔斯利用猴子研究眼眶额叶皮层(OFC),这是大脑中与决策相关的区域。在猴子习惯舔杆子以获取甜液体后,对其大脑进行成像。然后,当液体被咸盐水取代后,再次对其舔同一杆子的大脑进行成像。
罗尔斯发现,当猴子被新液体惊吓时,眼眶额叶皮层(OFC)的活动会急剧增加。施瓦茨认为,这是一项巧妙的研究。罗尔斯揭示了OFC作为一种错误检测回路的功能。那么,将OFC与强迫症联系起来就说得通了,因为强迫症会让患者充满对某种错误事物的致命恐惧。
大约在同一时间,施瓦茨建议团队调查尾状核,这是一个靠近OFC的尾状结构,是大脑的习惯中心。他认为,尾状核可能充当强迫症的某种枢纽——一个交通枢纽,在那里,大脑皮层中的理性思维与大脑边缘系统中更原始、受情感支配的中心相遇。这将是重复和恐惧的有害混合物发生碰撞的天然“震中”。
这项研究持续了数月。但有一天,巴克斯特把施瓦茨拉到一边说:“我们成功了。”
数据清晰明了。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强迫症患者表现出眼眶额叶皮层和尾状核的显著过度活跃——即使在休息时也是如此。PET扫描图像显示为色彩爆发,将这些大脑区域描绘成小小的火焰,持续燃烧,显然,即使没有发作,也改变了大脑的功能。
自由意志疗法
现在,强迫症的神经回路已经确定,研究人员可以测试疗法了。利用PET等成像技术,他们可以看到某种治疗方法是否能平息大脑中的“火势”。
对施瓦茨来说,这是利用他对正念兴趣的机会。他设想一个女人被无休止的洗手困扰,但她知道自己的手并不脏。她能够反思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怪异之处,她继续洗手只是因为这似乎是减轻她害怕被污染的唯一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迫症反映了正念冥想的一个关键方面——给予患者对其自身思想的超然视角。施瓦茨推测,这种意识可以促成一种基于正念的治疗策略。毕竟,如果正念的目的是超然地看待我们所有的想法和冲动,那么强迫症患者是否可以使用正念来甚至超然地看待致命的恐惧和强迫症呢?也许正念可以帮助重塑大脑中的强迫症回路。
施瓦茨在1987年遇到了他最早的病人之一宝拉·斯科特,当时她正深陷于一种如此超现实和严重的强迫症,以至于她经常考虑自杀。宝拉的疾病表现为一种不合理的恐惧,即她的男友是酒鬼和吸毒者。
施瓦茨认为宝拉的案例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她选择的重复行为来缓解恐惧,恰恰证明了她对现实有多么清楚。例如,她知道,如果她不断地向男友询问毒品和酒精使用情况,他就会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我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向他隐藏我的感受,”她说,“同时又屈服于强迫症。”
她的解决方案是:严格盘问他,但不让他察觉到她的具体恐惧。她问了他很多关于他一天的问题,基本上是让他详细描述他早餐吃了什么,什么时候上班,上午做了什么,以及和谁一起吃的午餐,看看他是否会不小心说出任何暗示吸毒的话。
其他人也加入了施瓦茨的治疗小组。他们谈到把手搓得通红,以避免感染自己,并由此感染他们的亲人。他们谈到上班迟到,因为他们花了太多时间检查烤箱和门锁。每周,施瓦茨都敦促他的病人以正念修行者在冥想中努力体验每一个念头的方式来体验他们的强迫症症状——超然地,不屈服于情绪。

施瓦茨的强迫症患者掌握正念后,他们的症状减轻了,大脑中的眼眶额叶皮层和尾状核(此处显示为绿色)的火光也减弱了。吉姆·道德尔斯/科学源
“不是我!是我的强迫症!”
在最初的日子里,施瓦茨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往何方,只知道自己的起点。他对客户的要求是真正戏剧性的:他要求他们尽快识别与强迫症相关的想法,并将其重新标记为不真实的——仅仅是他们强迫症的症状——而不屈服于它。小组成员反应热烈,但事情在小组中一位年长的女士多蒂突然惊呼“不是我!是我的强迫症!”之后才真正起步。
这成了小组的号召。施瓦茨意识到他找到了第一步,重新标记。
如果病人一直被脏手的强迫观念困扰,并有洗手的冲动,施瓦茨会建议病人这样想:这不是洗手的冲动。这是我的强迫症带来的恼人想法。他一采用这种方法,他的病人们下周就回来报告说情况有所改善,声称他们不再觉得这种疾病控制了他们。
然而,他们仍然有症状,症状干扰了他们的生活。几周后,当他的病人小组再次参加治疗时,其中一人问道:“医生,你能不能告诉我这该死的东西为什么一直困扰着我——为什么它不消失?”施瓦茨碰巧带着一些强迫症患者的大脑扫描图在文件夹里。“你想知道它为什么不消失吗?”施瓦茨说,“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他充满自信地拿出扫描图,指着他与巴克斯特一起建立的强迫症回路。“大脑的这个区域过度活跃,”他说,然后“砰!”他看到病人脸上发生变化,听者都兴奋不已。宝拉就是经历这个“啊哈”时刻并感到解放的病人之一。那些关于她男友吸毒的奇怪念头不再是精神错乱的迹象。它们甚至不再是她自我的产物。它们只是一个故障大脑的错误传输。
施瓦茨感到房间里的能量在上升,他看到他强迫症小组中先前沮丧的男男女女振作起来,变得更强壮,就好像他们莫名其妙地获得了更多的肌肉力量一样。这成了第二步:重新归因。他教导他的病人将他们的强迫症症状重新归因于某种扭曲的大脑回路,教导他们将大脑的功能视为与他们的自我意识有意义地分离。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患者开始定期报告胜利。起初这些胜利很小。宝拉可以更长时间地避免向男友询问他的一天——先是几分钟,然后是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她可以通过问更少的问题来度过难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患者们报告了一些更值得注意的事情:强迫症的侵入性思维正在减少,发生的频率降低,而且威力也减弱了。
施瓦茨认为,这是因为他的患者实际上正在运用他们的思维力量来重塑他们成年后的大脑——这一发现与当时只有儿童大脑才能经历如此巨大变化的观点相悖。
一天晚上,施瓦茨在办公室外意识到他的病人需要做更多的事情,除了强迫症的侵入性想法之外,还需要一些专注的东西。他回想起正念练习,找到了一个他喜欢的类比。在冥想中,如果他情感上投入到某个特定的思绪中,他会通过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呼吸上来重新调整自己。
运用同样的理念,他允许他的病人将监控呼吸替换为他们认为最吸引人的行为。一些病人发现,每次强迫症发作时,回到相同的健康行为很有帮助:例如散步或园艺。
施瓦茨已经找到了三个步骤——重新标记、重新归因,现在,重新聚焦。
但他需要最后一步,将所有这些整合起来。他把那一步称为重新评估。患者曾经认为如此重要的强迫症想法将被系统地解构、理解,并最终被重新评估为,用施瓦茨的话说,“垃圾……不值得它们所占据的灰质。”相反,施瓦茨的患者学会了高度重视他们的替代行为。
施瓦茨的四步疗法奏效了,但并非易事。这些词语击中了施瓦茨的关键之处,它需要巨大的**意志力**。
重塑大脑
最终,施瓦茨开始觉得他看到了自由意志在起作用:在他照料下的那些人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从事一种新的行为。但他需要等待,看看这种证据是否会出现在脑部扫描中。经过十周的四步治疗,是时候了。
他的病人,在任何治疗开始前都经过了大脑成像,第二次进入了庞大的扫描仪。巴克斯特处理了数据,并告诉了他这个消息:这些病人强迫症回路的活动量已经减少到与药物治疗所能达到的最佳效果相当的程度。强迫症回路,在强迫症患者的基线扫描中如此明亮,现在柔和地发光。
施瓦茨于1992年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并于1996年进行了复制,为我们对成人神经可塑性的概念增添了细微之处。但随后的几年,涌现出许多理论家和著作,它们都削弱了自由意志——以及施瓦茨强迫症疗法的操作模式。
神经科学家萨姆·哈里斯和大卫·伊格尔曼在过去几年里出版了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籍,两本都登上了畅销书榜。哈里斯明确地将人类称为“生化傀儡”。在他看来,我们选择人生道路的能力,不比八号球选择是否落入底袋的能力更强。
在他的书中,伊格尔曼不那么确定自由意志是否存在某种形式,但他思考了当前对心智和大脑的这种看法对犯罪和惩罚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的行为并非我们真正选择的,我们怎能指责罪犯造成的浩劫和痛苦?
施瓦茨将所有这些论点称为“不健康”和“有害”的,特别是对他的强迫症患者的尊严以及他们为夺回生命中的时光所付出的努力。“他们描述了一场斗争,”他谈到他的客户时说,“他们坐在那里,汗流浃背,将注意力从强迫症转移到某种健康的新的行为上。”
他承认,他的影响力或许能帮助他们一小段时间,但他的病人会回家一两周,独自与强迫症抗争。从纯粹的神经学角度来看,如果决定论占据主导地位,他的病人就没有自由意志,也没有希望。他说,扫描本身表明自由意志活得好好的。
施瓦茨认为自由意志如此强大,它甚至字面上影响着我们的进化。2004年,他甚至在探索研究所的《科学异议达尔文主义》上签名,该文件支持了智能设计的异端概念。虽然施瓦茨相信进化,但他表示,神经可塑性的机制改变了我们大脑的形状,可能也塑造了人类进化。以他富有争议的风格,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没什么好隐瞒的
我的访问即将结束,周日杰弗里·施瓦茨带我一起去教堂。“这就是我。我**没什么**好隐瞒的,”这位从犹太教徒转变为佛教徒,再转变为基督徒的人说。当教堂乐队一曲接一曲地演奏时,听到杰弗里·施瓦茨——一个花那么多时间争论的人——为其他目的而提高嗓门:唱歌,这着实令人惊讶。施瓦茨的乐器并不完美,只能间歇性地与正确的音高保持连接,但它有力且出人意料地流畅。
当乐队演奏完礼拜的最后一首歌,一首轻柔摇曳的《您真伟大》时,施瓦茨以一种暗示他坚定信念的音量达到了高潮,他的声音在附近其他人中尖锐地响起。
音乐戛然而止,施瓦茨随即绽放出一个开心的笑容,变身为一个出人意料的形象:一个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心安理得的人。
[本文最初以“为自由意志辩护”为题刊载于纸质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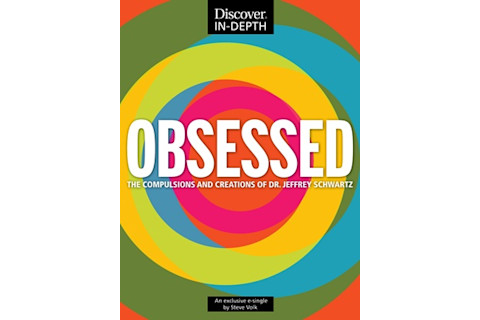
阅读《发现》独家电子单行本《着迷:杰弗里·施瓦茨博士的强迫与创造》中的扩展版故事。















